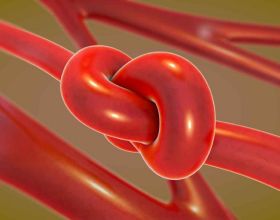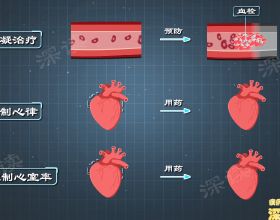編者按:邁克爾·貝里爵士 (Sir Michael Berry)生於1941年,現為英國布里斯托大學Melville Wills榮休物理學教授,是當今最負盛名的理論物理學家之一。他1982年當選英國皇家學會會士,1995年當選倫敦數學學會會士以及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1996年被英女王封為爵士。他曾獲得的獎項主要包括:狄拉克獎(1996)、卡皮查獎(1997)、沃爾夫獎(1998)、昂薩格獎(2001)、波利亞獎 (2005)、洛倫茲獎(2015)、邁特納獎(2019)以及復旦中植獎(2020)等。
貝里爵士極為重視物理學不同領域之間的深刻關聯,常常引用他在布里斯托大學的同事Charles Frank(理論物理學家,Copley 獎獲得者,「弗蘭克-瑞德位錯源」開創者)的話說「物理學不僅僅只關注事物的本質,也關注不同事物本質之間的關聯」。他在物理和數學至少四個重要方向均做出了開創性貢獻,包括貝里相位、奇點理論、量子混沌和漸進分析。貝里爵士在每個方向的洞見均迅速滲透到物理學甚至是純數學的多個分支並催生了全新的概念和獨特的研究視角。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他在1989年解決了斯托克斯遺留下來的、在漸進分析領域一個長達150年懸而未決的數學難題。貝里爵士雖已年過八旬,依然堅持開展原創性研究,每年均有數篇獨立作者研究論文發表。
貝里爵士於2022年1月7日接受了Advanced Photonics特邀編輯、國防科技大學前沿交叉學科學院劉偉博士的專訪,並在定稿的過程中刪除了一些比較尖銳的觀點和評論。儘管私下言辭犀利,但公開場合他會盡量恪守英國的紳士傳統。本次採訪僅僅涵蓋了貝里爵士研究領域的一部分,例如他對黎曼猜想的重要貢獻在採訪中並沒有提及。貝里爵士善於從日常生活現象中發掘深邃的數學和物理概念,在整個學術生涯中自始至終都對光學,特別是日常生活中的光學現象抱有極大的興趣,其中就包括中國古代銅鏡的神奇反射現象。對於部分學者(包括光學領域學者)的「光學相對於其它物理學領域比較淺顯」的言論,他曾反駁道「沒有膚淺的學問,只有膚淺的人」。
英文全文已公開發表於Advanced Photonics 2022年第1期 Explorer of light, and more: an interview with Sir Michael Berry。
劉偉:貝里教授,謝謝你接受採訪。此次訪談是Advanced Photonics特意安排的。訪談中我們可以隨意談論和數學、物理相關的,或其它任意你喜歡的話題,我們沒必要把話題侷限在光子學領域。Advanced Photonics的編輯們也希望這次訪談能讓其它領域的學者受益。
如今貝里相位的概念幾乎無所不在。它不僅貫穿於物理學的不同分支,也出現在化學和其它學科中,我們無論怎麼強調它的重要性都不過分。但這也導致一提到你,大家只會想到貝里相位。實際上你對物理學的多個不同分支都有極其原創性的貢獻。更鮮為人知的是,你同時對數學也有非常重要的貢獻,並培養了很多在物理學和數學領域極有建樹的學生。例如你的博士生Jonathan Keating現在是牛津大學數學系Sedleian講席教授、英國皇家學會會士、以及倫敦數學學會會長。我第一個想問的問題是:你一開始的時候為什麼沒有選擇數學?
貝里:因為我剛開始讀研究生的時候,對數學幾乎一無所知。那個時候我很清楚自己喜歡理論物理,但對數學卻知之甚少也鮮有熱情。後來我發現自己可以做一些數學計算,並慢慢地開始喜歡上數學概念。其實我從來沒有修過非常高等的數學課程,直到現在也只是對和物理有緊密關聯的那部分數學感興趣。當然和物理有關聯並不意味著一定和實驗物理有關聯。雖然我自己也動手做實驗,但實驗物理不是我關心的重點。
劉偉:還有個和數學相關的問題。我覺得你是一個自立而孤傲的人,你的工作方式更像數學家而不是物理學家。我想引用兩個數學家的話來闡明我的意思,他們一位是菲爾茲獎獲得者阿蘭·孔涅 (Alain Connes),另一位是首屆阿貝爾獎獲得者(同時也是菲爾茲獎獲得者) 讓-皮埃爾·塞爾(Jean-Pierre Serre)。 孔涅說「每個數學家都是與眾不同的,通常情況下數學家更像費米子,不屑於研究一些很時髦的題目;然而物理學家卻更像玻色子,熱衷於扎堆還時常賣弄吹噓,這是我們數學家非常不齒的。」塞爾說「我相信數學中最好的想法一定是個人的,我非常確信這一點!」你能評論一下他們的觀點麼?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說物理學中最好的想法也一定是個人的?
貝里:實際上不能這麼說。費米子的特點是互相迴避,但我不會迴避其他科學家,我喜歡和別人討論。你看我文章就知道,我偶爾也有些合作者,當然數量沒其他人多。我也獨立寫了很多文章,但這並不是因為我在刻意迴避其他人。科學從本質上講是一種集體活動,有些人認為自己能閉門造車,實際是不可能的,他們總需要站在別人的肩膀上。這是我對孔涅的回應,我認識孔涅也非常尊重他。
塞爾我並不認識,我明白他想表達的意思,但不認同他的觀點。在物理學中我們都會覺得新的發現是屬於自己的,因為它來自於自己全身心的投入,可過不了幾年其他人也大機率會發現同樣的東西。科學初看起來像是一種個人行為,可本質上它是一種為了實現更深層次理解的集體活動。我覺得科學是人類活動中最接近科幻小說中稱之為集體意識的東西。在過去幾個世紀中,科學上所取得的巨大進步都有意或無意地建立在同輩或前輩的成就之上。
我並不像孔涅所說的數學家那樣鄙視熱門課題,只是自己不太喜歡扎堆去研究它們。例如拓撲絕緣體、量子霍爾效應、高溫超導和絃論等,這些都是非常有趣、非常科學有效的研究課題,有很多人研究他們自然是極好的。不過也許研究弦論的人有點太多了,當然這不能怪開創弦論的那些人。我的選擇是有點與眾不同,也許是因為我太懶,不想讀太多論文。實際上我也讀很多論文,但確實不會到處翻找每一篇和自己的研究相關的文獻。當然這樣偶爾也會犯錯,最近我就發現自己忽略了一篇以前很重要的文獻,它恰好探討了我正在思考的問題。
劉偉:你對很多研究方向有一種近似殘酷的評論,當然只是私下評論,公開場合你從不如此。你的評論是「此方向雖然有趣,但無本質意義」。我想知道你判斷一項研究有沒有本質意義的標準是什麼?
貝里:這個評論談不上殘酷,有很多物理工作包括我自己的一些工作也都談不上有本質意義。我一生中有些想法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有本質意義的,當然它們不能和伽利略、麥克斯韋、狄拉克等人的想法相提並論。如果你的工作是簡潔而又優雅的,縱使是對前人工作的推廣,它也是有效的。我經常當審稿人,常會評論「這是有效的工作,計算也是正確的,但它更適合一些僅有教學意義的期刊,而不是核心研究期刊」。有些人可能會覺得這樣的評論很殘酷,但事實並非如此,我只是表達內心真實的想法罷了,因為這樣的評論也適用於我自己的相當一部分工作。我在《歐洲物理學雜誌》上發表了很多文章,這本身就是一本僅具有高等教學價值的雜誌。我發表的一些文章,現在回想起來,如果是別人就可能會投到例如《物理評論快報》(Physical Review Letters) 這樣的雜誌,但我自己不大關心文章發表在什麼地方。
劉偉:我個人的感覺是,一項工作想要吸引你,它得有一個清晰的數學結構,這樣你才更有可能覺得它有本質意義。可以這麼說麼?
貝里:大機率可以這麼說。
劉偉:所以你喜歡數學結構。
貝里:我覺得不管大家有沒有意識到,物理必須得用數學表達。這個想法可以追溯到伽利略,他說數學是科學的語言。伽利略所說的數學是指幾何學,實際上科學的語言還不止幾何這一門。科學需要數學,這背後是有深層原因的,對此我專門寫文章探討過。你知道尤金·維格納 (Eugene Wigner,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率先將對稱性原理引入粒子物理領域) 有一種非常有名的論述「數學在自然科學中具有不可思議的有效性」,因為他很驚訝,我們所有人也都很驚訝:為什麼很久之前發現的抽象的數學概念能和我們當下正在嘗試理解的東西完美契合?我並不同意維格納的觀點,數學能有效描述自然科學固然是十分美妙的,但其中並沒有什麼是不可思議的。我們都希望能深入理解前人沒能理解的宇宙奧秘,但理解得建立在概念之上。我們人類所發展出來的最精密的概念系統是什麼?是數學結構。有些數學結構已經存在,有些並不存在而需要重新創造。這兩種情況我都碰到過。從本質上講,我們只能理解那些可以被概念化的東西。
人類的智力非常有限,我們從事科學研究也就只有幾百年而已。當有人說到萬物理論時,他們表達的更多是找到某種理論的熱情,我不會太當真。人類總歸是比狗要知道得多一點,狗不能做量子計算而我們可以。但是極可能有很多其它東西是我們完全不知道的,就如同狗不知道量子計算那樣。人類學會了攜手向前,這有利於我們取得更快更深入的突破,可我們的智力還是有限的,僅僅發展出了數學這樣的概念框架。我差點忘了,我們還發展出了至少另外一套概念框架,它和數學一樣精密而又豐富多彩,那就是音樂。我非常嚴肅認真地對待維格納的論斷,但自己並不認同,他的觀點也沒能影響我對數學和物理的既有觀念。我在美國田納西州的橡樹嶺國家實驗室做維格納冠名報告 (Wigner Lecture) 的時候指出自己對維格納的觀點持有異議,本以為這樣會引起騷動並被攆出報告廳,但後來證明是我多慮了。
劉偉:貝里教授,你出身貧寒,母親是裁縫,父親是計程車司機。畢業於埃克塞特大學和聖安德魯斯大學,它們都不是最有名的大學。我個人覺得,因為這些背景,你對那些表面上看起來高大上的東西並不「感冒」。例如上次來訪長沙,你告訴我說自己特別喜歡像德雅路這樣的狹窄而擁擠的街道,街道上人流穿梭,很像你小時候生活過的地方。我覺得你不大喜歡那些表面上看起來富麗堂皇的地方。我很想知道你性格中的這一面是不是和另外一件事情有關聯,那就是你拒絕了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在對稱破缺、安德森局域、反磁性、超導等眾多物理學領域具有開創性的貢獻。安德森和楊振寧先生對於大型粒子對撞機持有相似的懷疑態度。)希望你加入普林斯頓大學的邀請。
貝里:邀請並不是安德森發出的,但是他知道這個邀請。最早提議我加入普林斯頓大學的是Martin Kruskal(美國數學家和物理學家,美國國家科學獎章和美國數學學會 Steele 獎獲得者,對孤子等領域有開創性的貢獻)。普林斯頓當然是極好的地方,他們對我也很友善,邀請我加入的還有其它學校。每當我非常客觀地考慮自己日常的科研工作和生活,想來想去還是覺得留在布里斯托最好,這兒更適合我的風格,僅此而已。
沒有選擇普林斯頓還有另外一層原因。我知道美國的同事需要在稅務檔案上消耗大把的時間,在英國應付這樣的事情我每年只需花半個鐘頭。這當然只是其它眾多麻煩中的一個。如果當時選擇去美國而不是留在英國的話,我會變得更像一個財務經理。現在情況完全變了,英國比我年輕的、還沒有退休的人需要在財務方面消耗更多的精力。英國現在已經變得和美國差不多了,但在我那個時候兩個國家還是有很大差別的。此外還有一些其它問題需要考慮,比如我到底希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美國長大。我並沒覺得美國不好,實際上我很喜歡美國。美國當下正處於一個陣痛期但它依然還是個好地方。我在美國有很多好朋友,也喜歡去那兒欣賞自然景觀和參觀環境優美的校園,但這些因素還不足以讓我下定決心定居美國。
劉偉:我覺得你的性格中有看起來矛盾的兩面,也許我的這種個人感受是錯的。在日常生活中,你喜歡再普通不過的東西,比如說你喜歡擁擠狹窄的街道。但是在科學研究中,我把你稱為一個極端的精英。例如,你對我說過,「科學不是民主;科學是由最好的科學家決定的」。這兩面看起來是矛盾的,你是怎麼調和它們的?或者說它們本來就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貝里:無論什麼背景的人都可以從事科學研究,都應該被鼓勵從事科學研究,研究科學的人越多越好。從這種意義上講,科學是民主的。但是在眾多人類活動例如體育或音樂中,人們總是尊重那些有所建樹的精英。在科學中也一樣,這是很自然的,但需要強調精英和精英主義是完全不同的。在其它方面,我喜歡的東西和別人並沒有不同。我喜歡烹飪,在接受你採訪之前還在想晚上該做什麼菜。我喜歡散步時欣賞風景,在沒有新冠的時候也偶爾坐在咖啡館裡觀察身邊的人或者和遇到的人交談。這些都很正常,所以我沒有感受到有任何你提到的矛盾。此外,我有相當一部分工作是發掘日常生活現象背後隱藏的抽象概念,這些現象很多是光學現象,例如彩虹和波光粼粼的海面等,我稱之為「見微知著」。
劉偉:你的科學偶像之一保羅·狄拉克 (Paul Dirac,量子力學奠基者之一)曾說過,自己是幾何型而非代數型的思考者。對於這一點,你剛開始的時候有些吃驚。我想知道你的思考方式。你是更偏代數型麼,儘管布里斯托大學很多人都是或者曾經是幾何型的?
貝里:剛開始的時候,我和其他很多年輕的理論物理學者一樣,都是偏代數型的。我現在依然做很長的計算,裡面有一頁又一頁的公式。當然有很多公式和代數型思維並不是一碼事,我還記得Louis Armstrong(爵士樂發展重要人物)的那句名言「你可以演奏眾多音符,但那不是音樂。」後來我逐漸意識到視覺的東西更自然一些,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受到了布里斯托大學偏重影象分析這一傳統的影響,我從同事那兒學到了很多,他們讓我意識到透過影象可以獲得更清晰的理解。如你所說,狄拉克說他自己是一個偏視覺的人,愛因斯坦也這麼說過,但是他們在自己發表的文章中並沒有插入任何圖片,這是非常有意思的。我相信他們說的話,也問了Graham Farmelo,他是一本很厚的《狄拉克傳》的作者。我問他「你看了狄拉克的文章以及他的檔案,有沒有發現一些圖片和計算被隱藏起來了?」Farmelo說他沒發現這種情況。 狄拉克還在布里斯托上學的時候,說自己最喜歡的課程之一就是工程製圖,那個時候的有些圖片最近也公開了。所以你知道,人們所說的和所做的並不一定完全吻合,無論是公開還是私下。狄拉克在自己的文章中雖然沒有插入圖片,但我相信他在大腦裡一定有清晰的物理影象。現在有很多軟體讓作圖變得容易很多。即使在有這些軟體之前,我也會用舊式的筆和蠟紙以及其它工具為自己的文章作圖。如今我們都更強烈地意識到視覺展示的價值。
但我們還沒有充分意識到聽覺展示的價值。我已經和偶爾的合作伙伴Pragya Shukla(印度理工學院物理與氣象學系教授)一道開展了相關方面的研究,我稱之為「聽覺數學」(Earmath),也就是用聲音來展示數學。我們既能看也能聽,兩者是非常不同的。我們的研究發現可以利用隨機矩陣的本徵值或者特徵多項式很容易地構造出一些此前從來沒有被聽到過的聲音。在現階段,我們僅僅是出於好奇從事這項研究工作,它的科學價值有待世人透過自己的眼睛或者耳朵來驗證。
劉偉:你對發散級數和漸進分析這些領域非常感興趣且做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我很難想象一個偏視覺化的人怎麼會對發散級數這個方向著迷。發散級數怎麼能被視覺化呢?
貝里:發散級數和一些哲學層面的考量高度相關,因為在描述不同層次物理間關聯的時候一定會涉及到發散級數。這樣的討論僅限於物理,我可不會討論用薛定諤方程解釋生命現象。當你從波動光學領域進入到幾何光學領域,或者是從量子物理領域進入到經典物理領域,你得到的相關的級數總是會發散。它們必須發散且這背後是有深層原因的,因為對不同層面物理的描述有著本質的不同。如果這些級數是收斂的,那就意味著量子和經典本質是等價的,相差的僅僅是一些諸如ℏ,ℏ2等等這樣的修正項。這當然是不可能的。關聯不同層次物理現象級數的極限必須是奇異的,而奇異的標誌就是級數必須發散。
關聯不同的領域需要數學,不同的關聯需要不同的數學,有時候這些數學是現成的而有些時候並不是。湍流可以理解為流體力學在粘度為零時的極限。但是這個極限是奇異的,如果你把粘度項直接設定成零,利用尤拉方程並不能得到湍流。當粘度越來越小的時候,粘性耗散會逐漸消失,但它分佈在一個分形 (fractal)的集合上。所以僅僅是簡單地寫一個粘度為零的方程,是不可能得到湍流的。當用漸進分析的視角考察不同理論的邊界區域時,會得到不同性質的科學詮釋,而湍流只是其中的一個特例。所以當你在描述不同層次的物理間關聯的時候,就一定會遇到這些必然發散的級數。
對於你的問題,我想指出的是發散級數里有很多可以被視覺化的東西。如果你把這些級數畫出來,首先它們是收斂的,然後會發散,其間的變化極為醒目。例如討論複平面內的穩定相位法,如果你把影象畫出來,就能得到更加清晰的結構,你會直接看到鞍點之間的關聯以及它們之間的斯托克斯線等等。
在幾何光學這個重要領域,奇點被稱為焦散線 (caustics),在焦散線的位置連線幾何光學和波動光學的級數必然是發散的。你知道焦散線學這門學科是非常視覺化的。當我們看遊樂場一些彎曲的鏡面,或汽車凸凹不平的閃亮金屬面,或金屬勺子的時候,會看到扭曲的反射影象,這樣的扭曲映象在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我最近發現要有效描述這些影象的扭曲以及它們的拓撲演化,焦散線至關重要。我的工作就是解釋我們看到的東西,這當然非常視覺化。如果要把這些現象及描述和更深層次的波動物理描述聯絡起來,就必然會涉及到發散級數,背後的原理是非常普遍的。
現在我們重新回到關於視覺化的問題。當我開始在物理學中有自己獨立想法的時候,研究的課題是準經典量子力學中類似的關聯。我很快發現準經典量子力學中的很多問題和光學中的問題是一樣的,而對於光學問題,一個明顯的優勢就是它們是視覺化的。總而言之,視覺化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用圖片來解釋數學關聯,另一個是詮釋你能用肉眼直接看到的東西,而發散級數屬於後者。
劉偉:所以你的思維偏幾何而不是代數?
貝里:不能這麼說。如果去看我最近發表的文章,你會發現其中既有代數運算又有物理影象。當我說某個方面不是更多的時候,並不意味著這個方面更少,我只是不知道怎麼比較它們。我可以和你分享一個關於斯托克斯的故事,故事的細節也許並不十分準確。斯托克斯是我的偶像之一,他是一個很嚴肅的人,相傳他有生之年只在別人面前笑出聲過一次。他為什麼會笑呢?在一次晚餐的時候,他旁邊坐著一個年輕的女子,這個女子問了個問題讓他忍俊不禁。在那個年代,晚餐後女士們會轉移到另外一個房間閒聊,男士則會留下來邊抽菸邊高談闊論。我不知道他們分別在說些什麼。所有的女士都圍著問斯托克斯問題的那個年輕的女子,問她到底對斯托克斯說了什麼能讓他開懷大笑。年輕的女子回答說「我問他是幹什麼的,他說他是搞數學的。我接著問他是更喜歡幾何還是代數,他覺得我這個問題很搞笑,就忍不住笑了。」
劉偉:我追蹤了一下你發表的文章,發現你很早就對拉曼在聲學和光學領域的工作感興趣。這個和你父親在印度呆過一段時間有關聯麼?除了拉曼的工作之外,據我所知你對印度飲食和印度文化也都非常感興趣。
貝里:這個和我父親沒有任何關聯,儘管他確實是在 1930 年代在印度服役過一段時間。當我開始讀博的時候,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就求助於我的導師Robert Dingle教授。他那個時候正在做一些關於發散級數的非常重要的工作,很久之後我也投入到這個領域。他給了我一些題目,讓我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能用上他發展出來的方法。我選擇了其中一個關於超聲波對光的衍射的題目,本質上講那就是一種波和另外一種波的相互作用。後來發現Dingle教授的數學方法對我研究的這個問題並沒有幫助,但沒關係,我還是順利完成了博士課題。在我選擇的這個研究領域,主要的文獻都來自於拉曼和他在印度班加羅爾的同事們。我讀博的時候已經結婚生子了,那個時候很窮,為了能掙點錢補貼家用,就當了聖安德魯斯大學理論物理系的圖書管理員。當有新的雜誌寄來的時候,我都會快速瀏覽一下。對於印度科學院院刊,我發現幾乎每一期都有一篇拉曼的文章。這就是我和拉曼之間的另一層關聯。很多年之後的1976年,我首次訪問了印度並聽說了拉曼傑出的外侄Pancharatnam(Pancharatnam 是拉曼妹妹的第三個兒子,他有兩個哥哥在物理學領域均頗有建樹,包括後面會提到的晶體物理學家 Ramaseshan。拉曼的哥哥有個兒子叫 S. Chandrasekhar,他和叔叔拉曼一樣獲得了諾貝爾獎,也是楊振寧先生和李政道先生在芝加哥大學時的老師)以及其他拉曼家族的成員。自此之後我和拉曼之間的關聯進一步加深了。總之我很早就對拉曼工作感興趣,這源自於我的博士課題,以及拉曼和他的同事例如奈斯(Nagendra Nath)在1930年代的一系列工作。
劉偉:在以前另外一個訪談中,你提到印度教中允許很多個神存在,這比只允許一個上帝存在的其它宗教要健康很多。有些人覺得現在物理學中的大統一理論(例如弦論)和單一上帝宗教從心理學上講是完全一致的。我可不可以從你對印度教的評論中推測你並不喜歡大統一理論?
貝里:我並沒有不喜歡大統一理論,它只是個名詞而已。在物理學中,所有的統一理論都是美妙的。發現一個能統一萬有引力和其它相互作用的理論將是一項巨大的科學突破。即使有這樣的理論,我也不會覺得那是物理學的終結,僅此而已。我沒有任何貶低的意思。我覺得大統一理論和印度教之間並沒有特別的關聯,不管是一個神還是我隨口說的很多神。我那次對印度教的評論並不是特別嚴肅,我自己也沒有信奉什麼宗教,至少沒有信奉任何有嚴密組織的宗教。我的那個評論實際上是說,如果有一天被逼無奈,非得選擇信奉一個宗教的話,那麼我就會選擇一個允許很多個神存在的宗教。當然這些都是假設,我從沒有認真考慮過這些問題,更沒有任何貶低大統一理論的意思。大統一理論僅僅只是一個名詞而已,不要把它當成無所不能的理論。
這裡面還有另外一層原因。我前面提到過,人類的智慧非常有限,不大可能會發展出所謂的萬物理論。即使有一天能得到這麼一個理論,我也不會覺得那是物理學的終結。就像安德森指出的那樣,我自己也從更廣的角度強調過這一點,那就是存在另外一種不同的根本性,即從舊的東西里面發掘出全新的東西。Ian McEwen的一本小說中有這麼一個故事:有一個弦論學者,被老婆發現一直盯著看另外一個女人,他於是信誓旦旦地說「不要擔心,親愛的,我能解釋這一切!」原則上講,你可能得到一個能囊括所有東西的理論,但是這個理論卻不能幫你解釋任意一個確切的東西,關於弦論學者的那個故事就是這一點的完美詮釋。狄拉克也說過他的方程能解釋所有化學現象,可實際上狄拉克方程卻對一個理論化學家理解一些確定分子的特性並沒有什麼具體幫助。這涉及到科學的不同層面:發現一些新的理論當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可是從已經發現的理論裡面發掘出一些全新的概念也具有同樣的重要性。關於這一點,Ian Percival有非常精闢的表述。他是我非常尊敬的物理學家,在我事業早期對我幫助極大,是他讓我領略到一個研究方向的重要性,後來我們稱該方向為量子混沌。Ian Percival說「理解方程的形式是一碼事,理解方程的解是另外一碼事。」這兩者都具有本質的意義,後者對我有非常深遠的影響。

圖 從左到右分別為採訪人國防科技大學劉偉博士、被採訪人邁克爾·貝里爵士、本文編譯潤色楊思佳
邁克爾·貝里爵士是英國布里斯托大學的理論物理學家,他一生有超過三分之二的時光是在布里斯托度過的。貝里爵士的研究集中於揭示不同層次物理理論(例如經典和量子物理,幾何和波動光學等等)之間的關聯。除了那些高度數學(多偏幾何)化的研究之外,他還非常熱衷於發掘彩虹、波光粼粼的海面、閃閃星光、天空中的偏振光、潮汐等日常生活現象背後深刻的概念,並稱之為見微知著。
劉偉博士分別於北京大學和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取得物理學本科和博士學位,目前任教於國防科技大學前沿交叉學科學院。劉偉博士主要研究米散射理論併發掘其和對稱、拓撲及奇點等原理和概念之間的隱秘關聯。
更多關於貝里爵士的資訊可以參見他的個人主頁:
https://michaelberryphysics.wordpress.com
撰稿 | 劉偉 編譯 | 楊思佳
編輯 | 呂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