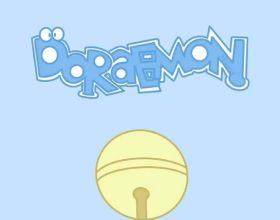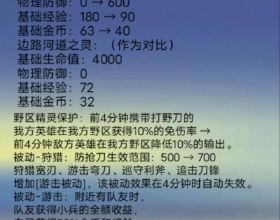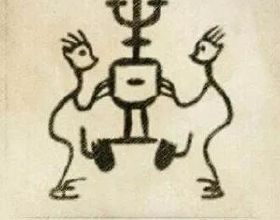李之儀:只願君心似我心
卜算子
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
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
此水幾時休?此恨何時已?
只願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
這是首以女性口吻所寫的相思之詞,作者卻並非女性,而是一個大男人。這首詞,是他寫給一個相好的歌妓的求愛詞。
從古至今,風流倜儻的才子都用優美的詩詞向某個心儀的女性求愛,這並不稀奇。稀奇的是,這是一位六十多歲,已經過了花甲之年的老人。而他所心儀的女子,則是位十多歲的青春美少女。
更稀奇的是,他們年齡相差五十多歲,在一起時卻絲毫沒有溝通障礙,甚至就像那些相濡以沫了若干年的老夫老妻一樣。
他們創造了一個愛情神話。
他認識她時,正好處在丟官、失妻兒的時候,是個無權無勢、多病多災,像根枯枝般的老人。而她認識他時,正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年輕美貌,追求者絡繹不絕。
他曾是蘇軾的幕僚,而她則是青樓的歌妓。
緣分是不可思議的。他們是那麼的名不當、戶不對。但看似完全不可能的兩個人,最終卻成為了宋代一段感人的愛情佳話。
他是李之儀,她叫楊姝。
李子儀就是在他對人生失去信心時,被愛神之箭射中的。他是北宋滄州無棣人,早年曾師從范仲淹之子範純仁,之後又任樞密院的編修官,最後又做了蘇軾的幕僚,與秦觀、黃庭堅關係很好。
李子儀曾經有過一段美好的婚姻,他的妻子胡文柔出身名門,通經史熟詩詞,文才絲毫不遜於他。
他們夫唱婦隨,琴瑟和鳴,是最令人羨慕的一對好夫妻。可這樣美好的婚姻,卻未能到白頭。胡文柔,那個賢良淑德的女子,在她58歲的那年,生病去世了。
李子儀悲傷不已,在《姑溪居士妻胡氏文柔墓誌銘》中寫道:“與餘伉儷四十年,胡氏上自六經,司馬氏史,及諸篡修,多所綜織。於修學則終一大藏。作小歌詞禪訟,皆有師法,而尤精於算數。”
文才武略,樣樣精通。可見,胡文柔的才華多麼了得。
可惜,她早早走了,留下年老體衰的李子儀成了孤家寡人。因為就在胡文柔去世的一年前,他們的兒子和女兒也相繼去世了。
一兩年之內,一下子失去三個至親,任誰都難以承受。
原本已經禍不單行,可命運像是要將他置於死地,將他什麼都剝奪。就在那時,他因為得罪了當朝宰相蔡京,被罷了官。
“倦臥終朝不捲簾,獨展《離騷》吊逐臣”,這,就是他當時的現狀。
從享受天倫之樂到孤家寡人,李子儀在兩年多的時間裡,體會到了人世間所有的痛苦和悲傷。原本就虛弱的身體,在遭受了這一連串的打擊後,更糟了。
他回到了老家,整天與田間的農夫、山間的樵夫聊天,度過那難熬的歲月。
那時的他,已經對一切都不抱希望了,他聽天由命,自生自滅。
是老天可憐他嗎?在將他所有的東西都搶走後,又送給他一段愛情、十個愛妻。或者,老天是想將他的人生清空,然後給他一段新的人生。
總之,因為遇到她,他的人生開始反轉。
李子儀遇到歌妓楊姝時,正好是他人生最低谷的時候,而那年,楊姝不過才十三四歲。
楊姝是安徽人,長相清秀美麗,雖然年齡小,但生活的磨礪,卻讓她過早地成熟了。她的彈奏技藝很高,凡是聽過她彈琴的,都會被她的琴聲打動。曾經,黃庭堅聽她彈過琴後,讚不絕口,特意寫下了一首詞:
好事近·太平州小妓楊姝彈琴送酒
一弄醒心絃,情在兩山斜疊。
彈到古人愁處,有真珠承睫。
使君來去本無心,休淚界紅頰。
自恨老來憎酒,負十分金葉。
這首詞除了讚美楊姝的琴聲感人肺腑外,還說她親自為他斟酒,無奈他不能喝,辜負了她的一番美意。
這還不夠,他又寫了一首《贈彈琴妓楊姝》的詞,送給她:
千古人心指下傳,楊姝煙月過年年。
不知心向誰邊切,彈盡松風欲斷絃。
“彈盡松風欲斷絃”,能將琴彈得這麼出神入化的,想必那時,也只有楊姝了吧。
能讓“蘇門四學士”之一的黃庭堅欣賞,足可見楊姝絕不是那種以色示人之人;而如此青春美貌的女子,能喜歡上年老體弱、無權無勢的李之儀,可見,她也不是那種攀龍附鳳之人。
他們之間的相遇,很浪漫,也很湊巧,全都緣於楊妹的琴聲。
那天,李之儀和往常一樣,在孤寂無聊中,去姑溪河畔徘徊,突然,他被河中畫舫裡傳來的琴聲所吸引,彈奏的正是他所熟悉的《履霜操》。
那是一首忠良訴說遭小人讒害後被貶的詞,被楊姝彈唱得悽悽楚楚,嗚咽哀鳴。
一個在河中的畫舫彈,一個在岸上聽,李之儀聽得淚水漣漣,瞬間想起了自己被貶之事。
這種感同身受,他已經很久沒有過了,曾經麻木的心,被一首曲子叫醒。而能將一首曲子彈得這麼催人淚下的,除了楊姝還會有誰?
李之儀雖然沒有見過楊姝,但聽黃庭堅說起過,而且還知道黃庭堅曾為她寫過詞。
他決定上畫舫會會楊姝,而當楊姝知道他是李之儀後,也熱情地接待了
他,併為他彈了一首曲子。
琴聲悠揚,如潺潺流水,又如風吹花落,林中鶯語
李之儀何曾聽過這麼美的琴聲?那不堪重負的心,瞬間就輕鬆了許多。忍不住,他以黃庭堅贈給楊姝的那首《好事近》的韻腳,和了一首:
相見兩無言,愁恨又還千疊。別有惱人深處,在懵騰雙睫。
七絃雖妙不須彈,惟願醉香頰。只愁近來情緒,似風前秋葉。
就一句“惟願醉香頰”,已經讓李之儀和楊姝全都緋紅了臉,兩個忘年之交的人,竟然越聊越投機,聊得李之儀忘了回家。
也許,在那時,李之儀已經喜歡上了這個年輕貌美、才藝雙絕的女子。於是,他又贈了一首《清平樂》給她:
殷勤仙友,勸我千杯酒。一曲《履霜》誰與奏?邂逅麻姑妙手。
坐來休嘆塵勞,相逢難似今朝。不待親移玉指,自然癢處都消。
仙女一樣的楊姝,一個勁地勸他喝酒,《履霜》這麼好的曲子,誰來彈奏好呢?幸好遇到了楊姝這仙手。
從這首詞就能看出,李之儀讚美女人還是很有一手的。在他的眼裡,楊姝那纖纖玉手,猶如那醫治百病的神藥。在她柔情撫慰下,他瞬間走出了罷官、喪子喪妻的陰影。
什麼才會有如此大的力量?當然是“愛”。只有“愛”,才能讓疲累和痛苦消散。
這次的相逢,竟然讓他們分開時,都有些依依不捨,眼神裡也有著說不出的情愫。
李之儀欣賞楊姝的琴藝,更羨慕她的青春活力。與她在一起,所有的悲傷都慢慢淡化了,曾經只想儘早隨妻兒而去,現在他有了莫名的求生慾望。
自此後,楊姝那裡,也成了李之儀常去的地方。他們不僅“以詩文自娛”,而且一起爬山玩水。李之儀身上的頑疾、疼痛在慢慢減輕,甚至好像一下子年輕了很多歲。
李之儀喜歡釣魚,一有時間,楊姝就陪他去小溪邊垂釣,他們過起了“一編一壺,放懷詩酒,觴詠終日”的日子。
相處久子,心也越靠越近。也許是楊姝過早進入青樓,比同齡女孩成熟很多的原因,他們雖然有著五十多歲的年齡差距,內心和精神卻很靠近。
真應了那句話,真正的愛情,是超越年齡、超越條件的。而也正是因為李之儀比楊姝大很多,經歷了更多的世間冷暖,所以才會珍惜他們在一起的美好時光。他寵她、疼她。讓她感受到了從別人那裡得不到的溫暖和尊重。而年輕的她,也給了他貼心的照顧,激情的生活。
他愛她,她也愛他。也許各方面差距太大,讓他們都不敢去想結果,所以誰都沒有點破。
不過,她的愛情,成了他的一劑藥。一劑能治癒他身體和精神傷痛的藥。他又恢復了讀書寫詞、吟詩作畫的生活。
他,變得越來越離不開她了。
那首有名的《卜算子。相思》就是在他和好友賀鑄去採石磯遊玩途中,突然思念起楊姝來,有了讓她嫁給他的想法。
這種想法,對於一個快七十的老人來說,有些可笑、荒唐,可對於沉浸在愛情裡的人來說,卻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於是,那首被後人反覆吟誦的詞就有了:
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
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
此水幾時休?此恨何時已?
只願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
她住在長江上游,他住在長江下游。雖然他們見不到,但喝著同一長江的水。長江的水在不眠不休、不停歇地流著,,他們之間的相思之情,離別之恨,也如那長江之水,永不停止。她希望他能和她一樣,鍾情於對方,這樣也就不會辜負他們之間的相思之情了。
這是李之儀以“她”的口吻,訴說著自己的相思之情。
想必,他在寫這首愛情宣言的時候,還是有所顧慮的,不然怎麼會以女性口吻來寫呢?不過,對於懂他的楊姝來說,這樣一首詞,已經足夠表達他的誠意了。
李之儀是浪漫的,曾經被歲月沉澱了的激情,在那時被楊姝徹底啟用。或許在寫完那首愛情宣言詞後,他還是有些忐忑的,怕被楊姝拒絕。沒想到,楊姝看了《卜算子。相思》後,感動不已,沒有絲毫猶豫就答應了。
也許,她一直在等著這一刻,等著他的表白。
兩個人像戀人一樣開始相處。這是李之儀愛情的重生,也是他生活的重生。李之儀按捺不住激動,又寫了一首詞:
謝池春
殘寒消盡,疏雨過、清明後。花徑斂餘紅,風沼縈新皺。乳燕穿庭戶,飛絮沾襟袖。正佳時仍晚晝,著人滋味,真個濃如酒。
頻移帶眼,空只恁厭厭瘦。不見又思量,見了還依舊,為問頻相見,何似長相守。天不老,人未偶,且將此恨,分付庭前柳。
冬天早已過去,春雨過後,清明很快也要過去了。在那花間的小路上,還有些許的落紅存在。微風吹過,池水泛起了漣漪。小燕子在庭前飛來飛去,那飄落的柳絮,落在了衣襟的袖子上。這是最好的時辰,是白天和黑夜不分的日子,在這樣的日子裡,生活就像醇酒一樣醉人。
他的腰帶在不停收縮,看著自己那被歲月折磨得越來越消瘦的臉,很是慌張。見不到她時很想她,見到她時,又會想到即將分離,很是難受。這沒完沒了的相思,折磨著他。為什麼要見了又分,分了又見?為什麼不能一直相守?天無情,天不老。人有情卻還是落得孤孤單單。這樣的相思,又有誰能瞭解?
“罷了,罷了,就讓庭前的柳樹,為我們的愛情做個見證吧!”
如果說那首《卜算子。相思》是首求愛詞的話,那麼,這首《謝池春》就是在求婚了。
前面一大堆鋪墊,描述了愛情讓他幸福得忘記了晝夜的轉換,愛情讓那一花一葉都生動漂亮。不過,他雖然每天活在醉人的日子裡,但看著自己日漸消瘦的臉,還是有些悵惘,那都是因為想她啊!
愛情會讓人變得貪得無厭,相愛了,還嫌不夠,還要每分每秒在一起。
即使年近七旬的李之儀,也是如此。
她接受了他的求婚,和這個將近七十歲的老人結了婚,住在了一起,一分一秒都不分開。他們的婚姻是幸福的,1107年,李之儀七十歲的時候,楊姝為他生下了一個兒子。
還有什麼比老來得子更讓他高心的呢?何況他的兒子和女兒已經過世。
李之儀視這兒子為珍寶,對愛妻楊姝更是疼愛,兩個人一個讀書填詞,個相夫教子,溫馨又快樂。
也許,楊姝和兒子的出生,給他帶來了好運。也就在那年,朝廷恩典,他的兒子得到了蔭封。
任何朝代,都有見不得別人好的人。那個曾嫉妒蘇軾的郭功甫,自知奈何不了蘇軾,便將仇記在了和蘇軾關係甚好的李之儀身上。他教唆李之儀家鄉的一個地主,狀告李之儀,稱李之儀的兒子是他的,還稱李之儀是冒領朝廷恩典。
朝廷並沒有做任何調查,便將李之儀的官籍削了,就連楊姝也受到了杖刑。郭功甫為此還幸災樂禍地寫了一首打油詩,嘲笑他們:
七十餘歲老朝郎,曾向元祜說文章。
如今白首歸田後,卻與楊姝洗杖瘡。
曾經做官著文的七十歲老人,如今卻只能回家,給楊姝洗身上的杖瘡了。
這種汙辱性的話,誰能忍受?能寫出這種打油詩的郭功甫,人品真是太差了。
不過,面對如此汙辱,經歷過人生起伏的李之儀,似乎並不放在心上。
確實,相比他之前的失官、失妻、失兒女,這點點痛苦算得了什麼?此時的他有兒子,也有愛妻,他們其樂融融,已經很幸福了,做不做官,又能怎樣?
為了表達給以了他這一切的楊姝的感激,他又寫了一首詞:
浣溪沙·為楊姝作
玉室全堂不動塵,林梢綠遍已無春,清和佳思一番新。
道骨仙風雲外侶,煙鬟霧鬢月邊人,何妨沉醉到黃昏。
“道骨仙風雲外侶”,“何妨沉醉到黃昏”。他和楊姝,過著神仙伴侶般的生活,即使每天從白天睡到黃昏,也沒人管得著。
這就是不為官,過閒散平淡生活的幸福。知足才能常樂!
這首詞既是對郭功甫嘲笑的回應,也說明他對這種生活的滿足。
雖然李之儀不介意削官,但是在若干年後,他的外甥還是為他申了冤,昭了雪。他的官職隨即也恢復了。自此,李之儀調去唐州,做了朝議大夫,而楊姝也帶著兒子前往,一家人很是幸福。不管是福是禍,來了就坦然接受,這也許正是他們幸福生活的秘訣。
79歲時,李之儀病逝。而他和楊姝之間的忘年之戀,也成了美談,被後人傳誦、敬仰。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關注遙山書雁,帶您領略文化的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