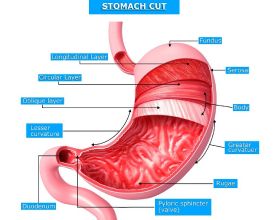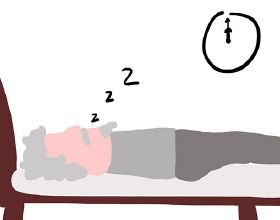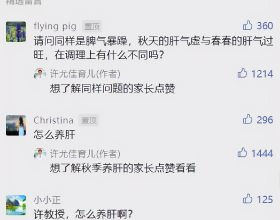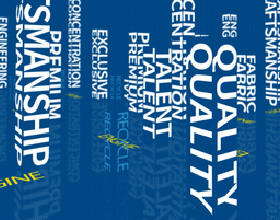我的過年記憶
人們對開心的程度、對獲得幸福的程度,都以像“過年”一樣好來形容。這種對年的期盼和重視的感情,在小時候尤為強烈。
圖片來自網路,如有侵權,請聯絡刪除
“小孩小孩你別饞,過了臘八就是年……”,家鄉的農村裡也有“吃了臘八飯,就把年來辦”的說法。我記得在小時候,從臘八節開始,年意就開始漸漸濃了。
我對於臘八飯的記憶不是太深刻,現在看書上說臘八那天要搞七種雜糧再配上大棗,熬成甜甜的臘八粥。但在我的記憶裡,小時候臘八節那天我家吃的並不是人們現在吃的這種臘八粥。或許是農村的家鄉沒有那麼多講究,又或是我家裡沒人知道該怎麼弄吧,我彷彿記得好像吃的是菜粥,還是鹹的,裡面還有菜葉和粉絲的那種,反正和平時的飯菜都差不多,所以印象也不是多深刻。
圖片來自網路,如有侵權,請聯絡刪除
但“臘八,扎耳朵眼子不得發”這句話我是有深刻印象的,說的是臘八節這天如果扎耳朵眼,不會發炎。記憶中的故鄉,有許多小女孩大姑娘,為了能在過年時戴上漂亮的耳朵墜,幾乎都選在臘八節前後幾天扎耳朵眼。扎耳眼的場景我沒親眼所見,據說是由一個有經驗的年長女性,用兩顆綠豆夾住要扎耳眼那人的耳垂,然後用手指捏住綠豆慢慢地加勁揉,直槓到兩顆綠豆間的耳垂肉慢慢地被碾成一層薄薄的皮,然後用一根針快速穿過,再留一根線頭在肉裡,過幾日去掉線頭,一個耳眼就成了。說是不會發炎,但我卻經常看到很多人的耳朵一個冬天都沒好,加上凍傷甚至還流膿流血,卻依然有這麼多擁有愛美之心的人前赴後繼,便讓我真心佩服這些大小女人們的勇敢。好在這些人中間沒有我的姐姐和妹妹,在我爸鞋底的威脅下,她們是不敢去的。不過一到這時候我卻知道,臘八節到了,馬上就要過年了,雖然這個“馬上”還那麼的讓人望眼欲穿。
年前的高潮,是從祭灶節開始的,就是現在很多人說的小年,這個節日一般都是在臘月二十三或者是臘月二十四過。我們村是個雜姓莊,和周圍很多村子只有一個姓的情況不一樣,雖然只有40幾戶人家,但張王李鄭徐、黃段朱劉童各姓齊全,外村人笑稱這裡是“鬼子國”,說莊子雖然不大,倒是姓啥的都有。姓氏不同風俗也就略有差異,於是就有的人家過二十四,有的人家過二十三。
我家是過二十四的。小時候每當我被臘月二十三的鞭炮聲撩撥得上躥下跳時,我爸總是鄭重其事地告訴我們:“我們家不過二十三哦,我們家從祖上就是過二十四的,人不能忘本,到什麼時候都不能變……”
爸說民間過祭灶有“君三民四”的典故,說古時候皇宮裡和官宦人家都是臘月二十三過祭灶,老百姓都是臘月二十四過。慢慢地後來有很多不是官宦人家的人也改了過節時間跟在後面和,這才有那麼多人二十三過祭灶。但俺家不能改,俺家這是祖上傳下來的規矩不能變,該是什麼樣就是什麼樣。我於是也就從那時知道,我們家祖上從來也就沒出過什麼達官顯貴的人,都是平頭老百姓。雖然有點為沒有顯赫背景吹牛而遺憾,也知道晚一天過節不會有什麼損失,但這多熬出來的一天,在兒時感覺竟是如此的漫長和艱難。
圖片來自網路,如有侵權,請聯絡刪除
祭灶節前趕上逢集,我爸會提前去集上買回一張老灶爺像,是那種民間用木板刻好成批刷印的版畫,紅紅綠綠的,上面印著慈眉善目、白乾白淨的灶王爺和灶王奶奶。畫像的上面多數是簡單的農曆,灶王爺和灶王奶奶兩邊一般都有“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二十四日去,初一五更來”等對聯,畫像的底部則是搖錢樹、聚寶盆等人們心中期望的寶貝。喜氣洋洋地請回家中,貼在土灶燒火口旁的外側牆上。買上用山芋熬成的糖瓜,再烙上裡面放著糖的“糖火燒”,祭灶時恭恭敬敬地供奉在老灶爺的面前。期望能讓老灶爺吃甜了嘴,然後在上天和老天爺彙報工作時,講一講這一家人的好話,以保佑這個家庭來年的風調雨順和老少平安。
這一天家裡一般是吃餃子,祭灶一般都是在準備吃飯前進行。先要洗手燒上一炷香,敬奉在老灶爺面前裝著大米代替香爐的碗或杯子裡,再把糖瓜、糖火燒、餃子等好吃的物品虔誠地擺上,然後放鞭炮,再從鍋裡舀點餃子湯淋在畫像前面的鍋門口,再磕幾個頭,講幾句請老灶爺保佑的話,就算完成祭灶了。然後一家人再開始熱熱騰騰地吃飯。
圖片來自網路,如有侵權,請聯絡刪除
圖片來自網路,如有侵權,請聯絡刪除
祭灶節後的幾天,就開始真正的準備過年了。首先是大掃除,裡裡外外地把家裡該洗的洗,該擦的擦,該掃的掃。愛乾淨的姐姐平時只要在家,總會把家裡收拾的利利郎朗。被子疊得整整齊齊,地掃得乾乾淨淨,甚至連堂屋條几上擺的空酒瓶都擦的一塵不染。這時候更是充分發揮了她的完美優勢,把一個農家小院收拾得非常舒適養眼。姐姐愛乾淨的習慣影響了我多年後的生活,以至於到現在為止,無論是寫材料還是做方案,我都非要在乾乾淨淨的環境裡才能舒心暢意的把這些事情做完。
過年要吃的菜這時候也開始買了,買魚,割肉,油鹽醬醋等等,都要在這幾天裡陸續備齊。老家用“慌得跟年三十稱不著鹽似的”這句土話來形容人的忙亂,也更顯出過年要備齊必要物品的重要性。這事由老爸操辦,幾乎每一個逢集的集市上都有他的身影,大多時候也會把我們幾個小孩帶在身邊去逛一逛,給我們買點零食小吃什麼的,讓我們解解饞。媽在我們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老爸在農村一個人帶著他的三個“小螞蚱”,渡過的每一年,每一天,都浸透著他的幸福和辛酸……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我姊妹三人也算爭氣,學習搞好的同時,在同齡人還在娘懷裡撒嬌時,我們就已經能夠在洗衣、做飯、喂牛等事情上獨擋一面。
家鄉的農村裡,年前都要蒸很多的發麵饃,就是城裡人說的饅頭。但我們老家那裡把這種長條形狀的饅頭叫做卷子,團的圓圓形狀的才叫饅頭。一蒸都要蒸很多,夠一個過年期間吃的量。還會蒸很多的包子,一般都是蘿蔔粉絲餡的。蒸好後晾在一個大匾子裡,每天吃飯時需要多少再拿出來熘一下,有時候都能吃到過罷年開春。到最後饃皮因為乾燥都是炸開的,一副齜牙咧嘴的模樣,成了不得不吃的老大難。蒸包子的情景多年難忘,我爸拽柴火燒火,我姐洗菜調餡,我和麵,我妹當個小跑腿,全家齊上陣,蒸出了一籠又一籠的包子、饅頭,蒸出了一幅又一幅熱氣騰騰、用心生活的幸福畫面。
圖片來自網路,如有侵權,請聯絡刪除
圖片來自網路,如有侵權,請聯絡刪除
終於等到大年三十,這一天是非常的繁忙。門對子要中午之前貼好,這是我爸早飯後第一重視的工作。每年家裡的春聯都是他自己親自寫,再遇到村裡有人拿著紅紙登門請他幫忙,這事就能差不多佔掉他大半個上午時間。堂屋、廚房的門上貼的是春聯,我清晰地記得有一年家裡的春聯寫的是“春風吹大地綠水長流,瑞氣滿神州青山不老”,每年春聯的內容都不一樣,但類似此類正能量的吉利話,都可以寫上。爸在村子裡算是個有文化的人,當過夜校老師。毛筆一拿,邊上再有幾個人誇他字寫得好,那就能連燒年飯的事都忘了,一氣的洋洋灑灑、神采飛揚。他寫我貼,門前大樹上貼上“抬頭見喜”,糧囤上貼上“斗大元寶”,板車上貼上“日行千里”,櫃子上貼上“黃金萬兩”,牛槽上貼上“人勤春早”,床頭上貼上“身體健康”,小福字到處貼,只貼得滿目紅色,喜慶滿堂。
圖片來自網路,如有侵權,請聯絡刪除
圖片來自網路,如有侵權,請聯絡刪除
圖片來自網路,如有侵權,請聯絡刪除
家鄉的風俗是年三十那天不殺雞,說殺雞就是殺當家的,因此家家要吃的雞都是提前殺好。年飯都是中午吃,不像現在城裡,都弄到晚上。那年月的年飯有雞魚肉蛋就很好了,倒沒有太高的要求。但菜盤子的數量要足,再節儉的家庭這一天都要滿盤子滿碗地做一大桌子菜。菜的數量多數字也要對,單數和不吉利的數字不能上,哪怕再補個鹹菜,也要湊個吉利數。先燒好的菜要先放在大土灶的後鍋裡熱上,到吃飯的時候再一道端出來,為的是怕提前做好的菜會涼。這頓飯的菜做多了也不怕剩,剩是年年有餘,有的家庭還故意讓小孩子剩點飯,就是為了要討一個新春如意的吉祥。
飯前要洗手燒香,堂屋的條几上,堂屋門口的東牆和廚房裡都要各敬一柱土香,說是分別敬老菩薩、老天爺和老灶爺的。然後放炮。全家按座次坐上桌。每年的這時候,家裡都會給過世的母親擺份碗筷,留個座位,彷彿她就坐在我們身旁。這時候忽然就想娘想的厲害,幾個小娃都強忍淚水望著空座,把自己喜歡吃的菜不斷往那隻空著的碗裡扒,嘴裡喊著“俺媽吃飯”,眼淚卻不敢往下淌。老家的風俗是過年不許哭,怕觸了黴頭,哪怕有一年我放炮炸了手都硬是沒敢掉一滴眼淚,這時候更怕引發一家人的情緒低落,所以姊妹三人雖然年齡都不大,倒個個都是一副堅強的模樣。爸說:“你們都吃吧,我們要歡歡喜喜過個年,你們平時的一舉一動,你媽都看著呢,所以你們都要爭氣,繼續加油,要化悲痛為力量……”
大人喝白酒,三個小孩喝汽酒。那是一種類似於現在橙味汽水的飲料,不含酒精,用綠色玻璃瓶子裝的,乍一看好像是啤酒,深受我們三個小孩的喜愛。飯後和麵包餃子,一陣叮叮噹噹中,天就慢慢黑了下來。熱騰騰的餃子裡每年都會包一個硬幣或者包一塊糖,爸說誰吃到了誰就是新一年裡最有福氣的人,於是我們便都想靠多吃來增加成為最有福氣人的機會。村裡吃飯早的家裡的小孩,早早地就打著燈籠出來呼朋喚友了,我和妹妹便迫不及待的吃完餃子加入到這個行列中,留下懂事的姐姐在家刷盤子洗碗。
我記不清是什麼原因,在兒時的農村,每年的大年三十晚上,村裡的孩子們都要打著燈籠出來玩的。新買的玻璃紙燈籠好漂亮啊,用幹了的高粱梢——我們土話叫做秫挺子的那種秸稈編制的燈籠框架,能透過彎成U型鐵絲的主骨架拿出來裝回去,以方便點蠟燭。框架上蒙著清晰透亮的玻璃紙,上面畫著蘭花、魚蟲等精美的圖案,襯著紅蠟燭點燃的火苗,放射著動人的光芒。一個又一個的小朋友打著一盞又一盞紅光閃閃的燈籠,慢慢匯聚成一個歡樂的燈火海洋,一邊唱著“打個燈臺亮燈臺”,一邊圍著村莊遊逛,為這個平原小村的夜色,增添了一份喜慶的光亮。
孩子的天性是頑皮的,間或就有些年齡較大的孩子,逗那些年齡小的孩子。大家正打著燈籠唱,他忽然來一句“咦,你燈籠底下怎麼有個蟲子?!”小小孩忙不迭地翻過來看,結果“蓬”地一聲就把燈籠燒著了,接著引來的便是小小孩的嚎啕大哭,和聞訊而至的小小孩媽媽惡聲浪氣的大罵,聲震全村,甚至都追到大小孩家的門上……
有一年我忽然也抽風似的來了這麼一出,結果哭聲招來了另一個小小孩的媽媽。嬸子一句話也沒罵我,一邊給孩子擦眼淚一邊說:
“孩不哭哈,小陽子是跟你玩的……”
“他起小就沒媽可憐哈……”
“俺不生他的氣好不好……
一邊拉著她的孩子漸行漸遠。
善良的嬸子用行動給我上了一課,讓我時刻記得在未來的生活中,要寬以待人,心存善良……
這一夜可以遲睡,聽爸天南地北地講古。後來家裡買了電視機後就更容易堅持住,春晚結束許久了都還能不睡。爸說老話講,年三十睡得越晚、年初一起得越早的人越有出息,我們於是便努力去做一個有出息的人。
年三十晚十二點是老灶爺回家的時刻,要燒香放炮磕頭迎接。接灶要搶頭時,誰家要是能在剛到十二點時第一個響起鞭炮,這家人將是新一年裡運氣最好的人。每年這個時刻,我爸都如臨大敵,一邊看著手錶,一邊還不放心地和電視機對著時間,大呼小叫的,彷彿在指揮遼瀋戰役。我則拿著一根香火,兜裡再備一盒火柴,早早地站在掛著鞭炮的大樹下,等待著爸爸的命令。遠遠地附近的村莊裡接二連三地響起了鞭炮聲,村子裡一部分沉不住氣的人家也都跟著點著了火,我和妹妹就裂開嘴巴在那笑:“哈哈,時間沒到,他那不算……”
我家每年基本上都是第一個在新年響起鞭炮的,我的經驗是年三十晚十一點五十九分後數三十個數再點火,算上過程和藥引燃燒的時間,剛好在十二點整炸響。每年此刻心裡都會因此緊張而興奮地咚咚直跳,好在一直從未失手,都能在關鍵時刻,準點炸響。
未炸的鞭炮是農村小孩最稀罕的玩藝,每年我都能撿一小堆。閒來無事時用香火單個點響嚇雞也行,掰開兩個炮身點其中一個火藥讓它們相互呲花也行,把火藥倒出來裝進圓珠筆殼子裡做“火箭”也行,甚至還把一個散炮插在牛糞裡點著再喊一個小孩去看……
總之把它們都當成寶貝。
圖片來自網路,如有侵權,請聯絡刪除
有一年下大雪接灶,炮聲一停,我和小妹也不管要給老灶爺磕頭了,一頭就扎進雪窩裡去撿未炸的散炮,怕的是雪水融潮了火藥。炮撿完後再忙著去小雞嘬米似的磕頭,歡迎老灶爺回家過年。估計如果真有老灶爺來家的話,也會被這場景逗得哈哈大笑。
年初一早上不興叫人起床。在我家還傳承了個優良傳統,就是作為晚輩要在老人起床前燒一碗紅糖饊子荷包蛋,端到床前給他吃,並美其名曰為“光腚茶”,以示孝道。小孩子們這天會穿上新衣服,然後成群結伴地去村子裡挨家挨戶地討要零食。我估計最初先輩們是讓孩子們挨家挨戶地去給村人拜年,只是傳著傳著,一代代孩子們把拜年的話忘了,就只記得要東西了。這時候家家戶戶都會拿出瓜子花生糖果等,塞滿孩子的口袋。記憶裡很小的時候我還用褂襟子兜過瓜子花生,為的是能讓別人多放點。後來慢慢長大後,總覺得有點像要飯的,再加上要陪爸爸回他的老家,就再也沒去過。
初一回爸爸的老家上祖墳。初二一般走親戚。初三一早送年。初四為避“戳事”不出門。初五要捏蜈蚣嘴、初七捏七仙女嘴什麼的,反正就是找個藉口吃頓餃子……
記憶裡後面的這些天內多數是走親戚的時間較多,一般在這個時候能吃到焦葉子等零食。焦葉子是用山芋面做好的面葉粘上芝麻下油鍋炸成,有的地方叫麻葉子,有甜的和鹹的兩種,香脆可口,回味無窮。我最喜歡吃的是甜焦葉子,聽說是面葉在外面凍過後再進油鍋炸的,色澤金紅,泡起來脆脆的,比現在大禮包裡的米餅什麼的好吃多了。原本是皖北農村最家常的零食,但我家沒娘做,我爸也不會弄,於是我便不能經常吃到。
圖片來自網路,如有侵權,請聯絡刪除
初七以後年的氛圍明顯淡了不少,許多家庭在不來親戚客人的時候,都忙著解決剩菜剩饃。一直到正月十五再來個小高潮,做一頓好飯,晚上再吃一頓圓宵,放一點菸花,這個年就算過去了。雖然還有人說正月裡面都是年,但人們都開始真正收心,迴歸日常,該幹嗎幹嗎了。
姐姐出嫁後,過年怕孃家孤悽,怕老爸和弟妹在農村受苦,於是便把我們一家都接到城裡她的小家過年。姐夫親如兄長,多年來對岳父賽過兒,對弟妹關愛有加,從未有過半點不悅之色,那聲“大哥”是我們從心底裡喊出來的。從他們28平米的小家到兩室一廳、三房兩廳,到今天上下三層空間的複式樓,五易其居,處處都留下我們一家人團圓相聚、歡慶過年的快樂場景。
我和妹妹慢慢地長大成家,我爸也慢慢地從一個熱血漢子變成兒女們口中的“老豁牙”,但三家子和老爸一起,仍然每年都盡力在一起過年。其中最多的地方依然是在姐姐家,偶爾也分別在我和妹妹的城市團聚。但無論是到了哪裡,廚房裡最忙的永遠是我的姐姐,她心疼老爸、心疼弟弟和妹妹,早已成為一個下意識的習慣。姐姐家是我們全家精神的歸屬地和情感的港灣,後來姐姐乾脆每年都把婆家孃家的親人接到一起,團聚過年,至今已近三十年。
我和我姐我妹做年飯
姐姐的孃家婆家親人一起過年
小時候喜歡過年,現在也喜歡過年。小時候過年盼的是美食與新衣,現在更在乎過年時的親情交融和心靈放鬆。誰說年味不濃,那是缺少經營。我喜歡這血濃於水的親情,這是我修生養息的港灣,我喜歡這吉祥喜慶的節日,這是我精神動力的源泉。我願這份親情,伴隨我整個家庭,長存天地間。我爸的幾個“小螞蚱”也會一直記得他的嘮叨,直到永遠。
2022年2月10日於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