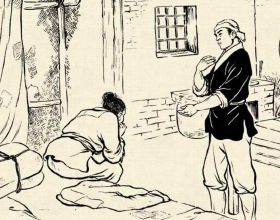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鄉。我的故鄉,在麻陽縣巖門鎮白泥田村一個名叫高坡上的小地方。
說高坡上是個小地方,是因為那裡只有十幾戶人家、五六十口人,在地圖上根本找不到它的位置。村民原本為漢族,上世紀80年代改為少數民族——苗族,且都姓張,同根同祖。
但高坡上又是一個空氣清新、林木豐茂、鳥語蔥蘢、四時花香的好地方。它距中國最美麗的小城鳳凰古鎮只有十里之遙。站在高坡上山頂眺望,鳳凰沱江宛如一條綵帶蜿蜒東去;巍峨的南長城逶迤起伏、氣勢磅礴、雄偉壯觀;山下不遠處的村寨炊煙裊裊,田園風光盡收眼底,江山如畫,美不勝收,令人心曠神怡。
故鄉一直是我魂牽夢縈的心靈之地,那兒有我童年的美好回憶。雖然1968年春天,我響應祖國的號召應徵入伍,離開了故鄉高坡上,但我入伍前,在高坡上整整生活了18個春秋,不僅熟悉那裡的房屋、田疇、樹林、山坡、小溪,而且對她產生了永遠難以忘懷和割捨不掉的情感。
如今,也許是人老了喜歡懷舊的緣故,那裡的山,那裡的水,那裡的人,那裡一切的一切,無時無刻都縈繞在我的夢中……
高坡上,除了山還是山,橫的是山,豎的是山,山靠著山,山連著山。開門就見山,出門就爬坡,由此而得名。
村莊的房屋依山勢而建,多為土磚瓦房,也有苗族特色的吊腳樓。房屋周圍,種植慄樹、杏樹、棗樹、椿樹、楓樹和楠竹,成了鳥兒們的樂園。從早到晚,成群的鳥雀在樹上飛來飛去、鳴叫不停。
屋前有一片碧綠的楠竹,高大挺拔,生機勃發。每到春雨過後,春筍競相破土而出,露出毛茸茸的腦袋,幾天工夫,就會身披黑色“鎧甲”,壯壯實實。再過半個月,黑色的面板一層層地脫落,逐漸長成高大挺拔的翠竹。
村莊周圍,還有一片片蔥蘢翠綠的松樹林,粗壯雄健,傲岸挺拔,密密匝匝連成一片,宛如一塊巨大的墨綠色翡翠,是我兒時玩耍的天堂,給了我童年極大的樂趣。
一陣風來,捲起陣陣松濤,時而如琴聲合奏、悠悠揚揚,時而如百鳥爭鳴、鶯歌燕舞,時而如萬馬奔騰、紅塵滾滾,時而如雲霧翻騰、地動山揺,時而如春雷霹靂、峰谷掠過,時而如波濤洶湧、驚濤拍岸,時而如涓涓溪流,叮咚歡歌……
聆聽著這百聽不厭的天籟之音,如同享受一個龐大的交響樂團演奏著高山、流水、林海的壯美華章,耐人尋味。
我凝視著松林,忘卻了砍柴、扒松毛、撿樅菇,可以在這裡呆呆地坐上大半天。這是一個絕對幽靜又很讓人享受的地方。我感悟其中,讚美松樹的常青和堅毅,讚美生命的真諦和堅定的人生。
有時候,我與小夥伴們來了興致,就在松林裡學著解放軍搞埋伏,打游擊,跟“敵人”周旋。每個人頭戴松枝做成的綠色草帽,手裡握著自制的小木槍,神氣活現地弓著腰,在松林裡往來穿梭,行蹤詭秘,不斷髮出“吧吧吧”的叫喊聲,弄得松毛沙沙,雀驚鳥飛。玩累了,往鋪滿松毛的地上一躺,一股淡淡的清香沁人心脾,那份愜意勁啊,別提有多爽!
屋門前的山腳下,還有一條小溪,一年四季流水潺潺,如同九天仙女的一根玉帶飄落在兩山之間的山腳下。
山區不像平原,水不是汪洋澤國。山有山澗,山澗有水流出,所以,水是山的兒女。這裡一座山,那裡一座山,漸漸地就匯聚成了小溪。小溪的水不像平原的水,那麼溫柔平靜,而是比較調皮,也琢磨不透。有的溪流涓涓,叮咚有聲;有的飛流直下,洶湧澎湃;有的清澈見底,常見魚兒遊動;有的碧波粼粼,深不可測。
每到盛夏,我和小夥伴成群結隊來到小溪裡戲水、洗澡、游泳、捉魚、撈蝦、抓螃蟹,其樂無窮。但母親總是不讓我下河玩水。可孩子終歸是孩子,一到小溪裡,我們就撲通、撲通跳下水去洗澡,打戲水仗,玩了個痛快。
有一回,我和幾個小夥伴一起跳到深水裡游泳,差點淹死,被兩個同伴救了上來。這個差點要了我小命的小溪,我卻非常喜愛。因為它很清澈,映著藍天白雲,映著周圍的青山,讓我有一種致命的誘惑。
房前屋後還有層層大小不一、錯落有致的梯田。順著石塊鋪成的山間小路,邊走邊俯視四周的梯田,你不能不感嘆這裡世世代代勞動人民的勤勞與智慧,以及大自然給人類的恩賜。
只見層層梯田拾級而上,彎彎曲曲,巧奪天工;層層梯田順山勢而造,用石塊砌成的田埂,坡面垂直平平整整,一絲不苟;梯田與梯田首尾相連,層層依偎,大小不一,高低錯落,春如根根銀帶,夏如滾滾綠波,秋如燦燦金浪,宛如一個個美妙的五線符,湊出一曲曲美麗動聽的田園曲……
連片的梯田在冬春季節,水田在陽光下金光閃閃。清風起處,微瀾清漪,青山碧樹,藍天白雲,倒映成趣。尤其是冬天的夜晚,月明星稀,寒光照水,碧波如鏡,樸素迷離之中給人以無限遐想。
高坡上雖然山清水秀,風景如畫,但在我兒時的記憶裡,它卻是一個十分貧窮落後的地方。那裡山高石頭多,農民們在狹窄的山坡上種瓜種豆,連一尺見方的泥土都不肯放過,統統被挖成狹小的田地。
山上的農民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地在這貧瘠的田地裡舉著牛鞭:“號——起,號——起”地趕著老牛犁田耕地。有的田地,三五步便到頭,半站在懸崖邊,既不能進,也不能退。於是,人們只得從泥土裡提起犁耙,使勁地往後拉,身子後坐,幾乎懸空在山崖外。
由於山高坡陡,讓人出行十分不便和艱難。記得小時候,行走在高坡上的山路上,我看著小夥伴在對面山上放牛、砍柴,或姑娘在對面山腰間向你招手,明明路就在腳下,但要會面卻要繞過九曲十八彎,走上半天,還不如直接喊話或對山歌來得及時。於是,如有同齡夥伴在山對面砍柴、放牛,大家都是用喊話、對歌的方式來交流。青年男女之間的隱私交誼,也是用對山歌的方式來互唱,互贊,互戀。
所以,大山裡的人,從小就生成了大嗓門。如今在家裡,妻子總是責備我說話嗓門大,可我總是改不了。因為山裡的人從小就養成了對山唱歌和對山喊話的習慣。在部隊軍營裡,嗓門大說明你聲音宏亮,有軍人氣概。可是,在地方機關,大嗓門就成了噪音,甚至會有人說你缺乏修養。所以,在地方上工作,我說話特別注意,從不放開嗓門說話。但在家裡,我就不會刻意去壓低聲音了。如果這樣,那就不是從湘西大山裡走出來的我。
由於高坡上山高坡陡,水成了山裡人生存的唯一源泉。在我的印象中,全村只有兩口水井,井壁四周用石塊砌成很堅韌,百年不塌。井壁上還長了很多青苔,井水是從山間岩石縫裡溢位來的。那源源不絕的泉眼,噴湧出清澈而衛生的水源,從未受到汙染,比今天城裡人喝的礦泉水還礦泉水,不知孕育了多少代人,為人們的生命補充了水分。水井裡長年漂浮著一把竹瓢,供路人舀水喝。這種山泉甘甜可口,富含礦物質,喝上幾口山泉水,既可解渴防暑,又能補水健身。尤其是夏天,井水很清凉,不少人勞作之餘,都要打桶水來飲個痛快。
春天,雨水特別多,雨水把水井灌得滿滿的。即使人們不停地挑水,泉眼與雨水很快就會補上去。可是,雨水掉進井裡,使得井水更加渾濁,一些蟾蜍和青蛙不知天高地厚,跳下井裡游來游去……
然而,遇到乾旱年份,泉眼冒水緩慢,往往供不應求。各家各戶為當天能飲到井水,天剛麻麻亮,就來到水井邊,先用小竹瓢舀水,一瓢一瓢盛在大桶裡。裝滿一桶水,不知道小瓢要在井裡上下舀多少個來回。有些人一夜未閤眼,守在井邊,目的是為了打兩桶水。雖然打水困難,但為了飲水,也只能無可奈何地等待。
如果遇上大旱,水井榦枯,只能到山下小溪裡去取水。平時洗菜洗衣是屋背後一口人畜合用的山塘水,汙泥穢垢,水質渾濁。所以,那裡的男女老少沒有每天洗澡的習慣,有的人一個冬天只洗一個澡。
由於天旱缺水,加之山區品種不優,糧食產量很低。但生於斯,長於斯的祖祖輩輩,始終堅持不懈地耕耘,用自己辛勤的雙手和滴滴汗水換回微薄的希望。
俗話說: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在別的地方,也許灑下的是一滴滴汗水,收穫的是一擔擔糧食,但在高坡上,人們灑下的是滴滴汗水,甚至是血水,收穫的不一定是糧食,可能是淚水。
記得有一年,禾苖、高粱、包穀泛綠伸枝,抽穗揚花了,父親那汗津津的臉上,終於綻露出了豐收的笑容。然而,連續數十天不下雨,原本田地裡綠油油的禾苗、高粱、包穀、小米枯黃了,變成了乾草。我那年近五旬的父親,站在田邊看著枯萎的禾苗在烈日下漸漸乾死,皺起眉頭,滿臉苦愁,嘆著氣:“看來,老天爺又要讓我們餓肚子了!”
高坡上不僅天氣乾旱,靠天吃飯,還經常有野獸出現。到了夜間,成群結隊的野豬出來覓食,翻拱紅薯,踐踏高粱,破壞莊稼。
記得小時候,每逢高粱、包穀、紅薯成熟時,父親與我就在莊稼地旁邊搭起一個草柵,用一根繩子串起兩個破鐵桶掛在樹枝上。我們晚上就睡在草柵裡,只要聽見草叢裡有野豬走動的聲響,就立刻拉扯繩索上的鐵桶。鐵桶便會發出:“哐當——哐當”的響聲,嚇得野豬屁滾尿流,驚慌而逃。
然而,我們不可能每天夜晚睡在草柵裡守護莊稼。況且,山裡的莊稼地又不成片,守了東片,守不到西片,所以,野豬破壞莊稼的狀況非常嚴重,甚至到了莊稼被野豬踐踏得顆粒無收的地步。
我母親見到地裡的莊稼遭到野豬踐踏,一片狼藉,心痛不已,含著淚眼罵道:“該死的野豬,你們到底還讓不讓我們活下去啊!”
即便這樣,山上的農民不管種下去的莊稼有無收穫,照舊揚起牛鞭 “號——起,號——起”的趕著牛,耕耘著那幾片狹窄而貧瘠的田地。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山坡還是那麼高、那麼陡,樹木還是那麼茂盛,泉水還是那麼清純 ,野豬還是那樣肆無忌憚的破壞莊稼,水塘邊那架古老的水車,還是那麼吱呀、吱呀地轉著,轉過了一個又一個乾旱的季節,既像是在有氣無力地歌唱,也像是在無可奈何地呻吟。除了大自然一年四季週而復始的交換更替,一切幾乎都還頑強地保持著幾分具有原始色彩的古樸風貌。但是,在這份近似原始的古樸中,流淌的卻是一種經年久遠的深邃與醇厚。父輩以及父輩的父輩們,把一生都顯得過於蒼涼凝重的歲月,毫無保留地交給了大山,交給了一年四季那清清的山風與淡淡的炊煙……
有道是:天道酬勤。惡劣的環境,貧瘠的土地,似乎並不能詮釋這哲理的深奧與準確。擁擠不堪的大小山巒,把簡陋的苗鄉山寨與山外的世界隔離開來,只有狹窄彎彎的小路,承受著一代又一代山民艱難跋涉的行行足跡。只有細細山泉,澆灌著山裡人家一輪又一輪苦澀日月。
在我的記憶裡,那日子始終被重重疊疊的大小山巒擠壓得瘦扁扁的。勤勞得無以復加的父輩乃至父輩的父輩,同樣有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雄心壯志,但只能是一種信念,一種理想,一種渴望,一種希望。
他們雖然付出了許多艱辛,但並未創造過任何輝煌的業績,也創造不出這樣的業績,更改變不了山區所決定的生存環境和千百年來貧窮落後的生活現實,只不過為了生存,為了養家餬口,憑著一雙開滿繭花的大手,憑著兩隻讓歲月的負荷壓成了紫銅色的肩膀,艱難地挑起大山裡的春去秋來,挑起屬於莊稼人那苦澀的夢想與薄薄的希望。雖然日子過得緊巴巴的,但終歸有他們火一樣滾燙的心血和永遠流不完的汗水,也把大山裡的日子澆灌得實實在在,更把在艱苦的自然環境中謀取生存的堅定信念與原始本能,一代接一代地傳承下來,傳給了生生不息的兒女。
俗話說:一方山水,養一方人。雖然那方山水,改變不了那方人的貧窮落後面貌,而被養育的那一方人,卻始終愛著那方水土,守護著那方山水。所以,自古以來,那裡就沒有幾個人能走出大山。
解放前,為了生活,父母試圖在高山之外的世界做出一些努力,攜帶全家老小離開了高坡上,投奔在麻陽縣城做生意的舅舅,做起了小販。每逢趕場,父母就在城裡做些小生意,經常是天不亮,就起床去進貨,天黑前才收攤,賣棉花、賣百貨,還賣醬油和食鹽,從中賺點差價錢,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
解放後,為了分田地,父母毅然重返高坡上,重建家園。雖然分得了田地,政治上翻身做了主人,但高坡上自然條件沒有多大改變,糧食產量很低,生活依然艱難。
“啊!故鄉,生我養我的地方,無論我在哪裡放哨站崗,總是把你深情地想往……”
蔣大為《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的歌聲,如今時不時在我的耳邊響起。
久居異地他鄉,難免經常想起生養自己的那片故土,忘不了那裡的青山綠水,忘不了那裡的大豆高粱,更忘不了那裡的父老鄉親。
我離開高坡上已經50多年了,但始終記得,參軍入伍的那天,全村老小聚在家門口為我送行,為我披紅戴花的情景。當我在鄉親們前呼後擁下離開故土時,我的視線開始模糊了。
再見了高坡上,生我養我的家鄉!
也就是從那一刻起,思念的種子便深深地埋進了我的心田,時至今日,難以忘懷。
記得小時候,在放學回家的路上,我與同學們常來太羅山寺廟玩耍。至今,還依稀記得在綠林四繞之間,掩映著一座數百年古廟——太羅山庵堂。庵堂不大,坐北朝南,外簷飛挑,牆壁、鬥垬、窗欞均用青磚砌成,翠竹、樹林環繞,蒼松迎客,環境幽靜。人們來到這裡求神拜佛,祈求神仙菩薩保佑五穀豐登、六畜興旺、兒女成長、盛世太平、生活幸福。
佛教文化為蒼蒼茫茫的太羅山庵堂披上了一層肅穆而神奇的色彩。我常坐在庵堂附近的臺階上,四處遙望,胡思亂想。這是高坡上的制高點,放眼一片開闊,心情舒暢,可以忘卻生活中的許多煩惱。如今,我彷彿又聽到了太羅山庵堂的鐘聲,肅穆而悅耳。鐘聲時急時慢,時重時輕,似乎要驅走我懵懂的童年。
我不信神,也沒做過祈禱,可是到了老年,遠在他鄉卻仍然忘不了太羅山庵堂的鐘聲。儘管此時太羅山庵堂的鐘聲,從神州大地上早已消逝,然而,它卻永遠留在我的耳際中。
那時的我,還特別喜歡高坡上的太陽、晩霞和雨過天晴的七彩虹。尤其是夕陽西下的晚霞映紅半個天際。我觀察著太陽的顏色,一會兒是白加紅,一會兒是金黃色,一會兒半紫半黑,一會兒半紅半黃,真是五彩繽紛,非常好看。我聚精會神地凝視著被晚霞映紅的雲朵,心中產生種種遐想。有時雲朵像人、像鳥、像獸、像高山、像流水……我的心也就隨著各種形狀的雲在飛,在遨遊,又隨著雲朵的消散而熄滅。
我怎麼也忘不了故鄉山坡上滿山遍野的油菜花、野菊花、油桐花、油茶花、喇叭花。那是我少年時代的色彩。
尤其是油茶花,那白色的花瓣淡白素雅,就像那不愛濃妝豔抹的山村少女一樣樸實無華,那淡黃色的花蕊鮮嫩欲滴,暗香浮動,就像自釀自飲的農家酒一樣平實溫和,引來許多蜜蜂嗡嗡前來追花采蜜。我和小夥伴們摘來空心的茅草杆,去吸茶花中的蜜汁,清甜可口,芳香醉人。
還有冬天的大雪,鵝毛一般飄揚,滿地白雪皚皚,銀裝素裹。堆雪人、打雪仗,是我兒時少不了的情趣。更讓我喜出望外的是高山上那滿樹滿枝的霧凇、冰條,猶如珠簾長垂,風吹樹動,撞擊有聲,宛如一曲動聽的音樂,和諧有節,清脆悅耳。
如今的高坡上,早已不是50年前的樣子了,在黨和政府的引領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首先是人們的觀念發生了改變,不再像祖祖輩輩那樣死守在那塊傳統、保守、貧瘠的土地上,而是一邊種田,一邊大搞山地開發,引進優良品種,種植油茶、甘蔗、西瓜、血橙、冰糖柑、獼猴挑、金銀花等經濟作物,收入可觀;家家戶戶用上了自來水和電燈,看上了電視;村裡還修建了一條水泥公路通往山外,結束了長期以來靠人挑肩馱的時代;還有不少人家拆掉了低矮的土磚房,建起了連城裡人都羨慕的別墅小樓;有的透過發奮讀書,考上了大學走出山外;有的則走出家門,外出打工,闖蕩世界,且多數幹得不錯,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我離家50多年了,但戀鄉的情結卻始終難以更改,它在我的記憶中,仍然保留著當年的影子,像夢幻一般縈繞在我的腦海裡。縱使歲月蹉跎,縱使父母不在,縱使華髮初現,我仍深深眷戀生我養我的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