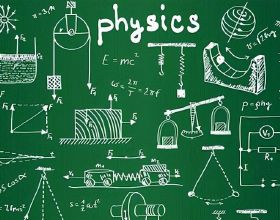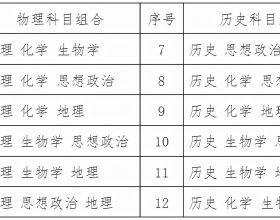某種程度上,各種各樣的練習都可能有效,但其中一種特殊的形式則是黃金標準,叫“刻意練習”。
1908年,約翰尼·海耶斯(Johnny Hayes)奪得奧運會馬拉松冠軍,當時的報紙把這場比賽描述為“20世紀最偉大的比賽”。
海耶斯不僅奪冠了,還創造了馬拉松世界紀錄,成績是2小時55分18秒。
一個多世紀以後,馬拉松的世界紀錄已經重新整理為2小時2分57秒,比他創造的世界紀錄快了近30%,而且,如果你是年齡為18~34歲的男性,想參加波士頓馬拉松比賽,那麼,只有成績不低於3小時5分,才可能獲得參賽資格。
簡單地講,海耶斯在1908年創造的世界紀錄,如果換到今天的波士頓馬拉松比賽中,只夠剛剛贏得參賽資格。
然而這項比賽吸引了大約3萬名長跑者參加。
同樣是在1908年的夏季奧運會上,在男子跳水比賽中,幾乎出現了一場災難。其中一位跳水運動員在嘗試空翻兩週這個動作時,差點兒身受重傷。
幾個月後釋出的官方報道認為,跳水是項危險的運動,建議未來的奧運會禁止該專案。
如今,空翻兩週已成為跳水專案中的入門級動作,即使是10歲的孩子參加的比賽,也必須會這個動作。到了高中,最佳的跳水運動員可以完成空翻四周半的動作了。
世界級運動員甚至可以做更加高難的動作,比如迴旋,也就是說,向後空翻兩週半,再加兩週半轉體。
我們很難想象,20世紀初期那些認為空翻兩週屬於危險動作的專家,會怎樣看回旋這個動作,但我猜,如果當時有人具有這樣的想象力,猜測到今後的跳水運動會出現類似迴旋的高難度動作的話,那些專家一定會認為這是個笑話,絕不可能做到。
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阿爾弗雷德·柯爾託(Alfred Cortot)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古典音樂家,他演繹的《肖邦24首練習曲》被認為是權威的演繹。
而如今,音樂導師們往往把類似的表演作為反面教材加以批判,批評家們抱怨柯爾託採用的那種粗心大意的彈奏方法,而且,每一位職業鋼琴家在彈奏同樣這些練習曲時,有可能運用比柯爾託嫻熟得多的技能。
事實上,音樂批評家安東尼·托馬西尼(Anthony Tommasini)在《紐約時報》上一度發表評論,認為自柯爾託的時代以來,人類的音樂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以至於柯爾託當時的水平,如果放在今天,可能連茱莉亞音樂學院的入學考試都通不過。
1973年,加拿大人大衛·理查德·斯賓塞(David Richard Spencer)背誦圓周率小數點之後的數字時,創下了前無古人的紀錄:511位。
五年之後,好幾個人在一系列比賽中爭著創下新紀錄,結果,這個紀錄最終屬於一位名叫大衛·沙克爾(David Sanker)的美國人,他背誦了圓周率小數點之後的1萬個數字。
2015年,該紀錄被塵封了30多年之久以後,來自印度的拉吉維爾·米納奪得了冠軍,再度創下紀錄,背誦了小數點之後的7萬個數字,這使得他花了整整24小時零4分鐘來背誦。
不過,一位名叫原口證(Akira Haraguchi)的日本人聲稱背誦了更令人不可思議的10萬個數字,或者,我們換個角度來想,這一紀錄是42年前的世界紀錄的近200倍!
這些例子都不是唯一的。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許多人擁有著超常的能力,那些能力勝過人類歷史上任何時代的人們所擁有的能力,如果“穿越”到以前的時代去,都會被當時的人們認為不可能。
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裡,馬拉松的世界紀錄並不是因為人們天生就具有長途奔跑的基因而提高了30%;
20世紀下半葉出生的人們,也不是因為突然之間擁有了一些天賦,就能彈奏肖邦的曲子或拉赫馬尼諾夫的曲子,或者記住數十萬個隨機的數字了。
他們練習,大量地練習。
在20世紀下半葉,我們看到,不同行業或領域的人們投入訓練的時長在穩定地增長,同時,訓練方法也日益高階。
這種在訓練的數量,和精細程度上的與時俱進,使不同行業或領域中的人們的能力穩定提高。這種提高,如果逐年來看,並非總是顯眼,但跨越幾十年,便十分驚人!
某種程度上,各種各樣的練習都可能有效,但其中一種特殊的形式則是黃金標準,就是有目的地“刻意練習”。
不論什麼行業或領域,全都遵循同樣一些普遍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