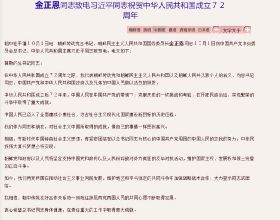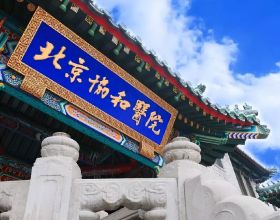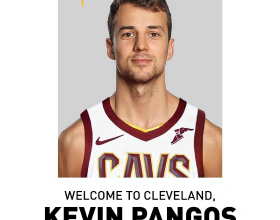著名導演李睿珺的《隱入塵煙》,講述了一對貧苦艱辛,樸素溫良的農民夫婦的白天黑夜與春夏秋冬。黃土地上的生命之歌:在土地上耕作,在土磚房子裡生活,在土包墳墓中安息。他們紮根在土地上的一生,和田野一樣沉默,塵埃一般微薄。茶米油鹽的點滴之間盡是兩人相扶相守的溫情,好幾處看得流淚。
他罵驢說,“你可真是賤骨頭,讓你走你還不走。”日子這麼苦,總要過下去。這是我最不喜歡這部電影的地方,因為太過殘忍;也是我最喜歡這部電影的地方,因為絕對真實。為一部完全屬於土地與土地上的人的電影喝彩,為這片土地上千千萬萬個個體的生命祝福。
在老人與孩童、生與死以至文化尋根等話題之後,導演嘗試討論:鄉村愛情是何種形式——如果它確實存在的話。一對被村裡公認境遇最慘的男女,相互扶持,在蒼茫田野中也竟活出了人定勝天的樂觀主義。
燕子仍會築巢,雞群仍要下蛋,土坯房倒了三次,索性便搬進樓房中去。向城市的輸血永不停歇,他/她們是熊貓,是不善言語的農民,他們的腳走再遠也離不了土地。在那裡,他們拋灑血汗,活出獨屬自己的浪漫與驕傲。
女主表演微有瑕疵,觀影偶感冗長拖沓,但瑕不掩瑜。影片和現實世界相比已經是浪漫化,導演點到為止的觸及鄉村現代化過程中的問題(強迫婚姻、拆遷、村霸、分配),溫柔地給了四哥和桂英一個田園牧歌式的童話:
把腳印種在自己的泥土裡,就能用最樸實的努力一步步得到更好的生活,如同小麥播種會從抽芽到成熟到收穫一樣,雞蛋孵出的雞雛會慢慢長大開始下蛋,人會相濡以沫地相愛。這樣符合“正常自然規律”卻是理想的“田園牧歌”,這樣的不真實。
就像是片中抽血的隱喻,對鄉村現代化中的本分的農民們而言,他們的命如同黃土地裡的水分,被時代緩慢地、沉默地一次一次抽乾,直到再也堅持不下去。
故事在不動聲色地流淌中,呈現出深厚的情感密度,兩個被邊緣化的人物,在被遺忘的角落裡用最笨拙,樸素的方式彼此溫暖,結局讓人唏噓不已。海清在影片中的表演有極大突破,無論是肢體還是語言,以及微妙的表演細節,都賦予人物精準而生動的表達。
素人男主用他久經風吹日曬的臉龐和熟練的勞作,自然而有力的讓影片深深的紮根於土地。攝影指導王維華運用紮實而靈動的光影、凝練有韻味的構圖和運鏡,以及對色彩元素的選擇和提煉,勾畫出了一副富有古典繪畫感的西北人民生活畫卷。整部電影內斂雋永,耐人尋味。
如果從鄉土情結,人與土地的關係來談這部電影,我想德國人未必真的能有所共情。來德國生活的兩年多里我去了許多小鎮,這裡的小鎮與國內的農村有著雲泥之別,沒有高樓與土坯房的衝突,也沒有因時代變遷而被迫離開故居的流離感。好在這部電影的格局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上升到了普世的人類情感。
我喜歡這部電影構圖中對人與環境關係的表達,沒有那麼多西北風光的空鏡,恢弘中帶有著人文視角的溫情。沒有強烈的戲劇衝突,運用了很多的中景平拍,能夠讓觀者恰好地處於情感介入與置身事外的距離平衡感中,看著劇中的人物完成各自命運的自洽。
電影中不斷出現的玻璃罐讓我想起了小時候,家裡常拿吃完的黃桃罐頭喝水,跟電影中的玻璃罐一模一樣。小時候到了秋收的季節買把麥穗一路嚼著麥子回家,長大後再也沒見過真正的麥子了。
泥沙,水源,莊稼,牲畜,純淨而踏實地用影像丈量土地。降住了塗抹戲劇化色彩的衝動,守住了堆砌刻奇元素與技巧的野心,導演用大自然拍出了一部電影。“吸血”、“腳長在地裡”、“燕子找不到巢”等等意象都直白清晰,農民主角化身農田裡的蘇格拉底,用行動與對話分享他的泥土哲學。
客觀評價,它可以是一部好電影,卻也是一部遠遠可以更好的中國電影。僅從抒情的角度看,它是精明且有效的。全片事無鉅細地展現農村生活,卻能牢牢錨定“土”(耕種的地和建築的泥)的核心意象,將情感增厚,為羈絆賦形,做到形散神不散:
窮人的命運就是紮根土地,風吹雨打,仍在默默隱忍中開出自己的麥花。但從一個瞭解電影語境的中國觀眾角度出發,這種將逆來順受浪漫化的溫吞做法背後,又有多少結構性的頑疾被草草略過?這片土地有太多值得且亟需被講述的故事,它們絕不該隱入塵煙。
從一個人撐全場的男主和打醬油的村民表演來看,從貌似講究其實並不講究的攝影來看,從符合國際標準可是並不符合本片風格的配樂來看,從被稱作毀容獻身但怎麼都無法融入的海清選角來看,從話不多說但字字矯揉造作的臺詞來看等等,都讓我懷疑本片的淳樸性和真誠性。
很多情節生硬設定讓我搞不清這到底是生活化還是舞臺化mise en scene. 一部好的電影應該有讓我們想要更多去了解我們不曾瞭解的人事物的慾望,而不是下一個空洞的結論,引發我們更多思考,而不是進一步加強固有印象。同樣情況也發生在比如敘利亞黎巴嫩阿富汗電影中。
影片一直在處理關於生命和時間的問題,那些細碎的平常,配合導演獨到的古典美學畫面掌控,將電影視覺觀賞性上升到了另一個高度。導演曾說過,“透過電影,我們都是在處理時間的問題”。對於時間的探尋,寒往暑來,夏雨冬陽,麥子與土地相生相伴,四季輪迴,人也一樣。
導演將鏡頭對準自己的家鄉——西部,談及家鄉,談及土地,導演的態度十分謙虛,沒有過多修飾,更多的是“生於斯,長於斯”的從容和質樸,將自己對於家鄉的理解和對於生命的哲思置於土地之上,緩緩流淌,耐人尋味。
影片女主人公是世俗眼中的殘障人士,但完整與殘缺本就是事物的一體兩面。被定義、被貼標籤,我們何時才能打破人與人之間的藩籬?透過一個近似孩童的視角,洗去成人世界的汙濁和不堪兩個生命的彼此依戀和惺惺相惜,是一種不帶任何偏見的愛,也是毫無隔閡的愛。
謝謝觀賞,關注我,帶你瞭解更多娛樂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