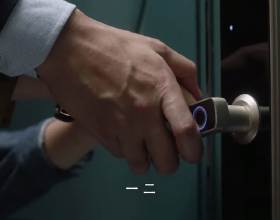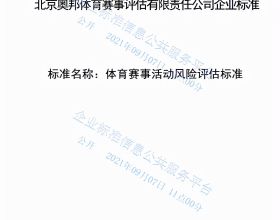從前讀《靜夜思》,覺得李白通篇都在講廢話,這樣寡淡如水的詩是怎麼做到流傳千古的。
正月初七,我坐上返程的大巴,看著窗外仰頭眺望的父母,看著他們隨著汽車加速慢慢變小變模糊的身影,突然就懂了什麼叫“舉頭望明月”。
長年身居外地,遙遠的物理距離似乎同時變得模糊不定。
“小學時半天回趟家;
初中時一星期回趟家;
高中時一個月回趟家;
大學時寒暑假回趟家;
後來我們工作了,回家的時間單位就變成了年。”
這段流傳在網路上的熱門句子惹哭了無數遠在他鄉的遊子。
春節回家的感覺真的不同於以往,本來想著過年暫不回去,等到疫情和溫度一起春暖花開的時節再動身,但就在年二十八的下午,當我看見父親發來的貼好春聯的大門、母親蒸好的大饅頭,還有背景裡隱隱約約的鞭炮響,回家的念頭再也抑制不住。
忙年忙年,過年大部分的精彩之處,就在於臘月底那幾天的忙碌:打掃屋子、換灶符、購置年貨、和麵調餡……它同時承載著小時候無數難以忘懷的時光,即使物質匱乏,生活困頓,但滿滿的都是愛,隨著鍋蓋一掀,幸福的感覺隨著水蒸氣上升盤旋,那滋味就像嗜酒的人輕抿一口老白乾,慢嚼一粒花生米。
如今,忙年的流程中多了一項父母對遠方孩子的念想。
近鄉情怯,讓人無法直面的除了家鄉今非昔比的面目,還有父母肉眼可見的衰老程度。
那不是像影視劇裡的角色透過化妝技巧體現在臉上分佈均勻的老年斑、刀劈斧鑿般的皺紋,或者白得恰到好處的頭髮,是在跟父母日常接觸中的切身體驗,真實且殘酷。
小時候,我是個多動且話嘮的人,經常不分場合大放厥詞,然後收到來自父母嗔怪的眼神,禁止我再羅嗦半個字,這種情況持續了多年,直到有一天,我發現父母開始無比信服我說的話,不管是我打電話回家,還是隨便在微信上說了一句話,都會收到他們的認真研讀、反覆確認。
雖然我曾經無比羨慕那些被家長讚美安靜和沉穩的孩子,但當這些被父母無比尊重和重視的時刻真正到來,我卻寧肯它從來不曾來過。
我寧願他們還是在寒冷的冬晨掀起被子,一邊怒吼幾點了一邊把我從床上拎起來的爸媽、一見我開電視就嘟囔不去學習光知道玩樂的爸媽、因為藏在床底為過年準備的糖果點心已經被我偷吃得所剩無幾而大發雷霆的爸媽、等客人都走光了開始訓斥我在生人面前人來瘋不懂規矩的爸媽……
雖然在語言上日益言聽計從,行動上的不放心卻一成不變,回家之後,幾乎所有的活我都插不上手。
洗衣服讓我一邊待著去,炒個菜熱個飯更是沒機會,好不容易爭取來了洗碗的權利,好說歹說,一定要看我戴上手套再動手。
除了母親這種大寫意的保護主義,還有來自父親潤物無聲的細密關照。
假期結束,臨出發的前一天,父親犧牲掉午睡時間,一遍遍翻看地圖,爭取把前往新機場的路線熟記在心。
午後的陽光透過窗戶,灑在他已經鬆軟的眼皮上,能看得出他一邊和瞌睡抗爭一邊記憶地圖的努力。
這條路線的前半段他走過幾次,只是最終到達機場的路況有些複雜,需要多看幾遍。
我知道直接勸他去休息是無效的,就說到時候跟著導航走就可以啦,不會出錯的。
父親頭也不抬,嘴裡嘟囔著:有備無患。
我這才明白父親其實不是不信任導航,只是為了我能順利到達多一重保障。
雖然準備充分如斯,路上還是出了兩次小插曲,車子拐錯了兩次路,不得不重新規劃路線。
志玲姐姐溫柔的提示音響起:“注意不要被同行車輛誤導哦”,父親臉上漸漸有些坐立不安。
我在後排小聲說,不急不急,時間還早哪。
也不知道父親能不能聽到,這次回來發覺他耳背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了。
好不容易到了機場,我才想起來定位應該停車場而不是航站樓,車子不能停靠。
父親下車,環顧四周,看到幾百米外一個正在打電話的年輕保安,他一路小跑奔過去,問人家停車場要怎麼走。
機場好大,西北風好冷,我呆在原地,一時之間竟然忘了可以用地圖軟體導航,就眼睜睜看著年邁的父親在寒風中奔走、諮詢、點頭稱謝,腦海中突然跳出了朱自清的《背影》。
我的父親並不胖,也沒有像朱老先生那樣有些野蠻地橫跨欄杆,除了現代社會交通規則日復一日的薰陶,還因為父親骨子裡是個強硬地抱著體面二字不撒手的人,所以他寧肯沿著長長的欄杆,一路疾行,矯健的身姿一時間讓人忘了他的膝蓋常年有病患。
我回過神來,掏出電話:“爸爸回來吧,咱們可以跟著導航開進去。”
父親在遠處露出笑臉,內容複雜,裡面有歉疚、無奈和不好意思。
關於他的膝蓋,曾經買了幾個療程的藥,電話裡反覆叮囑他一定要按時吃,結果今年回家和媽媽一起打掃衛生,居然清理出了包括十幾盒膝蓋藥在內的一袋子過期藥,趁父親外出不在家,偷偷扔了。
讓他看見,這些過期藥不一定能順利肄業,畢竟他是個把過期半年的鈣片還可以裝在口袋裡拿出來吃的主。
這項不到過期堅決不開封的優良作風,母親也執行地極其到位。別看她此刻在清理過期藥的時候對父親咬牙切齒,買回去的雞鴨魚肉,往往是拆開包裝,整整齊齊地碼在冰櫃深處,在他們的認知裡,低溫冷藏是食物長存不變質的尚方寶劍。
平時摳摳搜搜,捨不得拿出來吃一口,說說他們,他們會說,要是自己現在就吃了,進來個人拿什麼伺候人家?
我說,現在買就是現在吃的,以後來客人我們再重新買就是了。
他們說,那不還得另外花錢。
......
反正,他們總有充足的理由反駁你。
從小過慣了苦日子的父母,也許永遠都無法適應對自己好一點。生活剛剛展露出一點點甜頭,他們淺嘗輒止,總是害怕享受會令自己忘形,以至於無法感知災禍的來臨。
但是爸爸媽媽,你們要知道,除了你們自己,還有兒女和你們一起迎接每天的生活,不管它是陽光明媚,還是大雨傾盆,因為我們已經長大了呀。
筷子兄弟在《父親》裡唱道:“時光慢些吧,不要再讓你變老了,我願用我一切換你歲月長流。”
當年第一次聽到這幾句詞,內心如電光火石一般回到小時候,那個曾經在無數深夜醒來,暗中向造物主許願把自己多少年壽命借給父母的中二少年,離譜至此,還不忘平均分配,不偏不倚。
也因為這份從小種下的羈絆,讓我在去年春節對父親大為光火。
除夕夜對於家中每個人的意義不言而喻,在結束長達數小時的電話拜年之後,父親不知從哪裡掏出一個小本子,鄭重地坐到我們面前,臉上依舊掛著和善尋常的笑,嘴裡說的卻是我們聞所未聞的話。
“我年紀大了,這裡是幾張銀行卡和存摺,是我和你媽這輩子的積蓄,密碼都記在上面……”
電視機裡春晚正當高潮,氣勢恢宏的大合唱和交響曲充滿偌大的屋子,我顧不上過年應有的體面和規矩,衝還在絮絮叨叨的父親大喊大叫:爸爸你這是幹什麼啊。
母親在遠處,靜坐無語,面無表情,臉上的顏色隨著電視機的光影轉換。
後來,還是母親偷偷告訴我們,父親從去年開始,記性越來越差,有一次直接跟她說:我怎麼覺得我有時候腦子有些迷糊。
長期的兩地分居,讓我想當然地認為父母還是記憶中的模樣,即使不是無所不能,能幹健康依然不減當年,直到與他們耳鬢廝磨相處幾天,才知道自己的臆想大錯特錯,毫不負責。
零點到了,鐘聲敲響,不管在座的觀眾是否願意,晚會正在接近尾聲,新春即將來臨。
《難忘今宵》那熟悉的旋律響起,只用耳朵就能分辨出那是歌唱家李谷一的聲音。
這副我們自孩提時代家裡第一次有電視的時候就印刻在記憶中的嗓音,也不知道還能聽多久。
從一開始的零點即結束,到這些年零點過後還依依不捨,陸陸續續加節目,春晚的時常越來越久,就像即將離家返程的你我,臨行前的磨蹭和不捨。
回到北平不久,朱自清收到了父親的來信,信中提到他近來膀子疼痛,提筆寫字都受到影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朱自清讀至此,抬眼望燭,淚光點點,眼前又浮現出父親為他買橘子翻越月臺,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
“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
如果朱自清生活在現代,他一定不會如此感傷,只要他時時關注下航空公司的特價機票,囊中即使再羞澀,也能負擔得起來回的路費,分別和重聚都不再艱難。
常回家看看吧,別讓它只是一句空話。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