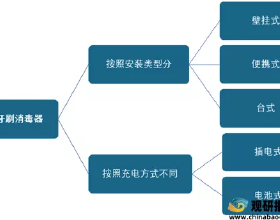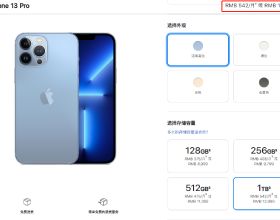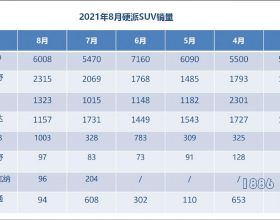海灣國家有多依賴石油,就有多依賴移工。
在中東國家阿曼的首都馬斯喀特(Muscat)。這裡的街景和其他靠油氣資源致富的鄰國沒什麼差別,一棟又一棟摩天大樓在沙漠拔地而起,想必也令初來乍到的女子伊莎(Isha)目眩神迷。
27歲的伊莎來自非洲的獅子山——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度之一,她飄洋過海來到阿曼,深信有一份收入不錯的餐廳工作等著自己;但隨著手中護照突然被奪走,伊莎對未來的美好想象全在那一刻戛然而止。
中介機構搶走伊莎的護照後,將她塞進車內,驅車送她到一處民宅,並告訴伊莎:從今天起,她就是這戶人家的女傭。隔天凌晨5點,才抵達新住所數小時的伊莎就被僱主叫醒,命令她打掃房屋,準備送家中孩子去上學。
“我不是為了這份工作來到阿曼,”伊莎表示:“中介對我說,他已經把我買了下來,所以他可以拿走我的護照。我覺得很困惑,你怎麼能‘買下’一個人呢? ”
壹
卡法拉制——全球首富國的外邦人
波斯灣六國——沙烏地阿拉伯、巴林、科威特、阿曼、卡達和阿聯酋在1981年成立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GCC),這幾個阿拉伯國家“富得流油”,公民往往享有令人稱羨的社會福利,並引入大量外籍勞工投入本地人不願從事的三K(骯髒、危險、辛苦)行業。
環顧GCC國家,家務勞動與建築業的從業人員逾90%由移工去做;以2022年世界盃足球賽主辦國卡達為例,該國以購買力計算(PPP)的人均GDP高居全球第一,但全國近300萬名居民中,只有30多萬人是“真・卡達人”,其餘全都是來自南亞、東南亞、非洲窮國的外籍勞工,阿聯酋、科威特的比例也差不了多少。
在移工人數是本國公民好幾倍的人口結構下,GCC國家發展出卡法拉(kafala)制管理外籍勞工,黎巴嫩、約旦等鄰國也跟進採用。卡法拉制度由僱主擔任外籍勞工的“擔保人”,掌控移工簽證與合法身份的生殺大權,而不受地主國勞動法規管轄。
在卡法拉制實際運作下,僱主可以單方面決定、終止勞動契約,移工的護照往往被僱主扣留,不得自由轉換工作,甚至不能在未經僱主同意下離開工作場所,休假日、工時等基本勞動條件自然也難獲保障。
儘管遭受剝削的情形十分普遍,卻也無法尋求工會救濟,勞資雙方的權力關係完全失衡。若移工不堪虐待而成為非法“逃跑外勞”,則將面臨被遣返回國的命運。
儘管卡法拉制長年為人權組織所詬病,甚至批為“現代奴隸制度”,科威特、卡達也因“菲律賓女傭遭僱主殺害”、“籌備世足賽期間數千名移工客死異鄉”的勞權爭議,在國際壓力下著手改革部分規定,但法規改善與實際落實往往是兩回事。
2018年2月,菲律賓女移工喬安娜(Joanna Demafelis)在科威特遭僱主殺害、棄屍於冰箱內的案件震驚全球,菲律賓甚至包機“召回”科威特境內數千名菲籍移工,兩國外交關係一度陷入冰點。
貳
她們為什麼來?為什麼想逃?
從海灣國家的角度觀之,來自海外的低薪移工填補了國內勞動力空缺;而貧窮和絕望則是移工被中介半哄騙來到沙漠國度的原始驅動力。
剛從大學護理系畢業的迪亞(Dija)是伊莎的獅子山同胞,2015年,迪亞的伴侶被伊波拉病毒奪去性命,為了撫養兩人的女兒長大,她決定出國打拼——中介介紹她到一家位在歐洲的醫院工作,月薪500美元(約人民幣3241元)、還有自己的公寓房間。
迪亞的中介安排她先經陸路抵達幾內亞,飛往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再轉往馬斯喀特。迪亞當時不知道,阿曼就是這趟旅程的目的地。如今她在阿曼第三大城撒拉拉(Salalah)擔任家庭幫傭,“我登機時還以為自己要去歐洲……對我而言這裡就像地獄一樣。”
而在新冠疫情之中,千千萬萬個“伊莎”的處境愈發艱難:由於海灣產油國的經濟同樣因疫情重挫,許多僱主首先就苛扣幫傭的薪資,家事移工在封鎖令下坐困屋內,不只工時因此拉長,僱主暴力相向甚至伸出狼爪的案例也屢見不鮮,但發生在家門內的一切卻難以為外界看見。
月薪180美元(約人民幣1167元)的伊莎說,她在僱主家中沒有休息時間,僱主不但會打她、甚至心情好才給她東西吃,她的手機也被沒收。在僱主連續欠薪3個月後,忍無可忍的伊莎決定逃走,但獅子山並未在阿曼設立使館,無處可去的她最後還是被僱主尋獲帶回。
伊莎的僱主表示,如果她償還僱主當初付給中介的1560美元(約人民幣10114)費用,就讓她如願離開,但伊莎自然是付不起這筆錢,僱主選擇將她賣給新東家,“他說有另一個男人想要我去工作,叫我包袱款款跟著他走……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真的很想設法回到家人身邊。”
叄
小結
如今在美國等一些國家,合法移工數量驚人,靠移工撐起製造業、營造業、漁業、家庭看護等產業的半邊天,與前面介紹的海灣國家“卡法拉”制相對比,有的地方,移工只有在取得原僱主同意或權益受損(遭毆打、欠薪等)的情況下,才得以轉換僱主,但後者往往舉證不易。
西方媒體更是將阿拉伯世界的卡法拉制形容為“現代奴隸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