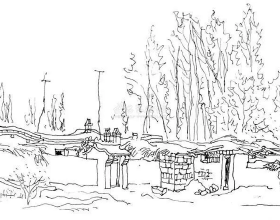李雪牙/文
1.
一次偶爾的機會,我在公交車上看到了一位初中同學。開始,我沒有叫他,我戴著口罩。
車快到站了,車速很慢。我那位同學用雙手撐著靠椅背,十分吃力地站了起來。這麼費勁?我沒有在意。70好幾的人啦,人老先老腳嘛!
忽然間,只見他從背後不顯眼處,拿出一副柺杖,往嘎雞窩一夾,動作之熟練讓我瞠目。看來,我這位同學藉助柺杖不是一年半載的事了。難道是高血壓中風後遺症?也不像!
下車的人很多,我緊跟他後面,萬一有個什麼閃失,我好隨時伸出援手。
“鍾才有!”下車後,我叫到。
鍾才有抬起頭來,望著我,他旁邊站著一位女的,不用說,這是他的婆婆。
我把口罩摘下來,好讓我這位老同學認。過了好一會兒,他沒認出來。也難怪,從學校分開都半個多世紀了。那時候都是雞崽沒離窩,絨毛鴨子沒下過河啊!現在要猛地相認,還真是有點為難他了。何況,我外在變化也太大了點,一時認不出來,也在所難免。但是,我一報出名字來。他大驚道:
“哦,是雪色!”
“是,就是雪色。是六月的雪色!”我很驚喜,驚喜的原因是他叫出了我的綽號。那時,我們班男生見人一個綽號,而且後面帶“色”的居多。什麼“賀色”、“顏色”、“彭色”等等,不一而足。眼前站在我面前的這位同學就是“有色”。
2.
我望著“有色”那副柺杖,憶往昔的思緒嘎然而止。我迫不及待地問:
“怎麼搞的,這是?”
說來話長。他說他三、四年前,那天他上街。突然一部摩托車朝他闖來,燒汽油的摩托車勁特別地大,將他從馬路這邊,一下摔到了馬路那邊。只聽得“嘭”的一聲響,就暈死過去了……事後,聽講有很多人幫他去追肇事者。由於逃跑的速度太快,沒追上。只記得是個年輕的後生,人樣子長得還帥氣,大概20歲出頭。
“就這樣我用上了柺杖,這一用就2~3年了。是真正的殘疾人了,而且是二等殘疾人。”鍾才有平靜地述說著,絲毫也看不到半點的怨恨來。
“其他方面沒有什麼毛病吧?”我問。
“其他的還好!”他偏著腦袋看著我。奇怪的是,他臉上的皺紋極少。也許上天的平衡術,在他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腳瘸了,臉上的皺紋就少了?
我和他互留了電話號碼,加了微信。
我站在原地沒動,目視著鍾才有。他在他婆婆的陪伴下,一步一挪地過了馬路,上了對過的人行道。剎那間,一股悲鳴的情緒湧上了我胸口,然後,又像蠶繭抽絲一般,一寸寸將鍾才有那多舛的命運拉扯出來。
3.
我們是被後來的人們稱之為“老三屆”的學生。大概從那個時候起,在學校也開始講究階級成份了。由於階級成份的介入,一群乳臭未乾的毛頭小子,自然而然地四分五裂了。出身好的,趾高氣揚;出身不好的,垂頭喪氣。
鍾才有家庭比較複雜,由於複雜而變得悲慘:
他父親鍾連祝土改時劃為貧農,時到30歲還沒有成家。也正是那一年,經人作媒討了一位地主的女兒。第二年鍾才有來到了這個人世間,緊接著他的弟弟鍾才狗也降生了。真是:窮苦人家別的本事沒有,生下的崽伢子卻像矮子上樓梯,一個接一個。只可惜他父親命不長,在弟弟出生後不久,就一命嗚呼了。
貧農出身的父親,並沒有給他母親帶來福音,反倒是他母親命喪黃泉的禍根。那個年代,在山高皇帝遠的農村,那些個文盲理不通的人們,硬是說他母親搞階級報復,將其夫鍾連祝活活整死了。於是,這些個貧農根子們(貧農中的骨幹)就將他母親活活整死了。
母親臨死前,把只有六歲的鐘才有叫到身邊說:
“才有啊,你一定要記住,你父親不是我整死的,是病死的;我死後,你帶著弟弟到城裡去投靠你伯父,他在河街裡開豆腐店,他叫鍾連意。只有他,才是你兄弟的依靠……”
鍾才有哭著央求左鄰右舍,將自己的母親用草蓆裹著埋了。
他揹著比自己小一歲半的弟弟上路了,他們要去投靠伯父。一條河阻擋了他們的去路,船老大出於同情,讓他們上了船,不收錢。誰知船行到河中間,船老大叫鍾才有把背上的細伢子放下來,好歇口氣。
“唉呀嘞,這個細崽伢子已經沒有了氣——死了。”船老大嚇得臉鐵青鐵青的。
確實是死了,是餓死的。只有六歲人的鐘才有跪在船板上,哭天喊地的。小小年紀的他,目睹了母親的去世,而今又目睹了唯一弟弟的死去。他懵懵懂懂地看著河水,衝撞著船弦激起的浪花,濺到了早已斷氣,冰涼的弟弟屍體上……
他想上岸後找一塊地方把自己這位可憐的弟弟埋了。船老大則說:
“算了吧,生死有命。把他丟到河裡餵魚吧,好讓他早投胎!”
弟弟的屍體被扔到了河裡,激起一個人字形的浪跡,隨即被推過的後浪掩蓋住了,永遠地掩蓋住了。
4.
伯伯鍾連意在河街裡開的豆腐店不大,但維持包括鍾才有在內的一家五口人的生計,還是不成問題的。
鍾才有苦難經歷,使他的性格變得有點畸形,不輕易同人交往,對周圍的人和事都持懷疑態度。更令人想不的是,他得了一種怪病——雞胸病。這種病直接導致了個子長不高,其次是胸前鼓起一大砣,像極了雞胸。他的這個雞胸病還有一個特殊,就在於影響到了他的頸椎變得特短,而且嚴重右偏。平時,他看人總是偏著頭,不知道的,還以為他是趾高氣揚,在白眼看雞蟲。實則是他的頭被頸椎固定了的,不偏不行啊!
平心而論,就五官,他長得還不錯。一雙烏黑髮亮的眼睛,無時無刻不放射出鷹隼般的光,在刺探著這個世界的方方面面;一個只有外國人才有的鷹勾鼻,彰顯著原本血統的高貴;一對招風耳,有如《封神演義》中順風耳高明;他一張闊又大的嘴巴,好像隨時隨地要吃四方的樣子;他個子確實不高,大概也就1米55左右;十分搶眼的是他那個雞胸,猶如背上了一個大大的包袱,像是要踏上那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的趕考之路。
鍾才有在班上屬於弱者,同學們沒有誰會在他面前頤指氣使,他是受大家保護的物件。對此,他心存感激。可是在外面,特別是學校四周的菜農,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們就讀的是一所完全中學,有初中有高中,是掛牌備案的公認名校。它得天獨厚,坐擁本市八大景點之一的“西湖夜放白蓮花”,是天然的一心只讀聖賢書的好地方。一塊標準的400米跑道的操場,平整地躺在兩邊的藕塘之間。每到農曆五六月間,藕塘兩邊合抱粗的柳樹成蔭;荷葉早已離開了水面,搖頭晃腦地陪襯著那羞羞答答的荷花,有粉白、有粉紅、也有一半粉白一半粉紅……真是此景只應天上有,人間難得幾回見?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菜農們就忙碌起來,他們分別搭起了值守的棚子,以防遊人和學生下塘踩摘荷花或挖藕。
順著校門外牆根往後走,就是郊區菜農耕作的菜地了,一望無際。他們種出來蔬菜瓜果,主要供應物件是市區居民。
每年端午前後,都是新鮮瓜果上市季。這個時候,也是菜農最頭痛的。他們防範的主要物件就是學生,怕他們順手牽羊偷黃瓜吃。
在這個學校讀書的學生,大部分是走讀生,鍾才有也是走讀生。
一天下午,鍾才有同隔壁班的幾個同學返校了。他們抄的是近路,近路必須要路過菜地,而這一路的菜地正好種的全是黃瓜。那一條條翠綠翠綠的黃瓜,吊在瓜架子上,在紅彤彤陽光的照射下,格外搶眼。走在前面的是初64班張黑子,他是學校田徑隊短跑運動員,跑得賊快。大概中午在家裡吃的是酸水籮卜,特別地鹹,這會兒口渴得厲害。望著那瓜架子上吊著的黃瓜,那經得起這樣的誘惑?他想都沒想就伸手摘了一根黃瓜,雙手一搓,一口就咬去了三分之一。突然,從後面追過來兩個菜農。
”捉偷黃瓜的賊呀!”那菜農加緊了步子,其中一個提著小瘀(小便)桶。
張黑子撒腿就跑,一溜煙不見了。跟著跑的,一人手裡一根黃瓜,像手握接力棒一樣也不見了。鍾才有手裡沒有黃瓜,他不是不想,而是沒來得及。他想:捉賊捉贓,手裡沒有黃瓜總奈何不了自己。
“站住!”
鍾才有站著了,他抬著頭望著這兩個菜農。
“唉……,這傢伙還有理了。你看他偏著個腦殼,啊?”
“好啊,他多半是把黃瓜吃了。讓我看看你的口!”那個提著小瘀桶的菜農說。
鍾才有人老實,他張開了那個大嘴,想讓他們看個究竟。萬萬沒曾想,一瓢小瘀灌到了他的嘴裡。一股子濃烈的尿騷味,擊穿了他的味蕾。“哇”的一聲,把中午在家裡吃的飯菜全吐了出來。他抬起頭來,用他那鷹隼般的眼睛怒視著對方。顯然,那兩個菜農被他的氣勢嚇怕了,走了。
這天下午,鍾才有上課遲到了。班主任和同學們知道這個情況後,集體到校長辦公室請願。後來,那兩個肇事的菜農,在強大的與論壓力下,向鍾才有作了賠禮道歉。
5.
那個年代,憶苦思甜是常有的事。在一次班上憶苦思甜的活動中,鍾才有把自己的苦難經歷全部述說出來了。同學們對他這個特殊的家庭出身,沒有,也不可能作出一個子醜寅卯來。唯有一位同學,叫向雪武。他的文章寫得好,不但有華麗的詞藻,還有一定的思想性。他就鍾才有的憶苦思甜,寫了一首散文詩:
有色,
真有特色,
肥了地主的五官,
瘦了貧下中農的下半闕,
有色,
真有特色,
一半是地主家的血,
一半是貧下中農的血,
混血兒,
有色,
典型的混血兒。
從這個時候起,鍾才有又多了一個綽號:混血兒。
6.
按照父系社會的古老傳統,鍾才有是個不折不扣的貧下中農子弟。他被分配進廠是鐵定的,但是他雞胸和偏頭症卻拖了他的後腿,體檢過不了關。沒有哪個工廠要他。
他上山下鄉了。
他回到了自己的家鄉。他以前同父母居住的房屋依舊在,但換了主人。
好在他屬於知青,早已不是10多年前,任人擺佈的小孩子了。再也沒有人在他面前提起當年他母親的事情,當年致他母親於死地的那些人,大都不在人世了。
三年後,同他一起下放的知青,都返城進廠當了工人。唯獨他沒有,沒有的原因不是生產隊和大隊卡他,而是他的雞胸和偏頭症耽誤了他。他徹底死心了,他已作了一輩子當農民的準備,本來自己就是農民的子弟。
第四年,一家區辦廠子來人招工了。他無動於衷,不是他看不起區辦廠,而是他看不起自己的身體。
“你想不想返城?”招工的人問。
“你們搞不搞體檢?”鍾才有問。
“只要不瘸腳瞎眼,我們都要!”
這是一家皮帶運輸機械廠,從業人員多半是街道的婆婆和半殘疾人。鍾才有在這個廠如魚得水,也很受上級領導欣賞。畢竟文化程度擺在那裡,老三屆。
兩年後,他出任該廠廠長。在他的帶領下,這個廠一躍成為了眀星企業。他們生產出來的皮帶運輸機,遠銷全國各地,曾一度供不應求。
7.
時間太瘦太瘦了,不經意間就從人們窄窄手縫中溜走了。
算起來,我們班這個混血兒——有色,即鍾才有今年應該有70有1了。真是沒有想到啊,臨老了(68歲)還被摩托車撞飛了,落得個終生殘疾。真是雪上加霜啊!那個年輕人的肇事者怎麼能逃之夭夭呢?這在幾十年前,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
回憶的思緒,像沙漏一樣,突然間被一個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卡住了。“為什麼人世間的苦難,全都堆積到了混血兒一個人的身上?難道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算了吧,那純粹是扯淡,都什麼年紀了?那又是為什麼呢?
還是混血兒本人,他的一句話解開了我這一心結。他說:
“人的這一生,是還債的一生。有的人是還幸福的債,這個債是甜的;有的人是還磨難債,這個債是苦的。我是屬於後者。想到這裡,我就想通了,反正都是還債。”
望著他那偏著的腦袋,我釋然了,如同卸下了重擔一般。但,同時我又在吶喊:天吶,你可曾聽見混血兒,一個安於本份人的心聲了麼?
8.
一天,我接到混血兒——有色即鍾才有的電話:
“雪色,你過來一趟吧。我有要事同你講。”
我心裡“咯噔”一下,難道……?因為都這麼大年紀了。我急匆匆地趕到了他指定的地方。
“什麼事?”我上氣不接下氣地問。
“看你急得!你先坐下,我慢慢對你說。”他笑眯眯地說。講句老實話,我們同學時,很難看到他笑。一次是班主任老師,當著全班同學宣佈,他的階級出身是貧下中農,他笑了;一次是那兩位菜農來校賠禮道歉時,明確說他沒有偷黃瓜時,他笑了。除此,他再也沒有笑過。
今天他笑了,肯定是好事。於是我說:
“有色,看你笑得如此開心,肯定是有好事。快講吧,別賣關子了!”
“好,好。”說著,他就把一個星期前發生的一件事情告訴了我:
那天,婆婆正陪著他在小區院子裡散步。一個小夥子提著一袋水果來到他面前。
“請問,您是鍾才有老人吧?”
“我就是。請問你是……?”
在確認後,他撲通一下跪在他的腳下,眼淚汪汪的。樣子十分地懊惱和痛苦。他雙手扶著那柺杖斷斷續續地述說著:
“三年前,就是我把您撞飛的那個年輕人。我叫王一博……”他述說了當初他也是一走了之的心態。後來,他冷靜了。他暗自下定決心,他要負責。然而,憑什麼負責?他南下打工去了……
“起來吧,事情都過去了。不要舊事重提了。關鍵是知恥而後勇,是難能可貴的呀!”
王一博臨走時,塞給了我一個活期存摺,上面有10萬塊錢。末了,他還加了我的微信說:
“大伯,我已是父母雙亡。如若不棄,我願作您們兒子!”
“雪色,情況就這個情況。錢,我收下了;這個兒子我也認了。雪色,你說我能不笑嗎?”
“是的,真的是該笑,應該開懷大笑!”
後來,有色在電話裡說,他把那10萬塊錢,在他家鄉那個小學,辦了一個圖書館。取名叫“一博”。
再後來,有色又在電話裡說,一博現在每個月都給他轉1000塊錢。我沒捨得用,我把它存起來了。這錢是給“一博”圖書館添新書用的。
“有色兄啊,這個錢你就買點營業品吧!”我在電話這一頭,幾乎是含著淚水說。
“不用了,我和婆婆有退休工資。再說,我也想慷慨一回,還一次幸福的債!”
我徹底無語了。我的耳邊響起了當年《渴望》的主題曲:好人一生平安來。
我放下手中的電話,很自然地抬起頭來。深秋的天,是湛藍湛藍的,沒有一絲絲雲彩。我在祈禱:假如,人有來生,那麼請老天爺記住,下回不要讓他再有雞胸,腦袋不再偏了。
這就是我,為我的老同學混血兒——有色即鍾才有,提前掛的專家號。
2021.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