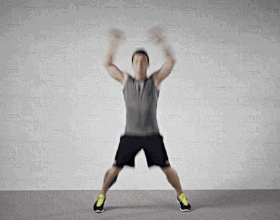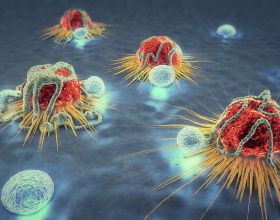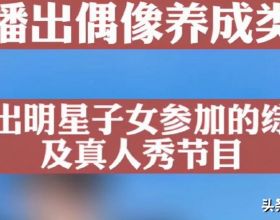視覺化表徵在科學實踐活動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學科,都有大量的視覺化表徵。尤其是隨著計算機成像技術和計算機製圖學的迅速發展,計算機將資料轉換成電腦圖形、影象,讓我們能夠透過視覺化表徵直接獲得關於研究物件的生動翔實的影象和畫面。視覺化表徵在科學實踐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科學實踐中的視覺化表徵有哪些特徵?是否存在刻畫科學活動中視覺化表徵的一般性框架?視覺化技術與科學家認知有什麼關係?這些問題不僅關係到我們對視覺化表徵本身的理解,還關係到我們對科學家、科學實踐的認識,成為認知科學、科學哲學等領域的新話題。
表徵的多樣性和變化性是科學中視覺化表徵的最主要特點。大多數科學研究的目標,是透過簡單、穩定的特徵捕捉複雜的變化過程。比如,透過晶體結構的穩定特徵解釋複雜X射線衍射的動力學;用諸多節肢動物化石的印記形態解釋早已滅絕的生物的生命過程。為了解釋新的或異常的現象,獲取新知識,科學家要擺脫靜態、2D(如繪圖和狀態描述)的表徵形式的約束,在 2D形式(如模式和圖表)、3D形式(結構模型)和4D形式(時間或過程模型)之間進行轉換以改變視覺化表徵。因此,構建與變化模型,進行推理和檢驗,成為視覺化表徵的重要環節。
視覺化表徵推理的一般框架
在一系列案例研究的基礎上,古丁(David C. Gooding)提出了一個囊括視覺化表徵重要特徵的一般框架:模式—結構—過程框架(Pattern-Structure-Process schema,簡稱PSP框架)。PSP框架充分捕捉到視覺變化的特點,呈現出視覺化表徵如何在科學活動中變化的一般情況。PSP框架中最基本的要素是三個節點:模式(草圖或圖表)、結構模型、過程模型,前端的源影象和後端的預測現象也在這一框架之中。此外,該框架還包含各種推理關係。推理關係要麼直接透過成像技術完成,要麼需要動用領域知識(domain knowledge)。從源影象到模式是由成像技術直接完成的,從模式到結構模型、過程模型再到預測現象用到的是領域知識,過程模型到結構模型再到模式的反向推理透過成像技術完成。推理的方向取決於是否需要增加或減少表徵的複雜性和資訊內容。
正向推理很容易理解,反向推理操作發生在如下情況:隨著科學家積累了越來越多的資訊,模型變得複雜難以使用,為應對這種複雜性,需要抽象表徵系統發揮作用。比如,利用微積分、費曼圖等數學工具,根據嚴格的轉換規則進行符號操作,提取繁雜視覺化表徵中的關鍵資料,實現科學理解、分析和應用。另外,表徵模型的潛在解釋和評估涉及各個節點之間推理結果的相互印證,如果結構模型與過程模型相互融貫,則意味著是對現有和預測現象的最佳解釋。比如,在古生物學中,透過視覺化技術,完成從各種古遺蹟照片(源影象)到模式的抽象特徵推理,表徵出已滅絕生物的可能特點,並參考結構模型的特徵,將事實資訊與相關領域的知識結合起來,從模式到結構模型再到動態模型的視覺化推理過程與生物形態、生理過程、生態因素(如食物來源和捕食者)以及地質過程這些領域知識有關。在對假設、表徵物件的可能特徵進行測試時,成像技術和模式可以發揮識別作用,透過比較,可以得出這些假設和預測是否與已有的化石資訊一致。將這些圖表和照片與從動態模型中推出的新現象聯絡起來,能夠得出化石痕跡的真實特徵。並且,新的資訊可以反過來促使科學家重新評估源影象中的表徵具體代表什麼。因此,PSP框架展現出視覺化表徵的一般過程,體現了科學實踐過程中生物要素與社會要素之間的辯證統一、領域知識與視覺化技術的辯證統一、科學發現過程中解釋性與創造性之間的辯證統一。
視覺化表徵與科學家認知
對科學實踐中視覺化表徵基本特徵、一般框架的探索,可以看到,視覺化技術提高了科學實踐的效率。不過,科學家的認知在視覺化表徵中的作用依舊不可替代。
第一,視覺化表徵過程中,視覺化技術需要同科學家的認知能力聯絡起來,產生和變換意象。視覺化技術所基於的認知科學理論傾向於根據複雜性和抽象性對影象進行排序,強調維度的重要性。馬爾(David Marr)的多層次視覺理論展現了場景在視網膜上的二維視覺陣列到作為輸出的世界的三維描述,這一過程實現了場景的連續三維渲染,是從感官輸入到3D模型的單向過程。與此不同,科學實踐中的視覺化表徵推理是非線性的、遞迴的,因為科學家們不斷地在生物賦予的感知過程與其習得的專家感知技能之間轉換。不同型別的表徵會呼叫一系列認知能力,並對錶徵技術提出不同的要求。例如,在使用心算、算盤、筆算或是計算器進行算術計算時,每種技術都結合了一種表徵形式和一種程式,而每一種都會組合不同的認知能力。
第二,視覺化表徵涉及科學家內部心理表徵的外部化,展現了個人心理意象與公共表徵之間的密切聯絡。內部表徵及心理表徵與科學家的心理活動有關,存在於觀察者或者學習者的心靈之中,是私人思想的一部分。儘管科學家的個人心理表徵有著重要作用,但科學實踐中的視覺表徵終歸是心理—物質混合的系統,在這種系統中,不存在內部和外部知識的二元論。並且,只有科學家將個人的想象、思考、信念這些內部表徵以影象、論文、程式等成果這些外部表徵的形式呈現時,將個人意象轉化為公共表徵時,對科學的進步才具有真正意義。
第三,科學實踐中視覺化技術的運用與科學家的認知目的密切相關。具體如何透過結構模型、過程模型進行表徵,不同的影象、模型之間如何轉換,關乎科學家的目的和意圖。正如吉爾(Ronald N. Giere)的科學模型意向性表徵觀刻畫的:科學中的表徵是科學家為了滿足某種目的,出於自身意圖使用模型進行表徵的活動。例如,關於水可以構造不同的模型,如需表徵水的擴散或布朗運動,最好採用水分子集合模型;至於表徵水透過管道流動,則使用連續的流體模型更合適。可見,科學家使用的表徵是科學發現中解釋性、創造性之間相互作用的一部分,其中表徵是可塑的和審慎的,看似相同的影象或物體能以不同的方式發揮作用——比如是為了解釋異常現象,還是挑戰已有解釋,或是成為解釋的證據。
總而言之,PSP框架可以解釋科學實踐中視覺化表徵的變換特徵:透過源影象推理與構建出模式和結構模型、過程模型等視覺化表徵形式,進行預測和假說檢驗。這說明了從純粹影象到各種視覺化表徵之間複雜的轉化關係,表明人類認知的連續性以及被機器部分取代的情況。計算工具如模擬成像技術一樣,以人類可以解釋和理解的方式重現資料、幫助解決更復雜的問題。然而,視覺化表徵中的變化操作卻依賴於科學家主體的專業知識、認知目的和認知能力。科學主體的積極操作而非計算成像技術,才是視覺化表徵中最關鍵的要素。
(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金一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