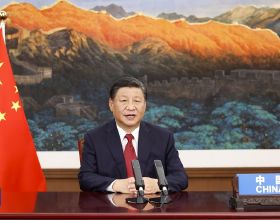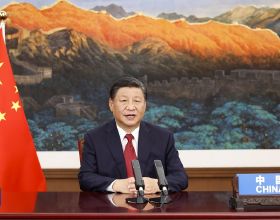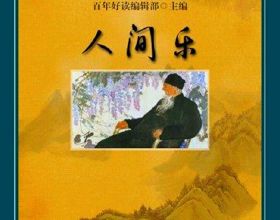1939 年 4 月中旬。
一望無際的東海洋水面,平靜的出奇,顯得格外蒼茫,一艘輪船正匆忙行駛。
船上,是與家國道義背道而馳的汪精衛。
自河內遇刺後,汪精衛有如驚弓之鳥,驚惶萬分,和日本方面協商獲得允許後,便第一時間乘船離開河內,準備赴上海寄身租界託庇於日本人,他的目的並不僅僅是為了保命而已。
大難不死,絕地反擊,汪精衛的心中,藏著一股子倔強和頑強。他計劃招兵買馬,還都南京。
空寂的海面上,輪船和輪船上的人就像是被世界遺忘,偶有幾隻海鷗長鳴而過,嘲笑著這個滑稽的“中國人”。
幾經周折,輪船終於快駛入上海,汪精衛站在船頭,看著那座越來越近的繁華大都市,長舒了一口氣,莫名有一種“遊子歸鄉”般的心境,但顯然,這種心情與他的處境顯得格格不入。
此時的汪精衛,就是一個過河之卒,只有一條路走到黑。
正在汪精衛思緒萬分之際,站在他身旁的陳璧君柔聲說:
兆銘,丁默邨、李士群他們已經透過周佛海表達了參加和平運動的誠心,日本人也答應將丁、李掌握的特務機關撥給我們。我們在上海是有力量的。
陳璧君一句話,多少讓汪精衛有了幾分底氣。他很自信地認為,一到上海,一定有不少老部下投奔自己,必然可以大幹一番。
抵達上海後,汪精衛一行住在愚園路一一三六弄,與極司菲爾路相隔不遠。
暗流湧動的大上海,汪精衛的歸來,掀起了不小的波浪。如他所料,風聲傳開後,上海大小漢奸,如傅筱庵、陳群、盧英等紛紛前來向這位前國民黨副總裁輸誠,汪精衛一一傾心接納,其中,就有手握特務機關的丁默邨和李士群。
汪精衛對丁默邨十分客氣,一見面,就如同舊友重逢,“默邨,好好幹,還都成功你就是和運的功臣了。以後政府裡會有一個適當的職位給你。”
李士群並沒有與上司丁默邨一起,而是晚一步單獨拜訪,他想要攀上汪精衛這個“高枝”,既撈銀子,又做官撈權,說不定還能壓丁默邨一頭,這是他的小算盤。
李士群見過汪精衛後,立馬拍胸脯表忠心:“汪先生,我與中統、軍統有不共戴 天之仇,不是我死,就是他亡。士群一定誓死追隨汪先生,將和平運動進行到底!” 汪精衛很高興,李士群看起來可比丁默邨要精明能幹得多,隨即問道:“士群,好好幹。你年輕有為,大有前途!你覺得默邨的領導才能如何?”
好傢伙,這要是在職場中,毫無疑問就是一道送命題。
但李士群並不在乎,他並不甘心居於丁默邨之下, 也並不害怕得罪他,於是回答:“丁大哥的領導才能是極好的。不過他有兩個毛病,一是貪錢,二是亂 搞女人。”
先肯定才能,再補充些看似無關痛癢的毛病,天衣無縫。
汪精衛一聽,頓時臉色大變,對丁默邨的印象也隨之大變,他一向認為,作風不端,遲早會斷送。
李士群小心翼翼的觀察著汪精衛的臉色,顯然,他的這句小報告起到了效果,於是準備再添一把火,他大膽而委婉的表示,丁默邨雖然是他的上級,但大部分實權卻掌握在自己手中。言外之意,就是他比丁默邨有用,提拔丁不如提拔他。
不久,汪精衛在日本方面示意下,召開了非法的偽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的目的是修改《國民黨黨章》,把“總裁制”改為“主席制”,以便取得“國民黨主席”的法律地位,利用國民黨代表的身份與所謂“各黨各派”的漢奸們拼湊所謂“中央政治會議”,進而成立偽國民政府。 “六全大會”後,汪精衛在家裡召開了“六屆一中全會”,成立了汪偽國民黨中央黨部,並給予七十六號一個名義: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務工作總指揮部(簡稱特工總部)。
一個讓人聞之色變的魔窟,自此誕生,丁默邨為主任,副主任為李士群,警衛大隊長是上海灘有名的流氓頭子吳四寶,有了日本方面的支援,七十六號迅速壯大,組織架構格外龐大,分三隊四廳,紀律嚴明,分工明確。
就在汪偽勢力逐漸壯大之時,遠在重慶的蔣介石,卻膈應得慌。
一天正午,戴笠奉召來到蔣介石的辦公室,忐忑不安地推開門。雖然是白天,蔣介石辦公室的窗簾卻是拉上的,電燈明晃晃開著,頗有些扎眼,蔣介石坐在厚軟的沙發上,消瘦挺直的身子投下一抹陰沉沉的影子。
“雨農,來了,坐。”蔣介石正低頭看著一本書。
戴笠並不敢坐,刺汪失敗,如今汪精衛捲土重來,他有很大的責任。
蔣介石念出書上的一段話:“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唸完以後,抬頭問:“雨農,知道這是誰的話嗎?”
戴笠畢恭畢敬地回答:“這是王陽明先生的話,語出《傳習錄下》。”
戴笠當然知道,蔣介石崇尚理學,又尤其對王陽明崇拜至極,為了投其所好,戴笠也下了不少功夫,對理學書籍日夜背誦,早已熟記在心。
蔣介石滿意地點了點頭,又問:“那麼陽明先生的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
戴笠短思幾秒後,才小心回道:"學生體會,陽明先生是說人看見花時,花才存在;看不見花時,花便不存在……”
戴笠還未說完,蔣介石便惡狠狠地說:“可是我看不見汪精衛時,汪精衛照樣存在!”
該來的總是會來,每次挨批評都要拐個彎,戴笠也司空見慣了,瞠目不知所對。
蔣介石又怒氣衝衝說:“哲學問題和現實問題不是一回事!我要求你清理汪精衛,可是你在河內只打死一個替死鬼。現在汪精衛連偽‘六全大會’都開了,又知道我的許多秘密,公佈出來,後果不堪想象!你的工作怎麼做的?”
戴笠嚇得大氣不敢出,小聲答道:“學生一定選派得力人員,在上海乾掉汪精衛!”
“你打算派誰去?”蔣介石很喜歡戴笠這一點,一問便有計劃。
“陳恭澍。能力不錯,對汪精衛也很熟悉,河內刺汪是他主持的,正好可以將功贖罪。”王天木投汪,戴笠元氣大傷,好在陳恭澍還可堪大用。
從蔣介石的宮邸回到戴公館,戴笠驚出了一身冷汗,事不宜遲,他命人準備一桌豐盛的酒席,然後派人去叫陳恭澍。
陳恭澍自從行動失敗後,被戴笠冷落了半年,此次召見,他不知是兇是吉。
陳恭澍很快來到戴公館,多年殺手生涯讓他變得陰鷙而沉穩,一掃忐忑換上了一張神色自若的臉,進入客廳,看見已經擺好的酒席,心裡放鬆了許多。
戴笠含笑迎上來,拉著陳恭澍入座,一邊倒酒,一邊寒暄,彷彿從前的冷落從未有過,陳恭澍也是見臺階就下,一掃心中不快,與戴笠開懷暢飲,微醺之時,還一展歌喉,唱了幾句《長坂坡》。
酒過三巡,戴笠再次為陳恭澍滿上一杯酒,徐徐說道:“恭澍弟,又有重任要倚托你了。”
所謂靜極思動,賦閒半年的陳恭澍一聽有任務,一下子來了興趣。
戴笠不緊不慢他說:“我想派你去主持上海區的全域性工作。你最重要的任務是繼續組織刺殺汪精衛,這也是校長的命令。汪逆現在已經收容了丁默邨和李士群,手下有了人馬,比在河內時更不好辦。但你要堅持,一次不成功,就來多次,總之要纏刺到底。千方百計破壞他組織偽政府的陰謀,另外,你還要發展上海的組織。”
這可是重任,陳恭澍之前的不快徹底消散,他堅決地回答:“雨農兄把這樣的重任交給我,我一定不遺餘力去做!河內辱命,我對汪逆恨之入骨。到了上海,我一定不會讓他有好日子過!”
戴笠滿意地點點頭,又加了幾句:“王天木是你的老朋友,他投了敵。我派吳安之去勸過他,他不聽從。你如能勸勸他更好,否則執行家法幹掉他!”
就這樣,陳恭澍便攜眷來到上海,風風火火的就任軍統上海區區長。上海區為陳恭澍擺了接風酒,眾人喝酒直到夜深。
夜深的大上海,依舊是九陌紅塵、目迷五色。有錢而不知亡國恨的人們在五光十色的廳中狂歡作樂,而那些關心民族命運的人則在黑夜裡揪心地痛,無聲地嘆息。 陳恭澍面對此景,深吸了一口氣。
在燈紅酒綠的背後,陳恭澍彷彿看到了黑暗處殺手們血紅的眼睛和他們手中冒煙的槍口、滴血的匕首,他也想到了王天木,他想起北平刺張時的驚天一槍, 想起和王天木共同踏入血淋淋的殺手生涯,想起那時的點滴往事,一種朋友之情濃濃地襲來。他沉思有頃,讓人帶一封信給王天木。
作為一個殺手,他深知飲酒作樂只能是暫時的享樂,過了今夜,他便要振作起來,打起十二分精神,整頓組織,開展行動,既為了殺人,也為了自存!
第二天,陳恭澍首先對滬區本部指揮中心作了一些安排和調整,陳恭澍就地發展成員,組建了第八行動大隊,並吸收了三四十名愛國青年成立抗日殺奸團。
在忙忙碌碌中,日子悄悄而過。這一天,陳恭澍收到了王天木的回信,信中說:“兄信已悉。戴老闆行事乖情悖理,餘誓不回頭。感兄盛意,他日殺場相逢,當避兄鋒芒。”
短短几句話,一下子使陳恭澍眼前浮現出王天木那張老江湖的臉,那熟悉的似笑非笑的狡猾眼神。
陳恭澍一聲嘆息,望向窗外,只見烏沉沉的雲直壓下來,一道閃電劈向遠方,接著是驚人的雷聲。
這末世光景,似乎在向他宣告,一場慘烈的交鋒,已經拉開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