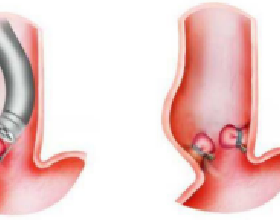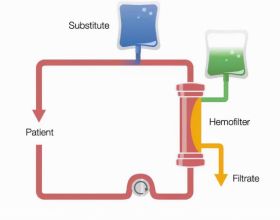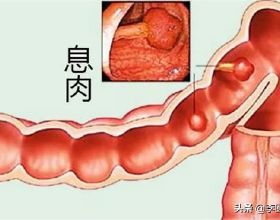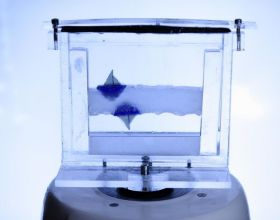一九三六年十月,我紅軍西路軍渡過黃河,向甘肅、新疆地區進軍,那時,我是三十軍軍長程世才同志的警衛員。國民黨“五馬匪幫”像毒蛇似的纏住我們,一路上,幾個旅的騎兵對我們夾擊圍攻,每天都有決死的戰鬥。
半年以來,我們在損失慘重之後衝出了重圍,陷入了彈盡糧絕的境地。部隊在荒無人煙的大沙漠上艱難地行進,找不到野菜和水,即使遇到幾戶人家,也很難買到糧食,什麼時候遇到野牛群或野羊群才能填飽一次肚皮,但這總是餓上一兩天才有的奇遇。
我們嘴唇裂開了血口,嗓子燒得幹疼,在這時用尿來解渴是很普通的事,但是尿水也是很少了。
氣候愈來愈壞,生長在溫暖南方的指戰員,穿著破破爛爛的單衣,忍受著零下二三十度的嚴寒與風雪的襲擊,手腳凍裂了,有的同志凍掉了手指和腳趾,但是紅軍的行列畢竟還是艱難地向西移動著,最終我們忍著飢餓寒冷到達了新疆東面的星星峽。
星星峽只有幾戶人家,部隊吃住仍很困難,除了少部分人住在老鄉家裡,部隊仍住在沙漠上。我到星星峽之後就當了警衛班長。
這天清早,我們排長忽然把我叫了去,交給我一個簡直可以說是新奇的任務。
排長嘴唇抖動著,沒法掩飾他的激動,慢慢地說:“你們八點三十分後,到村子南面兩里路的地方去,佈置好警戒,十點鐘後有蘇聯飛機來給我們送吃的!聽見了嗎?送吃的來……”
“蘇聯的嗎?飛機……”
“是啊!同志,想想吧!這麼困難,蘇聯幫助我們……”
我簡直以為自己是在做夢,但是,這一刻卻是即到的現實啊!
接到這個任務,我的心就不能安靜下來,越想越是高興。
在這萬分難忍的飢餓中,想到在遙遠的地方有蘇聯同志關心我們,幫助我們,我除了用感激這兩個字來形容我當時的心情,再也找不到更確切的字眼。
村南兩里路的地方,說是飛機場,實際上只是一片比較平坦的沙漠。四面看看什麼也沒有,除了星星峽以外,大地全被厚厚的沙子覆蓋著。這個地方飛機怎能認得出來呢?要是找不著我們怎麼辦?
我把全班同志分散開,就坐在沙漠上等著,看看天,晴朗的空中連一點雲彩也沒有。太陽好像比往日升得慢,心裡只盼著它快到當頭,那時就會有從蘇聯飛來的飛機,就會有吃的了。
“注意點,好好聽著,別睡著了。我們是來接飛機的,別讓飛機叫醒咱們,那就太不禮貌了。”我一再叮囑戰士們。
我聚精會神地聽著,不時看看西北方向的天邊。總想在飛機還沒飛到頭頂時就提前發現它,好眼看著它一點點飛過來,但是又總怕自己聽不到飛機聲。
好容易把太陽盼到了當頭,還是看不見飛機,連聲音也聽不見。難道不來了嗎?還是改變了時間?
唉,世界上再也沒有比等待更讓人著急的了,何況又是等待蘇聯飛機,我真是恨自己的眼睛看得太近,耳朵也聽不遠。
正當我納悶的時候,突然聽到徐英文同志喊:“班長,來了!來了!”我們都急忙站起來,沿著徐英文指著的方向看去,可還是什麼也看不見。但是細聽聽,真的聽到北方有一種輕微的“轟隆”聲,同志們都喊著:“來了!來了!”
這時候,大家都是又高興,又著急,不知不覺地喊了起來,跳了起來,跳動的身體中還有一顆火熱的心也在劇烈地跳動著!馬達聲愈來愈大了。
飛機上的蘇聯同志,也許看到我們這十幾個連蹦帶跳的人了吧,他們直奔我們這個方向飛來。飛機飛得很矮,馬達聲卻響徹了天空。四架飛機低低地飛過我們的頭頂,我抬頭看著這四架銀色的雙翼飛機,高喊著,一點也不害怕。
過去我見到飛機就躲,因為那是國民黨轟炸掃射人民的飛機,這是蘇聯的飛機,它給我們帶來了友誼和吃的!我一直在喊,不知喊了些什麼,只覺得自己的心都快被喊出來了!
飛機繞了兩圈,大約有兩三百米高,這時我們模糊地看到飛機上的駕駛員還都笑著向我們招手哩,我們更高地跳著招手,更大聲地喊。
正喊時,飛機打開了門低低地拋下一個個箱子,接著又繞了一圈,駕駛員再一次向我們揮揮手,就又向北飛去了。
這時候,我們才好像從夢中醒來一樣,也在這時才發覺胳膊酸了,嗓子也啞了。
我們立刻朝箱子跑去,幾十個箱子東一個西一個深深地陷在沙子裡,有的是完整的牛皮包著的大木箱;有的已經摔碎了,露出了一包包的麵包、餅乾或是芝麻餅。我們圍著這一大堆吃的,不由得想到這都是從社會主義的國家剛運來的啊,都是幸福的人做成的呵!
麵包的香味撲鼻,我真恨不得馬上吃口嚐嚐,但是我們還是抑制住了自己,很快地把這批珍貴的禮物運到了駐地。
星星峽這個小村落,立刻像過年似的熱鬧起來,每個紅軍戰士都抱著一大包東西高高興興地回去了。
我手裡拿著這些東西,心裡感激著蘇聯人民雪中送炭般的援助。分給自己的麵包餅乾的香味,使我想到很多東西。我似乎握到了蘇聯人民溫暖的手,看到了他們的幸福生活。這些東西,不僅使我們有了為革命繼續工作的能力,而且使我們更加嚮往將來一將來我們也能有這樣一個幸福的國家。
一連三天,我們忙著把飛機接來送走,又忙著把一箱箱的吃的運回來。我們駐地附近,糧食已堆成小山,我們再不愁沒吃的了。
第四天早晨,首長告訴我:“今天飛機要給我們送棉衣來,要我們好好警戒,並幫助蘇聯同志卸東西,因為飛機這次不再是空投了,而是要降落在沙漠上。”
我聽了這個訊息更加高興起來:這些蘇聯人真好,給我們送吃的又送穿的!我暗地下了決心,一定要趁今天飛機降落的好機會,好好和那幾位蘇聯同志親熱親熱,再看看飛機是個什麼樣子。
我本來有一點擔心人家看我這身破爛衣服笑話,又一想,我們都是無產階級,哪能會笑話呢?蘇聯同志決不是那樣的人。
和往日一樣,四架飛機在中午到達了,他們盤旋了一週,貼著沙漠向下飛來。
落地的時候,飛機在沙漠上一跳一跳,帶起一陣陣黃沙,馬達震天地響著,飛機頭上的螺旋槳轉動得愈來愈慢,最後終於成了一根棍棍,飛機停在距我們二百米遠的沙漠上。
不知怎的,我看到飛機著陸反倒呆住了,忘記了跑過去和他們親熱了,只是愣愣地站在那裡,直到看見每架飛機出來兩個人直向我們奔來,才想起來跑過去,我們像老朋友見面似的熱烈握手。
兩個紅臉的蘇聯同志走到我面前,他們都穿著黑皮衣服,皮靴,身材高大,我要抬起頭來才能看到他們的藍眼睛,其中一個拍拍我的肩膀,又伸出大拇指向我比來比去,然後他們兩個又說了些我聽不懂的話,我正在挑起大拇指稱讚他們的時候,沒有防備地就被他們抱了起來,一下把我扔到半空中,我笑著搖手,但是他們不說話,只是一邊喊著一邊笑,連扔了我好幾次。
我們和蘇聯同志一起將棉衣卸下以後,我用手比劃著表示要看看飛機,他們就拉著我向飛機跑去。我爬到飛機裡去坐坐,雖然座位很舒適,可是那一個個怪里怪氣的表,和一條條的電線卻弄得我眼花繚亂。
蘇聯同志笑著把我扶下飛機以後,就請我們全班站好,拿出相機給我們照了一張相,又要我們和他們合照一張。
臨走的時候,他們把身上所有的扁盒菸捲全送給了我們,又和我們擁抱告別。蘇聯同志是多麼真摯地愛著我們,多麼支援我們所幹的事業,又是多麼熱烈地祝福著我們啊!
當天,我們每人領到一套灰色的新棉衣,一頂皮帽,一雙棉鞋,還有兩套襯衣(據說這些棉鞋襯衣是用汽車運來的)。脫掉我那一身破爛棉衣,穿上了新棉衣身上暖和起來了,再也不怕西北的壞氣候了。
不久,陳雲同志從迪化(今烏魯木齊市)來接我們,我們分乘四十八輛汽車,向迪化開進。其中一輛汽車載著我們的破爛衣服和劣等武器,據說是要運到莫斯科去展覽的。
在迪化的蘇聯醫院裡,醫生們為我們檢查了身體,有病的得到了治療,就是沒病的也要連吃三天白色藥片,據說這是一種“保健藥”,在蘇聯也只有高階幹部和大學教授才能吃到,而他們對我們一個普通的紅軍戰士,都看得這樣珍重。
一個蘇聯老醫生向我們說:“你們是中國革命的種子,比黃金還寶貴。”
這些雖然是幾十年前的事了,但回憶起來仍然猶如昨日,一切一切都歷歷在目!
鮮開端,又名鮮克德(1914年7月——1999年8月),四川省閬中人。1933年初,鮮開端在鄉蘇維埃報名參加了紅軍,1934年被編入紅30軍88師二六八團一營,先後任戰士,傳命兵、班長、營團通訊員。1934年八九月,又隨軍經旺蒼進入蒼溪,參加了黃木埡戰鬥。1935年3月28日在河溪關時興場渡口渡過嘉陵江,踏上長征路。
長征中被紅88師長程世才看中,當了師長警衛員,程世才升任30軍代軍長、軍長後,又跟軍長三過草地爬雪山,渡黃河在甘肅一條山編入西路軍。與馬步芳、馬洪奎軍閥慘烈鬥爭,跳出敵包圍圈後,進入新疆迪化。1937年7月14日鮮開端跟隨李先念、程世才等被中央接回延安。
從那時起鮮開端被安排在王諍開辦的電訊班和延安黨校培訓。在這之前西安事變中,張學良兵諫蔣介石成功後,國共第二次合作,工農紅軍被改編為八路軍。那時黨中央在國統區建立了16個八路軍辦事處,在中央選派警衛員時,鮮開端因有文化,機靈反應快,被選為周恩來和李克農的警衛員。1937年初冬,隨周、李在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任警衛員兼譯電員。1937年底,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因日軍狂轟濫炸,辦事處人員被迫遷徒湖北漢口安仁里長春街,鮮開端亦隨周恩來、錢之光、葉劍英、郭沫若、羅炳輝等到達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仍作警衛員譯電員。
1946年,隨周恩來回延安,在延安黨校學習後,先後任120師司令部通訊科長;同年赴東北作戰任第三縱隊通訊科長,在陳雲、蕭勁光麾下工作。
1950年10月奉命抗美援朝,在特殊崗位上戰鬥了三年多,1953年從朝鮮返回後先後作長春市兵役局副政委、師軍事法院院長,九四五部隊政委等職。
1979年,離職在錦州紅軍院休養。榮獲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三級解放勳章、三級獨立自由勳章,三級八一勳章,中國人民解放軍二級紅星功勳榮譽章,朝鮮自由獨立勳章(二級)。一九八八年又被授予紅星勳章,一九九九年七月五日在錦州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