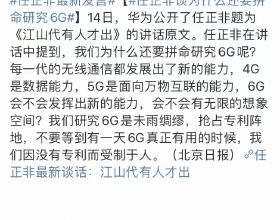一部里程碑式的長篇小說
——《我們的土地》管窺
文/林一安
拉丁美洲文學爆炸四大主將之一、墨西哥著名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1928—2012)於1968年動筆、1974年寫畢、1975年面世的長篇小說《我們的土地》(Terra Nostra),經我多年磕磕絆絆、跌跌爬爬的拼力翻譯,終於出版了,我總算抵達這座金字塔的底下;因為與譯者一樣,要面臨眾多挑戰,我們中國的讀者能不能攀登頂峰,坦率地說,尚需許多時日。
這部被譽為“里程碑式的長篇小說”“書中之書”“文學百科全書”“新大陸交響曲”“拉丁美洲的尤利西斯”的作品,有的評家甚至認為,它標誌著二十世紀敘事文學的開端與終結。
富恩特斯生於墨西哥一個外交官家庭,祖籍德國。童年和青少年在美國、智利和阿根廷求學。大學期間,在國內攻讀法律,於1955年獲正式律師資格。長期供職外交界,曾於1975—1977年任墨西哥駐法國大使。以處女作短篇小說集《戴假面具的日子》(1954)為起點,一生共創作了六十餘部作品。主要有長篇小說《最明淨的地區》(1958)、《阿爾特米奧·克羅斯之死》(1962)、《換皮》(1967)、《神聖的區域》(1967)、《我們的土地》(1975)、《淵深源遠的家族》(1980)、《克里斯托瓦爾·諾納託》(1987)、《狄安娜,孤寂的女獵手》(1993)、《鷹的王座》(2002);中篇小說《奧拉》(1962)、《美國老人》(1985);短篇小說集《盲人之歌》(1964)、《明澈的疆界》(1995);劇本《獨眼的是國王》(1974)及文學評論集《西班牙語美洲新小說》(1969)、《塞萬提斯或閱讀的批評》(1976)、《勇敢的新世界》(1990)等。曾獲加列戈斯國際文學獎(1977)、塞萬提斯文學獎(1987)、阿斯圖里亞斯親王文學獎(1994)、國際西班牙語文學創作獎(2012)。
富恩特斯是位極其獨特的作家,他從來沒有寫過兩本同樣的小說;而《我們的土地》,有評家認為,不僅是富恩特斯,而且也是整個西班牙語美洲有史以來最雄心勃勃、篇幅最為浩瀚,也是最重要的長篇小說。
富恩特斯不按常規出牌,他縱橫筆墨,恣肆汪洋,這部長篇小說追求的目標就是鍛鍊和造就一種新型的讀者。它是一部閱讀永遠也不會終止的小說,每次開卷閱讀,讀者會覺得越入佳境,一次比一次讀得入味。
小說分為三個部分:一、舊大陸;二、新大陸;三、另一個大陸。全書凡144章,約閤中文近百萬字,是迄今為止西班牙語文學中文翻譯字數最多的長篇小說,甚至超過《堂吉訶德》。
只需稍加瀏覽,我們就能發現,《我們的土地》具有歷史小說的一切特徵,只有該書第一章和最後一章即第144章,故事均於1999年在巴黎鋪陳展開。之後,小說描繪的情事都發生在十六世紀的西班牙及其勢力範圍——美洲和地中海。小說的時間節點是西班牙建造埃萊斯科里亞爾修道院和發現新大陸。情節圍繞著西班牙國王費利佩二世鬼迷心竅的願望、三個海上遇險者探尋自己的身份以及伊莎貝爾王后渴望自由而發展。
《我們的土地》的故事始於2000年前夕的巴黎。波羅·費博,小說裡的一個人物(獨臂人,如同將寫出《堂吉訶德》的那位編年史官),一個獨臂金髮青年目睹了一位九旬老婦誕生了一個嬰兒,在異常的環境下,參加了一位每隻腳長著六個腳趾、背上有紅十字印記的小孩的洗禮。一封神秘信函宣告,盼望數百年之後,他終將降臨世間。信函還命令,以約翰內斯·阿克里帕(該名為希伯來文,意為“榮耀歸於耶和華”)作為名字為孩子命名洗禮。而這個孩子,就是“諸多原先王國的延續”。那金髮青年身上掛著紙板,替一家咖啡館當廣告推銷員。他在目睹了盛行一時的類似生日典禮以後,在一座橋上與女藝人塞萊斯蒂娜不期而遇。她似乎認出了他,稱他為胡安。那獨臂年輕人從藝術橋掉進了塞納河。正在水中沉沒的當口,那姑娘把一個帶有標記的綠瓶子扔進河裡,自己變成一個新山魯佐德,給我們講述一千零一個將把小說完成的故事。
我們再來看看幾條敘述主線。
大約五百年以前,三個海上遇險者(他們有同樣的缺陷:每隻腳長六個趾頭,背上有紅十字印記)同時來到了災難角。他們被海潮衝到那兒,各拿著一個帶有標記的綠瓶子,瓶子裡還塞有一份手稿。他們中的第一個人,將被西班牙國王費利佩二世的妻子伊莎貝爾王后領走。王后把他暗藏在自己的化妝間裡,當做情人。後來,這第一個海上遇險者就變成了堂胡安,誘姦宮女和修女,取得伊內斯修女的歡心,還在一場決鬥中,結果了修道院院長的性命。最後,在皇家陵墓裡,變成了一尊石像。
第二個六腳趾被海水衝到了災難角。他戴著一副奇特的羽毛假面具,在岸上被費利佩的母后、瘋女王救走,送到她夫君的靈車上。他穿著她夫君的服裝露面了(那死鬼倒領受了假面具和破衣服)。然後,就給暗藏在瘋女王的密室裡,成了傻王子,還被宣佈為儲君。後來,他居然想進入皇家陵墓眾多大理石棺材中的一個,緊挨著堂胡安和國王陛下的遺體,和皇家其他死者一起安眠。
第三個人是侍童兼鼓手(其實是塞萊斯蒂娜)發現的,他老是拿著帶有標記的那個瓶子,被她帶進了皇陵。在那兒,他與另外兩個人相遇了。他與她,還有一位盲人吹笛手共同生活,直到跟他們兩個一起被國王陛下的衛兵抓走。他被帶到國王面前,講述來到新大陸的旅行。
這三個人,也許就是許多、許多年之後的阿格里帕一個人。
他們中的第一個人,是塞萊斯蒂娜和那位貪婪女色的國王、瘋女王的夫君、費利佩二世的父王的兒子。塞萊斯蒂娜姑娘和費利佩王儲成婚那天,國王讓他兒子享受初夜權,卻發現此子不通人道,於是,就把姑娘破了身。後來,她在托萊多的猶太區產下了一個帶有十字印記、每隻腳長著六個腳趾的男孩。
第二個人,是一條母狼的兒子。出生的時候,塞萊斯蒂娜也來了,是她揭露了國王(姦汙她的人)和被圈套夾住的那條母狼獸交的。
第三個人,是美男子國王和他未來的兒媳婦伊莎貝爾的兒子。在她還是一個小姑娘的時候,國王就強暴了她。
這樣,這三個海上遇險者就都是同一個父親的兒子,因此,又都是費利佩二世的兄弟。
關於這幾個人的身世以及彼此之間的關係,我們不難在羅馬暴君提比略·愷撒在臨死之前說的這麼一番話裡,找到蛛絲馬跡:
“……著遺孤阿格里帕某天覆活。該子一身三人,來自母狼之腹……著阿格里帕之三子稍後降生九子,自九而二十七個,又自二十七而八十一,一直至分解為數百萬個體之眾……”
接著,故事便切入十六世紀的西班牙。國王費利佩二世計劃建造埃萊斯科里亞爾修道院,以便在其地下室裡安葬他先祖的遺骨,自己百年之後也於此地安眠。
《我們的土地》的故事也許可以濃縮為這麼一個問題:
“為什麼是三個?為什麼有十字?為什麼每隻腳有六個腳趾?世界如此廣漠,為什麼這三個人在這裡?”
本書無論形式和內容,都十分錯綜複雜,讀者,特別是譯者,必須面臨三大挑戰。
一、語言文字的挑戰
作品中,除了西班牙文原文,還大量使用了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希伯來文、哥特文,甚至墨西哥土著民族語言納瓦特爾語以及文字遊戲般的迴文;不過,如果不是閱讀原文,這些都不是障礙,因為,譯者經多方諮詢查問,都譯成了中文,不會對中國讀者造成太多的困難。
二、知識層面的挑戰
小說涉及的知識層面繁雜龐大,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佛教等)、宮廷、軍事、狩獵、醫藥、習俗、神話、聖經、文學、哲學、繪畫、天文、歷史、地理、數學、物理、動植物,等等等等,無所不及。這些層面的疑難,經過諮詢查問,大致也能解決,讀者倒還可因此而增加不少知識,獲益匪淺。
三、寫作手法的挑戰
秘魯作家巴爾加斯·略薩稱《我們的土地》是一部“全面小說”(novela total),是有一定道理的。
富恩特斯要求讀者,自然也包括譯者,瞭解甚至熟悉世界文學和歷史,特別是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文學和歷史,因為他在作品裡,提及了大量的歷史典故,引用或模仿了不少世界文學著名作家如塞萬提斯、費爾南多·德·羅哈斯、普魯斯特、喬伊斯、雨果、卡夫卡、博爾赫斯、加西亞·馬爾克斯、科塔薩爾、巴爾加斯·略薩、卡彭鐵爾等的句型、段落乃至手法。而且,富恩特斯還把這些作家作品裡的人物變成了《我們的土地》裡的人物,如塞萬提斯本人、堂吉訶德、桑丘、塞萊斯蒂娜、《悲慘世界》中的警官沙威爾和囚犯冉阿讓、《百年孤獨》中的布恩地亞上校、《跳房子》中的流亡者奧利韋拉、《酒吧長談》中的記者聖地亞哥·薩瓦拉,古巴作家卡彭鐵爾的長篇小說《光明世紀》中的表姐弟索菲婭和埃斯特萬等等。
至於寫作手法,富恩特斯還借鑑了西班牙語國家的著名作家。例如,在本書中採用了墨西哥作家胡安·魯爾福的《佩德羅·帕拉莫》、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中的開篇手法。請看:
“許多年以後,倫特里亞神父一定會想起,那個夜晚,他那張床硬邦邦的,讓他睡不著覺,後來逼得他走出了家門。”(《佩德羅·帕拉莫》,原譯文由筆者改譯)
“許多年以後,面對槍決執行隊,奧雷良諾·布恩地亞上校一定會想起,他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百年孤獨》,原譯文由筆者改譯)
富恩特斯一定也認為,這種從未來的角度回憶過去的倒敘手法,值得仿效,它容納了現在、過去和未來三個時間層面:
“許多許多年以後,年邁、孤獨、隱居的國王陛下將會回想起,那天黃昏時分,他最後一次愛撫了伊內斯背上那溫熱的凹窩兒。”(《我們的土地》)
“許多年以後,國王陛下行走在宮內空曠的長廊裡,用一隻手捂住眼睛,為的是免受光線造成的傷害;那光線穿過白色的屋頂鉛皮而滲透進來。他會回想起,他與他青年時代的夥伴最後幾次的會面……”(《我們的土地》)
他還借用了秘魯作家巴爾加斯·略薩的《酒吧長談》中的句型:
“……秘魯是什麼時候倒黴的?秘魯算是倒黴了,卡利托斯也倒黴了,大家都倒黴了,真沒治了……”(《酒吧長談》,原譯文由筆者改譯)
巴爾加斯這部於1969年面世的小說裡的這番話,竟成了當今拉丁美洲國家民眾經常掛在嘴邊的口頭語了。所以,富恩特斯當然不會棄之不用。在《我們的土地》最後一章《最後一座城市》裡,不難看到類似的句型:
“……西班牙美洲是什麼時候倒黴的啊?……倒黴的秘魯,倒黴的智利,倒黴的阿根廷,倒黴的墨西哥,倒黴的世界……”
其實,總體來說,富恩特斯雖然知識淵博,但絕不故弄玄虛,他的文字在許多地方倒還通俗易懂,明白如話;而且,也許他考慮到讀者會審美疲勞,全篇各章長短不一,錯落有致:有的篇章極長,達數萬字;有的超短,僅幾行字。
本書各章人稱的變換,也是作家用來鋪陳故事的一種寫作手段:
我,你,他,我們,你們,他們。有時單獨出現;有時同時出現。例如,在《你是誰》這一章裡,人稱為“你”;《女旅人的獨白》裡,人稱為“我”;《在國王陛下腳下》裡,人稱為“他”。《啟明星》裡,人稱為“我們”;《托萊多的猶太人區》裡,人稱為“他們”;《造反》裡,人稱為“你們”。在《眾聲嘈雜》裡,人稱一會是“我”:“……不不不不,西班牙只容得下西班牙,多一寸土地都不行,一切在這裡,一切在我的王宮之內。請寬慰我吧,我的主啊,上帝啊,真人啊,看看在你神秘的祭臺前面轉身跪下的我吧……”一會兒又是“你”:“……你告訴我,蒼鷹,兇殘的蒼鷹,我漂亮的鷹啊,我該怎麼辦呢?你是我唯一的忠心朋友,是真正傾聽我懺悔的……”
人稱的不斷變化,作家的目的可能是要不斷引起讀者的注意,而人稱出現又故意不標明人物究竟是什麼身份,則恐怕是作家要提高讀者辨別能力的一種手段了。
極為罕見的是,富恩特斯居然還讓宮殿、油畫、鏡子等建築和物件,也出來敘述說話,《我所有的罪孽》《第一道遺詔》等各章均有詳盡的描寫。
宮殿,描繪這項工程的建築過程:
“……裡裡外外,上上下下,在周圍一片廣闊的平地上,堆放著一塊塊花崗岩石料.六十名石匠把式帶著自己的團隊在幹大理石的活兒,牛車拉著石頭過來了。泥瓦匠、木匠、鐵匠、刺繡工、金銀匠和伐木工,在平坦的曠野上,頂著太陽的炙烤,建立起自己的作坊、酒館和茅屋……”
油畫,敘述聖經故事:
“……他們吃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就掰開,遞給門徒,說:你們拿著吃,這是我的身體;這樣做,你們就記住我了。又拿起苦杯喝酒。吃罷晚餐,他說:這是我立約的血,為你們流出來。你們看哪,那叛徒之手,與我同在一張桌子上,與我蘸手在同一個盤子裡……”
鏡子,是本書某一個人物的映照:
“……我們是最後的天使,我們從來沒有見到過天父上帝,我們軟弱無力,我們又能想象出什麼來?我們是上帝最卑微的代表……”
而作家描繪各種人物從不同的視角,對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也別出心裁。如《眾目睽睽》一章:
費利佩國王陛下把所有的人都召喚了過來,但見:
古斯曼的一雙眼睛注視著這一切;
修士兼畫師胡利安的眼睛,注視著這一切;
躲在高高的格子窗後面的米拉格羅斯院長也在朝油畫瞧;
見習修女堂娜伊內斯在這一堆混雜的人群裡發現了這麼多感興趣的方方面面,她又會朝哪兒看呢?
那位新上任的修道院院長、塞維利亞高利貸者、堂娜伊內斯的父親,正用他那雙細長而精於算計的眼睛注視著這一切。
瘋女王那副閃爍發亮的目光是勝利的目光。
魔幻現實主義手法的運用,富恩特斯也是得心應手,遊刃有餘,而且更大膽,想象力的翅膀展開得更為高遠。請看:
本書《初更夜》一章裡,在作者筆下,王后陛下居然變成了一隻蝙蝠:
“……變成一隻蝙蝠的王后陛下從地下室到臥房來回飛了好幾次,每次都在她殘缺不全的趾骨間帶回一根骨頭和一個耳朵,一個鼻子和一隻眼睛,一條舌頭和一條胳膊。就這麼從墳墓裡偷,末了,把偷來的部件,在床上連成完整的一個人……”
“王后陛下點亮了煙囪,把一隻鍋放在火上,把胡安的指甲和頭髮扔進鍋內;接著,加上實際上是一棵阿拉伯樹木的淚水和猶如樹脂一般凝結、變硬的安息香脂。然後,將其一起攪打,等其煮開。最後,把這麼形成的蠟從火爐拿到床鋪,滾滾燙燙地澆到床上一塊塊已成木乃伊般的肉上,抹上蠟,把分散的部件連線起來,直至成了人形……”
在《水日》那一章裡,有這麼一個怪物:
“……伐木人那張臉上,什麼也沒有,只有一對閃爍發光的眼睛,一條時伸時晃的舌頭,它出奇地長,拖在嘴巴外面。那張嘴巴像是給刀削了似的,受著傷,露出了傷疤,還沒有嘴唇。這個怪物的肋骨飛快地一張一合,猶如風中兩扇大門。每次一開啟,就露出一顆正在跳動的活心來,還像他那對眼睛一樣,閃爍發光……”
《老人的傳說》中對土地女神的描繪:
“從女神的軀體裡,誕生了萬物……”
“從她的頭髮裡,生長出樹木;從她的面板裡,生長出花草;從她的眼睛裡,生長出水井、水泉和洞穴;從她的嘴巴里,生長出河流;從她的鼻孔裡,生長出山谷;從她的肩膀,生長出群山。”
故事差不多講完了,富恩特斯又使出另一個絕招。在《復原》這一章裡,作家描繪宮廷畫師胡利安被派去修復一幅古代油畫,讓其再現昔日的光輝:
“……那幅畫,老舊不堪,遭人遺棄,數百年來因潮氣、黴菌和照看疏忽,多處損壞……”原來,“……這幅畫是畫在另一幅畫上面的,很難一眼看穿……”
於是,把油畫擦拭乾淨,用刻刀剔除灰泥、黴菌、硬斑,又用油、氨水、酒精、松脂精進行處理,“……油畫的原來面貌便漸漸展現在那一小群藝術家驚詫的眼睛前面……”
果然不出所料,“那是一幅奇特、大型宮廷肖像畫……畫面上,佔據首要位置的,是一位雙膝跪地的國王,他神情悲慼憂傷,手裡拿著一本禱告書,一條機靈的獵犬依靠在他身旁……還有一位,是穿著獵務副總管服裝的男子,他一隻手握著配刀把柄,肩上立著一隻蒙著腦袋的獵鷹,另一隻手緊緊掌控著一群獵犬。左側和背景裡,進入畫面的是一支送葬隊伍,為首的是一個裹著黑布的老婦人,她肢體殘缺,沒有大腿也沒有胳膊,簡直就是一個黃眼珠半身人像,由一個女侏儒拉著大車送她。那矮婆子掉了牙,腮幫子鼓鼓的,短小的身材衣服皺皺巴巴、鬆鬆垮垮的。在她們後面的,是一名鼓手兼侍童,他一身黑衣,灰色的眼睛柔和溫順,嘴唇刺了青。侍童後面,是一副豪華的帶輪靈柩和一大批隨從人員,有各級地方長官、差役、管家、秘書、侍女、工役、乞丐、持戟武士、猶太和穆斯林俘虜。他們護送著這支沒有盡頭、漸漸消失在油畫背景裡的靈車佇列。靈車周圍,是主教、副主祭和各級教士。畫面右側,是一個蹲著的笛手,一個面板油膩膩、綠眼睛凸出的乞丐。他後面,是一個巨大的怪物,它張大著嘴巴;那是鯊魚和鬣狗的雜種,浮游在火海里,吞噬著屍體。畫面中央,在以跪倒在地的國王黑色形象為首的圓圈之後,在原先由一群裸體男子佔據的地方,是三個小夥子,也精光赤條的。他們互相交叉著,背對著觀眾。三人背上,印有十字標記,一個肉十字,嵌入肉內。這幅場景之後,在灰大理石和黑影的深邃背景裡,一群半裸修女漸漸消逝。她們用懺悔苦行帶鞭笞自己,其中最漂亮的一位,嘴裡全是碎玻璃,嘴唇在滴著血。拿著正燃燒著的長長的大蜡燭的教士遊行隊伍。一座塔樓和一名正在觀察不可逾越的蒼穹的紅髮修士。一座與其平行的塔樓和一名弓腰閱覽陳舊羊皮紙文稿的獨臂寫手。一尊騎著馬的修道院院長的塑像。平原上是酷刑、煙霧瀰漫的木樁、刑椅、痛得扭曲變形給綁在木樁示眾的人。戰役和屠殺的場景。種種細節:破碎的鏡子,火堆下從燒焦的土地冒出來的曼德拉草根,燃至半截的蠟燭,瘟疫蔓延的城市,一名戴著假面具、有著鳥喙的修士,遠方一個海灘,修造一半的船隻,手裡握著一把舊錘子的老水手,一群飛逝的烏鴉,兩列消失在畫面邊遠處的隊伍;列隊裡是王家靈柩、花紋大理石墳墓、躺著的塑像、純粹的素描,那是沒有窮盡的接連死亡,朝向無垠的令人眩暈的吸引力。畫底越發諳黑,前方的色彩明亮和諧……”
透過這段描寫,本書長達五百餘年的前後故事便互為呼應,等於是歷史重溫了。
富恩特斯在小說中,對於西班牙殖民者、墨西哥征服者科爾特斯在美洲大陸的暴行大加鞭笞,不遺餘力。例如,在《反光之夜》一章裡,他借這個殖民者之口,使其自行暴露:
“……我是白人,頭髮金黃,滿腮鬍子,騎著馬,武器配有石弓,還配有佩劍,胸前繡有金十字。就是我,放火燒了神廟,毀壞了偶像,開炮打擊這片大陸的武士,可他們的武裝只有長矛和弓箭。我就是半人半馬的怪物,自從我從海岸朝聖以來,我把這一片片田野、這一片片平原,這一片片叢林都毀得荒蕪乾枯,我的馬隊踏平整座整座的鄉鎮,一座座城市被我狂暴的火把化為黑色的灰燼,我下令屠殺金字塔節假日裡跳舞的人們,我強暴婦女,我把男人當成牲口一樣,給他們打上烙印,拒絕承認自己是我一路撒下的私生子的父親,我讓窮人扛起沉重的大包,一路用鞭子抽打他們,我把新大陸的珠寶、牆垣和地板都冶煉成金條,我讓這些地區的居民都傳染上天花和霍亂……”
近代有資料揭露,印第安人自己的暴君對其子民的兇狠殘酷,比之西班牙殖民者有過之而無不及。對於印第安人頭領殺人同樣血淋林的場面,富恩特斯也沒有放過,進行了犀利的抨擊:
“……巫師們在金字塔頂端,遵照……指令,把石頭匕首插進妓女的胸脯,從乳房中間開了膛,接著便直捅脖頸,用他們的泥手掏出了心臟,最後割下了她們的腦袋,把殘缺的屍體堆到金字塔水道一側。女人們的鮮血便從那裡流淌到塵土溫和的平原……”
“……武士們帶著俘虜來到了頂峰,俘虜隨即被司祭接走,從後面捆綁住手腳。很多俘虜來的時候已經昏迷過去,就這樣,給扔進大火,扔進在平臺高處熊熊燃燒的火堆裡去。每個在那兒掉下的人,在火中都形成一個大坑,那裡全都是炭火或火灰。在火中,俘虜翻滾,嘔吐起來,身軀吱嘎作響,彷彿在燒烤一個動物,身體到處都鼓起了水泡。正垂死掙扎間,巫師們用鉤子把他從火里拉出來,拖到大砧板上,在乳頭之間開了膛,把心臟扔到夫人腳下;砍下俘虜的腦袋,把腦袋和分割了的屍體扔到臺階下面……”
西班牙國王治下的工人和農民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在富恩特斯筆下,工人馬丁是這麼說的:
“……國王答應給我們公平,可這是老爺們為了自己而拼命維護的一種公平,是為了更好地壓迫我們,把大量的稅都堆到我們背上,不管是實物還是現錢,幾輩子都繳不完……我們是地上無足輕重的小人物,什麼權利也沒有,而老爺就有權利把我們殺了,我們只准選擇死亡的方式:餓死、渴死和凍死……”
作家筆鋒一轉,又極其大膽、無情地刻畫了西班牙王室的奢靡、黑暗、無恥與淫亂。請看看西班牙王室是一副什麼樣的嘴臉:他們強暴民女(《初夜權》)、大動干戈(《凱旋》《編年史官》)、大興土木(《我所有的罪孽》)、大擺宴席(《深夜的傷害》)、荒淫無恥(《愛情的俘虜》《王子的肖像》),等等等等,無惡不作。
當然,富恩特斯也不惜筆墨,熱情歌頌了新大陸,憧憬新世界的美好、平等和自由。
新大陸不僅土地遼闊,空氣潔淨,物產豐饒,民風淳樸,更重要的是自由平等。請看那是什麼樣的一番天地:
“……我環顧四周,這座蠻荒村落的所有房屋,都是用席子架在四個拱門上建就,彼此完全相同,沒有高財富或者高權力的明顯跡象……”
“……這裡所有的東西都是大家的。男人獵鹿捕龜,女人收檢螞蟻卵、蛆蟲、小蜥蜴和壁虎,用以製作菜餚,而老人善於抓捕長蛇,肉味不賴。之後,這些東西就由大家自然分享……”
總之,《我們的土地》是一部歌頌光明、揭露黑暗、憧憬未來的作品,值得閱讀、借鑑。
近日,哥倫比亞記者安德烈斯·費利佩·奧索里奧向筆者提問:
“依您所見,什麼是翻譯的最大困難?”
筆者回答:
“作家的風格。我認為,體現作家的風格,是世間所有譯家最大的困惑與困難。而富恩特斯的風格,在《我們的土地》裡,又不止一種,這就更加困難了。作家的風格,我們只能朦朦朧朧、隱隱約約地感受到,體味到,例如,博爾赫斯文字簡約、精煉、高雅;加西亞·馬爾克斯大都明白如話,深入淺出;巴爾加斯·略薩語言不故作高深,文體結構繁複但安排有序;而富恩特斯的風格,竊以為則是變化無窮,時雅時俗,時文時白,時高時低,實在難以把握,難以表述。”
的確如此。例如,在《所有的罪孽》這一章裡,他還採用了聖經的筆法,譯者必須亦步亦趨地緊跟。我是這麼譯的,不知道像不像,且看一段:
“……耶穌看見這許多人,就上了山;等他坐定,門徒們就到他跟前來,他便開口教訓他們,說: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你們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財利。”
又如,在費利佩二世的秘書、獵務副總管古斯曼向國王上的一道奏摺裡,為了表現古斯曼文化程度有限,作家用的是不太地道的古西班牙文;因此,為稍加對應,譯者勉為其難地採用了文言文,而且也要不太高明:
“……至神至聖、誠如愷撒之天主教國王陛下……如今,臣一無所有;反之,擁有一切者,乃教會及君子也。臣今老邁貧困,負債累累,現年七十有三矣。年齡如斯,不宜行走於旅次,實應採摘勞動之果實矣……臣請求再三,乞陛下即行降旨,餘不一一,餘不一一……”
最後,我想借用巴爾加斯·略薩的一句話,來結束我這篇文章。
對於《酒吧長談》,作家有這麼一番話來自我評價:
“如果非要我只救出一部我寫的小說,那我就救出這一部。”
那麼,對於拙譯《我們的土地》,我就套用這位秘魯作家的話:
“如果非要我從火裡只救出一部我翻譯的小說,那我就救出這一部。”
作者簡介:
林一安(1936—),1959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德西法語系西班牙語專業。曾任北京外國語學校西班牙語教師、《世界文學》副主編、編審、中國社會科學院翻譯系列正高階專業技術職務評審委員會委員、中國西葡拉美文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來源:北方文學創作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