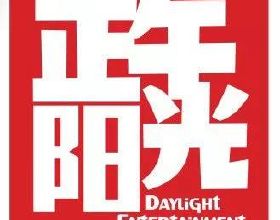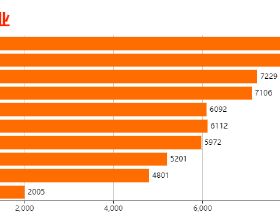有好幾次完成高強度的健身目標,忍不住與家人分享,自己運動之後身體的暢快淋漓,然而,換來的是家人重複過的幾句話:這個習慣很好啊,鍛鍊身體,培養意志力,要堅持下去。不知怎的,身體湧動的能量一下子停滯了。
我突然覺得家人並沒有真正感受過,我透過健身這份體驗獲取的滿足與快樂;他們看到的是健身帶來的功能價值,眾所周知的理論——健身帶來的好處。他們看不到我因為健身戰勝自己的快樂、由內而外散發的自信。
是的,我一直被家人看不見。就好比一些大學生害怕節假日回家,外地打工者害怕春節回家,因為他們回家就要面臨親朋好友的種種問候,問考研留學,問薪水提拔,問結婚生子。家本是放鬆地,然而這份放鬆卻被家人剝奪了。
時刻拿你是問,此時此刻他們看到的你,是用社會約定俗成的功能價值套住你,看別人家的孩子都留學了你怎麼還在家打遊戲呢,看鄰居某某都生二胎了你怎麼還不結婚呢。你不斷被疏忽,疏忽到只剩下你的功能價值了。
我曾有長達幾年給自己的定義是廢人,聽說障礙對我的約束太大,連公共場合急需搬運東西我都搬不了,因為搬運需要聽從指揮,且變化性很大。外加我從小被包辦長大,尤其成年後,明明是主角的我,卻只能做配角的事情。
我看到人與人之間都是功能價值的交換,我身上唯一的社會標籤是聽力障礙者,無非就是告訴人間:耳朵也可以聽不見,口語也可以不清晰。除此以外我還能有什麼價值呢?就在我奶奶去世後沒多久,我漸漸找到了一個答案。
原來,除去功能價值,還有一個存在價值。即在剝去你身上所有的功能價值後,還剩一個存在價值——你究竟是誰?或者說,當你邁入老年階段,在你無法做任何事情的情況下,只要你活著,這個時候的你,究竟有什麼價值?
不禁想到我奶奶,至今去世已有一週年。我奶奶是文盲,來自偏僻的農村,入住我家這十幾年來,她不太會用城市的智慧裝置,如出門需要乘坐的電梯,如煮飯需要用的電飯煲,如買東西需要用的不同現金,她不得不需要依靠她家人。
奶奶這麼多年來一直做一件事,唯一一件能為家人做的事情——每晚為家人燒水灌水壺。我們晚上有飯後外出的習慣,奶奶一個晚上都呆在廚房裡與水壺相伴,她都會燒兩三壺水,灌滿兩個暖瓶,為的是我們回家直接用暖瓶洗漱。
因為奶奶,不再用功能價值看待她,而是用存在價值接納她。直到我奶奶去世,奶奶的葬禮中,她五個子女們的悲慟,給我上了一堂深刻的課,原來,“活著”本身就足夠支撐全家人的心,這個時候,我放棄了我對我自己的否定定義,因為,平安無事地存在已經難能可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