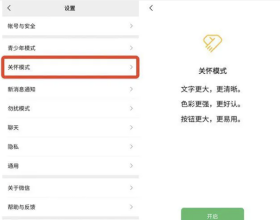在我們家,有三個人屬鼠,姥姥舅舅和我。我們順連式相差二十四歲,呈不等邊三角形,牢牢地插在姥姥溫馨的兩間土屋裡。舅舅最恨鼠,常常用他的聰明才智搞一些惡作劇,想置鼠於死地。
這一天,他帶著我去村西的水塘放鼠。
舅舅的放鼠其實就是教訓鼠,懲罰它們不知深淺地總是偷吃他的糧食。而這主要是因為它們不僅僅是自己吃飽,走時還要帶上一些,彷彿有意與舅舅作對,不知把糧食搬運到了哪裡。等忙碌了幾天的舅舅再到穀倉裡一看,一麻袋穀子竟讓它們弄走了小半袋。
氣憤之餘,舅舅燒了一鍋開水,逐一往鼠洞裡灌,想把它們活活燙死。但舅舅終究是敗興而歸,沒有實現預期目的,不但沒有“水漫金山”,還惹得老鼠們奮起反擊,刨了更多的洞口。
舅舅極其氣惱,下大力氣做一些鼠夾和捕鼠的籠子。把它們捕捉到後,並不弄死,而是帶到村西的水塘,一股腦兒倒進水裡,然後用柳條趕它們,不讓它們上岸,想處以極刑,享受勝利的愜意。
十幾只鼠好像是一個家族,大小不一,大的有半尺長,小的也就兩三寸,但都有令人稱奇的本領。它們出乎意料地會游泳,用後腳划水,用前腳操控方向,用尾巴充當舵,並且有著驚人的耐力和毅力,如一隻只鴨子,根本就不會被淹死。
舅舅與它們周旋了一上午,又煩又急,大呼上當,只好把手中的柳條一扔,放生。
但是鼠災在我們家沒有減少,它們有時還會出演“五鼠鬧東京”,大半夜在棚頂躥上跳下嘶喊連天。舅舅突發奇想,抱回幾隻貓,大貓生小貓,不到三個月,貓的隊伍就變成了一群。可它們非但沒把老鼠嚇退,還把自己吃得好胖。因為舅舅為鼓勵它們好好幹活,有時會犒勞它們一些小魚。有了魚,貓就和老鼠為鄰了,它們和睦相處,彼此相安無事。
最讓舅舅受不了的是,老鼠好像總跟他過不去,舅舅弄走了它們家族的成員,它們很孤單,竟在一天夜裡,趁舅舅睡著,偷偷把他的書嗑碎了。舅舅愛看書,每晚都藉著煤油燈看,累了把書放在枕邊就睡著了。可是早上醒來一看,枕邊全是雪花,白花花的,大米粒一樣,一堆又一堆。老鼠把他的書啃得只剩一副狼狽的骨架,悽慘地蜷縮在他眼前。舅舅氣得高聲大罵,挨千刀的,有朝一日我非滅了你們的種族!
可舅舅沒有這個能力,只能急得團團轉,直摔東西。倒是一直不吭聲的姥姥給他出了個主意:你每天給它們喂點東西,它們就不報復你了。舅舅聞聽怒目圓睜,反問:咋地,當爹供著啊?攜帶病菌,傳播疾病,您不知道啊?姥姥沒有理睬舅舅,而是揹著他,自己去做。
姥姥弄來大半碗小米,上面滴上一星豆油,黃昏來臨時,一小撮、一小撮地放在牆根兒的幾個鼠洞旁,然後對一旁的我說,有了吃的,它們就不會出來惹事了。也果真像姥姥說的那樣,打那以後,舅舅的枕邊無論擺放多少書,老鼠都沒再問津,舅舅也就避免了遭受群鼠的攻擊和洗劫。
我也不再視老鼠為敵,常常問姥姥一些關於鼠的事。姥姥告訴我,老鼠也是善良的,它們吃糧不吃人,眼睛先天性近視,一般看不到前方的路,它們靠嘴旁的幾根鬍鬚探路,大多時候喜歡沿著牆根兒跑,不和人類搶路。姥姥還說,老鼠是孩子脾氣,它們亂玩東西、偷吃東西是在和人生氣,因為人從不給它們餵食。如果有人稍稍給它們一點吃的,它們吃了就會心滿意足地離開,不再搗蛋。
這一年春脖子長,大地甩臉子一樣堅決不返青,各家各戶都開始缺糧食了,我的童年基本是在姥姥家度過的,多少也讓他們家的糧食吃緊。舅舅有些愁眉苦臉,姥姥卻依舊樂觀。有一天,趁舅舅不在家,姥姥領著我拿著小鐵鍬,到房子後面的菜園裡這杵杵、那敲敲。姥姥說,她在找鼠洞,洞裡一定有好多好多的糧食。可是我們費了好大的勁兒也沒找到。忽然,一隻老鼠出現了,在我們面前停了停,黑幽幽的眼睛把我們看個夠,然後不慌不忙、一步一回頭地鑽進玉米秸垛。姥姥按著它的指引開始挖掘,挖了大約一尺半深,奇蹟發生了,一堆黃黃的麥粒出現在我們眼前,足有十五六斤的樣子。
我和姥姥開心極了,終於有糧食了,可以吃上香噴噴的麥飯了。
長大以後,這些都已成為往事,但中國神秘文化總結出的鼠的通靈,卻如種子一直在我心中發芽。回頭細想,鼠確實是很靈性的動物,身上有比其他動物發達的第六遙感器,直覺能力特別強,很多事都未卜先知,沒有一個好記性,卻是個樂天派,被誰傷害過,當時反應敏感,過後就不當一回事了,其實這何嘗不是一種優長和生存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