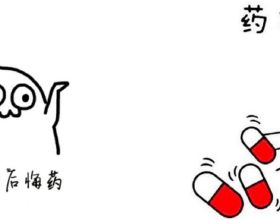文/孫新生
我生來好動,自知本性不是垂釣之人。
看到那些釣魚人靜坐水邊,悠閒自得,雖覺得有些無趣,但不免寂寞孤冷,且有愚笨呆板之嫌。然而,近年來隨著年齡增長,性格趨靜,在好友的鼓動之下,趁著雙休日之機,也偶爾去領略過幾次垂釣之娛,這才知道釣魚之事也是機關算盡,靜中有動,十分忙碌。
人這個靈物就是聰明。當年柳宗元獨釣寒江雪,充其量魚竿是竹的,浮漂是木的,拉繩是麻的,餌也不過蚯蚓之類,絕捨不得把什麼好東西往水裡投。但現在的誘捕手段之高明,令人瞠目結舌。
魚竿用特殊塑膠製成,如什麼碳素鋼之類的,還便攜,可伸縮。掛鉤一端細長,堅韌而不易折;細如髮絲的尼龍線代替麻繩,透明又結實;魚漂紅白相間,顯眼而又靈敏度極高;魚鉤鋒利,且有數枚。最可嘆的是誘餌的變化,以白糖、香料、酒、雞蛋和麵,輔之少許麩糠,聞之香味醇厚,食之可口垂涎,魚鱉這類低等動物,怎不趨之若鶩?
垂竿之前,先將食料撒入水中,漁人謂之“做窩”。拋鉤的動作十分優美,在柔韌的竿端作用下,釣者一揚手,鉤拋物線狀地滑落水中。魚漂浮在水面。魚稍有動靜,便有顯現。
釣者此時心情看似平靜如水,實是緊張得很。靜是為了保持穩定,誘魚上鉤。這是表面現象。動則是內裡,如打太極拳盡萬鈞之力於柔弱之中。既要察看水色,觀察魚路,確定垂鉤方案,又要不斷地放鉤、挺竿、收鉤、取魚、加料,無一刻閒散,尤其不能走神,故不親身經歷不知其忙碌之甚。
對魚來說,又是另一番心情。覺察到誘餌垂於水中,吃與不吃,心理十分矛盾。先上鉤的往往是些小魚。它們活潑好動,幼稚爭吃,浮游在淺層。大魚則深潛水底,待機而動。實在忍不住了,有經驗的先用嘴翕動餌料,將餌松落,再食之。魯莽的則撞而吞之。此時,釣者要把握時機,乘勢收鉤,把魚釣上。
就數量而言,上鉤的魚僅是少數,更多的是靠自己辛勤勞動——以捕食為生。它們不為餌所誘,遊弋於廣闊的水域之中,好不自在。
善釣者熟知魚性,因時、因地、因魚類而採取制宜之策。一日之內,早晚陰,午間曬,上午九、十時和傍晚是垂釣的最佳時機。一年之內,冬釣午,春秋釣辰辛,夏釣早晚。臨江放鉤,擇迥水處;塘旁水庫垂竿,宜選沙底水淨的地方。烈日當空,樹蔭遮陽風涼地;山雨欲來,流水匯聚之要衝。
魚有百種,百魚百性。就性格而言,有柔弱與剛硬之分。性弱者,如鯽、鰱、鯇等,長於中淺水層,喜甘香之餌;性烈者,如鯉、烏等,常在陰暗處探幽,習深水,味口與前者不同,以蚯蚓、小魚等弱物為食。釣法也不一樣,對強者最好是放長線,尤其在颳風下雨時為佳。
人對魚性摸得越透,捕魚的法子也越多,有竿釣、輪釣、線釣之分別,還有筐伏、網捕以至竭澤而漁等。看似很笨實為巧妙的手段就是鉤團魚(俗稱老鱉),對付這些吃豎不吃橫的傢伙只要有根小木棍加點活食即可。如此各種釣法都說明人對魚知根知底。姜太公“無餌之釣,願者上鉤”絕非釣魚,那是別有所圖,非本文所論。
由世人釣魚想到獵獸、捕鳥,我明白了環境學者驚呼保護動物的原因。如此多的手法,如此強的力量,魚、獸、鳥怎能吃得消?那些頭腦簡單的傢伙,在地球上消失得很快,如老鱉其價格幾年間扶搖直上,由幾元賣到幾百元一斤。
垂釣所要解決的矛盾看起來是放餌食餌之輪迴,實為人魚之間引誘和反引誘、貪吃和反貪吃之鬥爭。以餌誘吃是過程,貪吃被釣受煎熬是一種結果,不為餌所動活得天然成趣也是一種結果,兩種不同的下場,完全由魚自己的態度所決定。只不過現在出現了“釣技”日高、“餌誘力”日強的新情況。要做到不為餌所誘,顯得更為困難罷了。
“人場”和“釣場”極為相似。對於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來說,抵制誘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顯得尤為突出。當然,誘人之餌較之魚餌名堂要多得多,價值要高得多,滿足享樂之程度要舒適得多,絕非“吃”字所能囊括。
有官銜之餌、虛名之餌、金錢之餌、酒綠燈紅之餌等等。釣法也很繁。有明舉,談判桌上就講清回扣之數量;有暗法,天知地知之時送你知我知之物。有垂有形之餌,小至日常用品,大至鈔票股票、名車美女、文物古董、房屋花園,不一而足;有懸無形之餌。授以虛名,揚聲顯像,封以官職,扭為圈內之人。有放長線釣大魚,時常施之恩惠,給予拉攏,以求關鍵時刻備用;有急抓急用,收立竿見影之功,可這“餌”的量要足,價要高,最好能達到賞心悅目、驚心動魄的程度。
據說現在還有以“陪”試“釣”之法。除傳統的陪吃、陪喝之外,再加上陪玩、陪樂、陪洗、陪睡“一條龍”服務。名酒佳餚之後,再卡拉OK試喉,雕花地板上曼舞、現代髮廊裡摩娑……經過這番處理,豈有不上鉤不被釣之理?嗟呼,可憐那刀下物,盤中餐,櫃中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