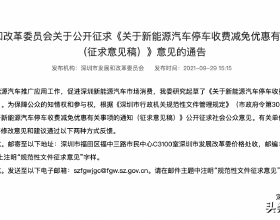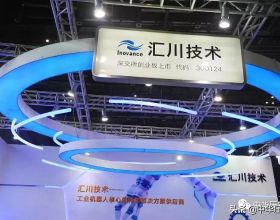首先說明,過於殘酷的圖已經被刪除和打碼,但仍然可能會造成不適。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上與日軍拼得血肉橫飛,損失比歐洲還大。因此心懷憤懣的美軍,自然對日本人的遺體不那麼客氣。
比如收屍,美軍自己的屍體有專門的收屍隊完成,遺體都有埋葬深度等標準。日本人屍體則處理得非常潦草,多半是直接拿個大推機,在沙灘最好挖的地方推出一道平溝,從兩側把屍體推進去,再推平了事。
有的圖省事,直接往林子裡一推了事,任其鳥啄蟲蝕,還美其名曰“這樣樹林就藏不了人了,並不妨礙我們修機場”。
所以,戰後日本官方負責收拾遺骨的隊伍,居然能在太平洋很多島嶼叢林裡和淺層土裡找到相當多的舊日本軍殘骸。
其實這都只是小意思,戰場對輸家就是這麼殘酷,也沒法過於抨擊美國人的敷衍。
但最令日本人受不了的,是有些美國士兵已經不滿足於搜刮隨身戰利品了,居然拿日本人的骨頭做工藝品,甚至自己玩不說,還要拿來送禮或者搞紀念品交易。
美國士兵收集日軍屍體甚至引起了盟軍軍事當局的注意,在美日雙方的媒體上都得到了廣泛報道和批評。
一般來說,主要存在“骨骼工藝品”、“牙齒工藝品”、“頭顱工藝品”和“耳朵掛飾”等問題。其中人頭骨受到的關注最高,但調查者認為牙齒才是最受歡迎的,而且也能得到普遍的接受。
根據一位美國軍人作家韋恩斯坦(Weinstein)的說法,當時搞日軍頭骨和牙齒是一種普遍的做法。
撰寫了《擁抱戰敗》的美國曆史學會委員,二戰史專家,美日關係專家,約翰·W·道爾教授則反對這一觀點,聲稱:“耳朵是最常見的戰利品,而顱骨和骨頭則不太常見。”
他特別指出,“頭骨不是受歡迎的戰利品”,因為它們很難攜帶,而且去除頭骨的過程令人反感。
不過,事實似乎與道爾教授所說的有點差別。
最出名的一次事件就發生在二戰期間的1944年,當年5月22日的《生活》雜誌上居然刊載了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一位年輕女性含情脈脈地注視著一具人類的骷腦殼。
據悉,這具骷腦殼來自於她正在太平洋上作戰的戀人,他剝取了某個日本兵的頭骨,將其作為“勝利的獎盃”送給女友。
單人駕機跨越大西洋而聞名的飛行明星查爾斯·奧古斯都·林德伯格(林白)揭露了這種行為——美軍處理日本人骨頭的常見做法是:將頭切下來,放到鍋裡煮,以去除肉和脂肪,這樣便能製作頭蓋骨獎盃。
記載者不止林白,1944年美國詩人溫菲爾德·湯利·斯科特當記者時,一名水手在報社展示了他獲得的“頭骨獎盃”。於是詩人詩興大發,當即撰寫了一首名叫《帶著日本頭骨的美國水手》的詩,詩篇中描述了製作頭骨獎盃的方法。
這種方法屬於水手,他們連下鍋煮都懶得幹,直接將頭骨剝皮,然後用網拖到船後“清潔”,剩下空殼後再用燒鹼擦洗拋光。
當年的美國報紙刊登了不少這樣少兒不宜的內容,比如坦克上掛著日本兵齜牙咧嘴的乾癟頭顱,用日本兵的牙齒做成的項鍊,拿日本兵掛在鐵絲網或木樁上嚇人等等。似乎美國人並沒有將日本人當做人類,他們總能以千奇百怪的黑色幽默來侮辱屍體,也沒有因此而感到反胃。
林白在珍珠港事件以後以航空顧問的方式進入了美國陸航,還以平民的身份參與了50次戰鬥。因為與納粹相親,與美國政府若即若離,他毫不客氣地在日記中記下了太平洋地區美軍開發手工藝品的種種經歷。
林白提到:在新幾內亞時,軍隊將殺死日軍掉隊者視為“某種業餘愛好”(原文是:as a sort of hobby),並經常將他們的腿骨拿來雕東西玩。
林白在與某個陸戰隊軍官聊天時,對方告訴他:經常看到沒鼻子缺耳朵的日本士兵屍體,那是被人洩憤割掉的。
也有些說法認為,這些削掉耳朵鼻子的屍體是澳大利亞人的傑作,這是對日本鬼子的報復,因為日本人曾殘酷虐殺了不少澳新軍團官兵。
1944年林白從夏威夷透過美國海關,海關的申報內容中居然要求作出“是否攜帶任何骨骼”的報告。當他表示震驚時,海關官員告訴他:“這是個常規問題”,因為海關經常發現美國兵帶回來的大量“紀念骨頭”,甚至還包括“綠色頭骨”(指未加工過的)。
後來日本官方在1984年收集馬里亞納群島的日軍遺骨時,居然發現60%的人沒有頭骨。
同樣的事情發生在硫磺島上,許多日本人遺骸的頭骨都不見了,這絕非尋常。
也有人專門調查過美國戰後的“頭骨獎盃”,試圖幫太平洋地區的美軍洗白,結果經過法醫的樣本考察,沒有一個樣本來自歐洲,全是亞洲人的。
對美軍而言,他們並不僅僅是報復,許多人有著奇怪的戰場心理,他們懸掛著日本人的牙齒項鍊,認為這能充當護身符和“賦予力量與幸運”;頭蓋骨則多是寄回家的“勝利獎盃”,在他們眼裡這很洩恨,很酷,因此蔚然成風。
用當時的“行話”來說,這叫“trophy-taking”,即“奪冠”。
但林白亦表示,那些骨頭並非從剛殺死的日本人身上採集的,大部分來自戰場上撿到的部分或完全白骨化的日軍屍體。
就連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都收到了這種日本兵骨頭工藝品,有名國會議員一天送給他一個拆信刀(letter-opener),是用日本兵手臂骨製作的。
不過羅斯福不想要,報紙輿論也越來越過分,於是他下令把這噁心的禮物還回去,還要求對方“將其妥善埋葬了吧”。
隨即美軍開始明令禁止拿人骨做工藝品的行為,只是沒有任何作用,遠在北美洲的政府命令完全管不到遠在天邊的美軍,他們依舊我行我素,還明目張膽的用軍用通道將人骨製品送回家或賣給收藏家。(正如美國政府1933年說手持5盎司黃金即違法,但壓根沒人遵守一樣。)
美軍早在1942年就釋出了附加戰場指南,明確譴責人骨製品行為,尼米茲海軍上將更是以太平洋艦隊總司令的身份釋出命令,要求“不得將敵人身體的任何部分用作紀念品”,任何違反這一原則的美國軍人都將面臨“嚴厲的紀律處分”,就差把它印在巧克力盒子上了。
1943年10月,麥克阿瑟曾經與馬歇爾將軍通電話,馬歇爾表示:“對美國士兵暴行的最新報道感到擔憂”,指的就是拿人骨做工藝品的行為。
可麥克阿瑟也很無奈:“至少他們很有勇氣,我甚至巴不得新兵們拿敵人的頭當球踢……”
到1944年1月時,由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釋出專令,命令“禁止一切拿走日本人身體器官的行為”,但指揮官們依舊愛搭不理的一片無所謂態度,命令無法在所有地方生效。
《太平洋》電視劇的原始素材創作者,撰寫了《與老兵同在:貝里琉島和沖繩》的傳記作家尤金·斯萊奇教授(Eugene Sledge),當年曾在陸戰1師擔任下士,參與了太平洋上最慘烈的戰役。他描寫了一些親身經歷的殘忍事件。
“幾個同僚從日本人身上拔金牙,有個日本人還活著,他背部受了重傷,手臂無法移動……日本人的嘴裡有顆大金牙,俘虜他的人想要它。”
“他把卡巴軍刀的尖塞入一顆牙齒的底部,然後用手掌敲打把手。日本人疼得拳打腳踢,於是刀尖從牙齒上掠過,深深扎進了他的嘴裡。”
“馬潤咒罵他,然後用刀斬開了他的面頰,一直裂到耳朵。”
“他用腳踩在傷兵的下頜上,又再試了一次。鮮血從日本兵嘴裡湧出,他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拼命捶打著。我喊道:‘結束那個人的痛苦吧!’但我得到的答案只是一句髒話……另一名馬潤跑過來,將一顆子彈射進敵兵的頭顱,結束了他的痛苦。而‘拾荒者’連頭都沒抬,咕噥著,不受感染地繼續‘提獎’。”
顯然,這種行為的動機可以說是貪婪而不是仇恨。
澳大利亞士兵也被控訴過同類事件,他們在歐洲挖德國俘虜的金牙,結果迎來了包括宗主國英國在內的一致厭惡,認為這是“野蠻而不可接受的”。
另一個叫唐納德·法爾(Donald Fall)的陸戰隊老兵也講述了差不多的故事,他將行為詮釋為仇恨和復仇的渴望。
“瓜島的第二天,我們攻佔了一個日本的大型露天營地……我們發現了很多陸戰隊士兵在威克島被砍頭和肢解的照片。”
“你能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陸戰隊士兵們四處走動,他們用安全掛鉤把日本人的耳朵掛在腰帶上……”
“命令提醒海軍陸戰隊,肢解屍體是上軍事法庭的罪行,但戰鬥中你會陷入一種糟糕的心態。你會發現一個被日本人用陷阱殺死的馬潤,他們肢解了屍體。於是我們幹掉日本鬼子時,也降低到了他們的水平(原話:We began to get down to their level),肢解了他們。”
海軍陸戰隊隊員奧雷·馬裡恩(Ore Marion)在回憶中表示:
“我們從日本人那裡學到了野蠻。”
“我的那些16到19歲的小夥子們學得很快,黎明時分,我手下的兩個孩子,他們鬍子拉碴,衣服破爛,髒兮兮地,餓得骨瘦如柴,還被刺刀創傷,他倆把三個日本鬼子的頭給擰了下來,還插到了面向日軍一邊的杆子上。”
“上校看到鬼子的腦袋戳在杆子上說:上帝啊,你們在幹嘛!你們就像群畜生!”
一個又髒又臭的孩子笑嘻嘻地說:“沒錯,上校,我們就是畜生。”
“我們像動物一樣生活,我們像動物一樣吃飯,也像動物一樣被對待——你他喵的在指望什麼?”
不過,美軍也並非只在太平洋戰場作孽,儘管曾經有法醫報告認為頭骨都來自亞洲,但二戰時歐洲也存在美軍拿屍體開玩笑的情況。
德國人曾控訴多起美國士兵辱屍的問題,例如有個德國士兵被美軍剝了頭皮,而美軍則辯稱這是“美國溫尼貝戈族印第安人的部落文化習俗”。此外還有人將德國兵的骷髏掛在坦克上,但沒有得到證實(還有的說法是捷克人看到的)。
同樣的事情發生在越南戰爭,美國兵用同樣的方式將戰場頭骨寄回家,其中有些後來遭到舉報,然後被警察搜走了。
實際上,美國社會並不能接受這種拿人身上零件整活的行為,但正如無關痛癢的法律和軍令管不到大兵們一樣,美國社會也沒轍,因此他們選擇了拋棄和淡忘這種歷史。
許多美國曆史學者認為,士兵們的“顱骨獎盃”行為源於當時的社會空氣,其中蘊含著大量的種族主義和廣泛的政治觀點。
從美國政府開始,人們廣泛地傳播著“日本人不是人”、“日本人是低劣民族”,是“黃色害蟲”(yellow vermin),是“活的,尖叫的耗子”(living, snarling rats)。因此對許多美國人來說,日本這個對手不過是一隻動物。
因為日本人被視為動物,所以日本人的遺骸與動物遺骸受到同樣的對待也就不足為奇了,虐待它們的殘骸並不會帶來任何道德上的汙名。
甚至有人寫了一篇名為《太平洋戰爭的骷髏戰利品》(Skull trophies of the Pacific War)的論文,稱“少數美國人之所以收集骷髏,是因為他們來自一個非常重視狩獵的社會。狩獵是男性氣概的象徵,而敵人也是非人性的……”
有些問題並不能全讓戰場上的大兵背鍋,比如有個段子稱,某個姑娘朝軍人們要骨頭紀念品,於是有個軍官真的從戰場上帶來了一個簽了十幾個大兵人名的骨頭。
就連被視為“音樂人類學家”的艾倫·洛馬克斯都不能免俗,1942年艾倫·洛馬克斯釋出一首藍調音樂,有個黑人士兵聽眾高興地承諾,會給他的孩子送來一個日本頭骨和一顆牙。
實際上這些亢奮、膽怯、仇恨和獻殷勤背後,還有經濟利益。
沒錯,就是拿骨頭賣錢。盟軍1944年初的一份報告稱:“駐紮在瓜島的海軍建造營成員在向商船船員出售日本人頭骨”,而且“貿易經常發生”。
最後,還是美國一些老軍人說得最真實——拿人身體部位做獎盃和紀念品的行為,是一場殘酷戰爭的殘酷副作用。
戰爭從來都是人類最野蠻,最瘋狂的暴力行為,它摧殘著一切世間的美好,把人變成了野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