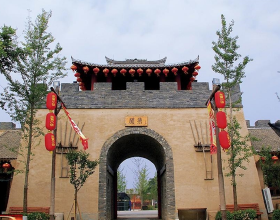(本文系本人原創,首發《深圳特區報》)
所評圖書:
書名:《世界戰爭:二十世紀的衝突與西方的衰落》(上、下)
作者:(英)尼爾·弗格森
譯者:喻春蘭
出版社:廣東人民出版社
20世紀,準確來說,是二戰結束前的幾十年,是人類歷史上最為灰暗的階段。這一時期比以往任何文明史時期,有著更多更殘忍的殺戮。兩次世界大戰是史無前例的大屠殺,以密集的頻率展現了現代文明國家相互攻擊和自我毀滅的瘋狂。
二戰之後,美蘇對峙多次拉響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警報,就是因為先前的世界大戰的教訓足夠慘烈,才遏制了不負責任的戰事第三次全面蔓延。儘管如此,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巴爾幹危機,以及發生在前蘇聯、柬埔寨和非洲、拉美一些國家的政治高壓和種族屠殺,也製造了相當驚人的傷亡和屠戮。
我們應該從這樣一個動亂世紀中,汲取怎樣的教訓?上演動亂世紀的原因,我們究竟有沒有有所公正的認識?
一戰為什麼按理說不該發生?
一戰並不符合人類在剛跨入20世紀時候,對世界的期待。英國等歐洲國家對世界其他大洲的統治及變相控制,在當時看上去是相當穩固的,並且經過幾個世紀的掠奪,殖民統治本身開始變得文明。以英國為例,這個國家甚至嘗試用幫助建立法治體系、代為培養殖民地本土精英並由後者代行管理職責的方式,來維持日不落帝國體系的繼續運轉。
如果戰爭(一戰)沒有發生,想必分析人士可以得出以下原因:
首先,在歐洲大陸,除了德國之外,沙俄等其他君主國家都陷入了顯著的衰落,這不是指經濟上的完全衰落,而是指統治階層的控制力變得薄弱。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意味著這些國家戰爭動員能力的下降。事實上,一戰打響時,所有主要參戰國都並沒有做好周全的戰爭準備,對戰爭的殘酷性和長達四年的週期也毫無思想準備。
其次,英國和歐洲大陸上的若干個君主國家,都有著非常密切的姻親關係,德國皇帝、俄國沙皇、英國女王、奧匈帝國皇帝及其他王國的君主都是近親,德國皇帝還曾致信俄國沙皇,希望歐洲王室團結起來以重視黃種人的崛起,避免白種人再度迎來古代和中世紀時遭遇過的幾次“黃禍”。
第三,19世紀是個戰事極少的世紀,歐洲國家之間形成了運作良好的爭端調解機制,人們有理由相信,這一機制還將繼續發揮其作用。
第四,當時的全球化貿易體系,促成了後來成為主要交戰國的若干個國家之間密切的經濟聯絡,以羅斯柴爾德家族為代表的金融寡頭也不希望歐洲上演大的戰事。
第五,工人運動在歐洲的蓬勃開展,形成了看似強大並能在所在國家遏制戰爭發動的反戰力量。
一戰又為什麼還是發生了?
以上這麼多阻遏因素,也沒有避免一戰以一種近乎荒誕的方式打響,並從區域戰爭迅速蔓延為了世界大戰。這背後的決定性因素是什麼?除此之外有哪些偶然原因?我們應該從世界大戰中吸取哪些教訓?而今還存在誘發新一次世界大戰的可能嗎?對這些問題,世界著名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歷史學和商學院金融學雙科教授尼爾·弗格森在其所著的《世界戰爭:二十世紀的衝突與西方的衰落》一書中,還原了19世紀末至一戰發生期間歐洲、美國、日本等戰爭策源地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潮、文化等場景,給出瞭解答。
尼爾·弗格森認為,一戰發生與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被刺的象徵性意義有關。19世紀沒有發生大戰,卻催生了民族國家意識(經多次國際會議推動確立),多民族帝國漸趨瓦解為單民族的民族國家,問題是歐洲大陸的許多區域內各民族居住分散,不可能高度精確的劃分出真正單民族的國家,這就產生了新興民族國家中主體民族與少數民族的矛盾,以及殘存、衰落卻不失軍事威勢的舊帝國與新興民族國家的尖銳對立。
這種矛盾和對立直接催生了頻繁的族群衝突,日後在一戰、二戰、巴爾幹危機期間上演的族群大屠殺,其實在一戰之前就有了若干次預演。斐迪南大公被刺,刺殺者(塞爾維亞青年)踩在了觸發國家衝突、文化衝突的“斷層線”之上,接下來才是奧匈帝國、沙俄、德國、法國、英國一連串莽撞擴大沖突範圍的決策。歐洲誕生於19世紀末至一戰之後被扶持建立的若干個民族國家,晚至20世紀90年代仍不可避免滑向巴爾幹危機,再演族群屠殺;而類似的矛盾和衝突機制在其他大洲的部分割槽域同樣存在,迄今並沒有很好的從根本上消弭仇恨的辦法。對此,世人仍有必要保持高度警惕。
族群差異演化為族群衝突的教訓
當然,一大批新的民族國家誕生,以及相應的民族主義萌生,尚不足以讓各國公眾都陷入歇斯底里的仇殺,更不能讓英法德俄等歐洲老牌資本主義大國也加入到亂戰行列。尼爾·弗格森在書中揭示的另一項埋下國家、民族仇恨的原因,也同樣值得今天的人們引起注意。
心理學家揭示,人們傾向於善待與自己擁有同樣身份標籤的其他成員,對跟自己有著不同特徵的人們則敬而遠之。這種傾向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被當時盛行的優生學理論、社會達爾文主義誤導成為了族群仇視。《世界戰爭:二十世紀的衝突與西方的衰落》書中介紹了我們而今很難相信曾經存在過的、歐洲和美國普遍推行過的嚴禁跨種族通婚的法令,這些法令不可思議的流行開來,被視為保持某個種族、民族血統純潔性的保障措施。在當時,歐洲國家特別是誕生了一大批新的民族國家的中東歐,種族、民族間雜居和相互通婚程度很高,“血統保衛”說、“文化基因”說讓鄉里、鄰里甚至家庭內部都開始上演衝突。
還不容忽視的是,在當時,包括老牌歐洲國家和新興民族國家在內,各國為了轉移社會矛盾,都在縱容甚至主動製造本國主要民族中下階層人士對猶太人的仇恨。國家、種族仇恨漸漸強化,在一戰最後階段之外的各時期戰場上,交戰國軍隊甚至拒絕接受對方士兵的投降;我們還能想起的是,一戰後期,美國政府為了解除本國國民普遍厭戰的心理,率先引入了新誕生的傳播學理論,在國內對假想敵德國開展了有效的妖魔化宣傳。
來自科學(學者論證)、政治作用、民間等方方面面的推力,加深了仇恨,讓衝突一旦形成就逐漸升級,並使得試圖終止衝突的努力常常受到了中斷。毫無疑問,這使得衝突、戰爭損失最大化,堪稱最不理性的選擇。近年來世界各地仍屢屢出現與誘發一戰相類似的矛盾、衝突升級鏈條,也表明百年前的那場世界大戰的教訓還沒有真正發揮出應該發揮的作用。
矛盾只能消弭而不應掩蓋
一戰的閉幕,並不是戰勝國在戰場上取得了對戰敗國的絕對優勢,而是戰敗國先一步迎來了“打不下去”的困境。但可惜的是,除了當時的美國總統威爾遜,其他戰勝國均沒有意識到即便再強大的資本主義工業力量,在世界戰爭面前也顯得脆弱的定律。戰勝國基於不切實際的自信,開展了對戰後世界格局的重新確定,德國等戰敗國受到了徹底羞辱和部分肢解,大國寡頭們一方面放縱了日本的遠東擴張野心,另一方面輕視了引燃歐洲國家和民族之間衝突的根本原因,繼續推動多民族帝國分解為多個單民族國家的程序——這三大動作,經二十年的發酵,讓更為慘烈的二戰降臨到世界。尼爾·弗格森在《世界戰爭:二十世紀的衝突與西方的衰落》書中也不無惋惜的指出,一戰後建立或恢復建立的民族國家,都上演了主體民族對少數民族及猶太種族的壓制,但大量的流血衝突卻沒有引起當時的幾個大國的重視,更談不上介入干預。
一戰和二戰之間所謂的“和平二十年”,對於捲入了這兩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國家來說,並不是安寧繁榮的二十年,相反,成為了讓先前矛盾得到進一步發酵和積蓄的重要週期。經歷了漫長通脹、蕭條和動盪的德國主動擁抱了納粹,美國的羅斯福新政也飽受質疑,蘇聯採用類似英法16-19世紀殖民統治的方式在本國建立了高壓式的計劃經濟體制,經濟危機讓歐洲許多民族國家效仿德國和義大利走向了獨裁。英國則試圖推行一種花費最少成本而在全球範圍內維持對其最為有利的和平,即後來被恥辱寫入史冊的綏靖政策,包括對日本、義大利、德國的擴張野心的縱容,以及在西班牙等國家上演叛亂者顛覆民主政府的個例。
納粹德國讓相當多的猶太人迎來了噩夢。但必須指出的是,排斥乃至默許民間清理、殺害猶太人的國家,在當時並不只包括德國。而官方和民間排斥力量相對較弱的一些國家,比如美國和英國,在當時對本土猶太人、外來各種族移民的政策態度也很不友好。尼爾·弗格森認為,這正是相當多德國猶太人面臨日漸臨近的壓迫,卻無處可去的重要因素。
在尼爾·弗格森看來,德國和日本之所以在二戰中戰敗,是因為秉承一個共同的、不切實際的願望:建立一箇舊式的帝國。如前述,英國的殖民統治在19世紀末已實現了很大改變,同期開始在全球範圍內謀求戰略控制地位的美國也很少採用直接佔領、瓜分他國的方式。但是,德國和日本都希望擴充所謂的生存空間,讓被佔領區域的人們減少生育、陷入窮困和愚昧,與之同時鼓勵本國(本民族)公民大量生育;他們的美夢是,等到幾十年之後,被佔領區域的主體民族就將變為德國人或日本人,完成帝國的真正擴張。這也是德國和日本熱衷對被佔領區域民眾展開毫無軍事意義的屠殺的原因。從這個意義上講,那些為日本侵略翻案、甚至幻想日本佔領會為當時的普通中國人帶來更好生活的歷史空想家,迄今還在受到日本法西斯二戰戰時欺騙宣傳的愚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