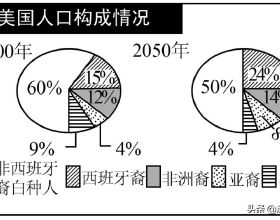1960年3月29日,一列從連雲港開出的悶罐車,沿途走走停停,拉上站臺上一隊隊穿著軍便裝、肩背揹包的退伍兵,一路向北而來。那個坐在車廂一角、不言不語打著盹的,就是本文的主人公郭朝品。
陰差陽錯去種地
郭朝品,是前來支援石油大會戰的10萬轉業官兵中的一員。
“悶罐車咣噹3天多,在喇嘛甸火車站停了下來。站臺不寬,我們一下車,把整個站臺擠得滿滿當當。”郭老說。
“我們這批退伍兵,軍政素質相當高,當時天下著大雪,落到地上有半米多深。我們這些人,沒有預先準備,還穿著很薄的部隊配發的夾襖,冷風一吹,雖然凍得受不了,但一個個站得筆直,整個站臺鴉雀無聲。
“一會,來了位油田上農副業科的領導。他說,交給我們一個光榮艱鉅的任務,因為糧食供應緊缺,為了保證石油會戰順利進行,需要我們到剛建立的機關農場,開荒種地,解決前線吃飯問題。我們是軍人,服從命令是天職。聽完講話,二話沒說,登上站外的解放車,向目的地馬家窯開拔。
“為了用水方便,宿舍搭在一個泡子邊上。幸運的是,分給我們的兩頂帳篷是棉的,看起來很厚。雖然當時已是初春了,但在這無遮無擋的荒原中,孤立的帳篷再厚也扛不住寒風的持續攻擊,小風專找縫隙鑽,整個帳篷裡妖風亂竄。睡覺要頭戴棉帽,身穿棉衣、棉褲,甚至大頭鞋,再蓋上單薄的軍被,全副武裝,才不至於被凍醒。
“說農場所剛建!一點不假,農場連工具還來不及配齊,再加上北方的節氣照南方至少要晚上一個月,為了不窩工,場裡要求我們跟著一臺大解放,在戰區範圍內撿糞積肥,積到的農家肥再埋到地裡發酵,等待播種的開始。
“地是生地,我們這50多人,大多來自農村,農活對於我們來說是輕車熟路。但這麼大片的地要翻整,要犁出壟來,沒有現代化的農業機械,就憑人工實幹,著實讓我們這些遠離農活多日,又難忍寒冷的老兵,吃了不少的苦頭。有的人因遭不了這個罪,在夜晚連行李、工作關係、戶籍關係都沒要,不辭而別,當了逃兵。
“當時,我知道他們私下裡嘀嘀咕咕,趁夜深從我身邊溜走的事。我那時候就想,跑哪去,這年頭,上哪都一個樣,咬咬牙就挺過去了。
“春種剛完,農場為了穩定大家的情緒,消除‘跑路同志’對我們心理上產生的不良影響,給我們放了探親假。就是這個探親假,讓我差點沒回來。”
探家差點沒回來
“那時出門,沒有身份證啥的,身份主要靠組織上給開個介紹信來確認。當時,不知道是正規的介紹信沒印好,還是辦事員不明白,給我開介紹信時,沒找到紙,正好邊上我的小孩在寫作業,就在他本子上扯了張帶方格的紙,就這麼手寫了個介紹信,蓋了個公章就交給了我。我當時挺猶豫,還多問了一句,對方說有公章沒問題,我也就不好再說啥了。
“回家還算順利,返程時出事了。中間在徐州站換車,把介紹信送進售票口,售票員警惕地看了我半天,可能她也是頭一回看到這麼簡陋的、隨便的介紹信,盤問了我一六十三遭,還是把介紹信給扔出來,說介紹信的時間過期了。我拿著一看,可不是,超期了。這可怎麼辦呀?那個年代沒有介紹信,別說買票,就連住個店都不行,簡直是寸步難行。
“忽然,我發現有個警察朝我的方向走來。對,有事找警察。我和警察講了我的難事。一嘮,我們都當過兵,又知道我是石油工人,他非常熱情,把我請到他工作的徐州市公安局。多方聯絡,終於聯絡到了會戰農副業處的蔡處長。蔡處長一聽是我,張口就說:‘我以為你趁機跑了呢!沒想到你是回不來了,回來就好,你是好樣的!要啥我給你提供啥。
“按照程式,蔡處長以會戰指揮部農副業處的名義,給徐州市公安局打了電報,證明我的身份,在公安局的幫助下,我才買上了返回大慶的火車票。”
破獲豬案還清白
回到油田的郭老,接受了一個新任務——養豬。
郭老說:“讓咱幹啥就幹啥,有啥說的。交給我時,圈裡大大小小的豬有50多頭。在我的精心飼養下,到了下半年,數量達到了108頭。”
“看著一群胖胖乎乎的豬,自己就有著使不完的勁,特有成就感。
“人都說:家有萬貫,帶毛的不算,這話真不假。有一天,豬和往常一樣,吃完了白菜、土豆、雜糧烀出的豬食後,不明原因倒下了一大片,只剩下8只沒搶上槽的豬還活著。這是咋的了?是得了豬瘟還是有人下毒啦?看著我的勞動成果就這麼毀於一旦,我的眼淚一雙一對地往下掉。
“這在那個講階級鬥爭的年頭可不是件小事。當時會戰指揮部派了一個排的消防員,把案發的豬舍封鎖了起來,一來保護現場不被破壞,二來在沒弄清原因之前,也怕附近的老百姓偷走吃掉,再出問題。公安人員現場還提取了當天豬食的樣品,並帶了一隻小豬送往黑龍江省公安廳檢驗。農副業科的主管領導和我被請到二號院的門衛室,保衛科的同志很客氣,說在事情沒有查清之前,暫時留在這委屈兩天。
“咱沒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好吃好喝,沒有人看著我們,我們也老實地沒動地方。等就等吧,反正我也想知道豬是因為什麼死的。
“沒過兩天結果出來了,既不是豬瘟,也不是人為投毒,是因為冬儲大白菜堆在一起,不通風,產生了亞硝酸鹽,豬吃了中毒死了。
“豬案大白於天下,我自然又回到了飼養員的崗位重操舊業。”
土豆施救飢餓人
在那個糧食極其緊張的年代,機關幹部下基層義務勞動最愛來農場,因為在這即使幹上一天的累活,最起碼能吃上三頓的飽飯。所以,機關幹部中流傳著這樣一句順中溜:“三個人的活兩個人幹,抽出一個去會戰。”這個會戰,指的就是去農場義務勞動。
“那時候,農場再窮,吃還是不成問題的。”郭老說。
“那時的人都相當自律。知道到農場來勞動能吃飽,輪到這個機會,許多人特別是一些孩子媽媽,都不捨得吃,把分給自己的那份用手絹偷偷包回家,給孩子或老人吃。
“有一次,職工醫院的一個大夫,吃完飯,在我工作的豬圈邊上轉來轉去。和她一聊,她紅著臉說,不怕你笑話,家裡什麼也沒有了,孩子多,又有老人,農場分給她的飯不夠他們吃。她看到豬圈邊堆著些凍土豆,想要一兩個回去。聽到這我眼淚都下來了,趕緊進屋,給她拿了幾個沒凍的土豆。她千恩萬謝,都要給我跪下了。
“這以後,我常從農場淘汰或是凍壞不用充當飼料的土豆中,挑些凍得輕的能吃的,存在布袋裡,等著大家來取。可是,許多人好面子,怕別人看見偷拿豬食吃,給我找麻煩,都不主動來拿。
“我也瞭解他們的想法,每次知道有機關的同志來農場幹活,我就把像樣的土豆用繩串起來,掛在房簷下明顯的位置,有和我熟悉的,知道我的用意,晚上臨走時,不和我見面,趁著夜色,把土豆拿走。
“後來,這事兒很多人都知道了,但都秘而不宣,每到晚上,認識不認識的人,都會悄悄地到我的房簷下取走土豆。就這麼著,掛掛取取的,直到糧食不緊張、大家都能吃飽時,才結束。”
郭老說:“那些凍土豆,對農場來說,就是淘汰成餵豬的飼料的東西,沒人稀罕。但對於飢餓中的人來說,那是救命的傢伙,我不求什麼感謝,也不想讓誰記住我,只是想,在人有難處的時候,自己能力所能及幫上一把,這才叫雪中送炭吧!”
紅色傳承:善良老父親讓我感到光榮和自豪
我和父親工作在一個礦,雖然不在一個單位,但礦裡的千八人裡,許多人和父親都熟悉,他們都有一個評價:老郭是個真正的心地善良的好人。他在那個年代不知道撿了多少這樣充滿善意和真情的土豆,又因為這些土豆救了多少飢餓中的人和家庭。我每想到這件事,想到他不求回報,默默地為相識或不相識的人送走飢餓時,我都對眼前的老父親心生敬意。作為他的後代,我感到特別的光榮和自豪。
他們那代人是無我的,一切為了利他,只要能為困難中的人出一份力,都願意全心全意去做,這份樸素的、發自內心的善良,他自己並未在意,但受他恩惠的人都會記憶終生,這正是我們要學習的地方。
記者 伏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