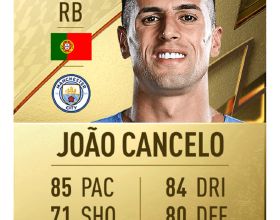“人歌小歲酒,花舞大唐春。”(唐·盧照鄰《元日述懷》)春節是國人最重視的節日之一,不過,在唐朝,老百姓並沒有“春節”的概念,新年的第一天叫作“元旦”、“元日”、“元正”或“歲日”。
年 俗
“草秀故春色,梅豔昔年妝。”(唐·李世民《元日》)有一年正月初一,唐太宗李世民不禁對著身旁的大臣們抒懷,感慨新的一年到來了,大唐王朝在自己的治理下欣欣向榮。底下的大臣們一聽,自然得附和皇帝的自誇,甚至還需要賦詩一首歌頌皇恩。現代人在大年初一喜歡說喜慶的話,古人也一樣,連皇帝也不例外。
在唐朝,大年初一,在京城的大臣們必須進皇宮給皇帝拜年,這是唐朝元旦時的一個重要的活動,叫作“元日朝會”。除了文武百官外,各地長官及一些附屬國也會派人來送禮朝賀。唐詩中有很多記述元日朝會盛大場面的詩歌,詩人楊巨源就記載過:“天顏入曙千官拜,元日迎春萬物知。”(唐·楊巨源《元日觀朝》)
唐朝人過年還得“爆竹”。唐朝詩人來鵠曾經寫過一首《早春》:“新曆才將半紙開,小庭猶聚爆竿灰。”這裡的“爆竿”就是爆竹,說的是庭院裡還殘留有新年爆竹留下的殘灰。唐朝人的爆竹和後世的鞭炮不一樣,而是真的用火燒竹子,使之逐節燃燒並爆裂發聲,以驅逐瘟神,“爆竹”、“爆竿”因此得名。
開元名相張說有一年被貶為嶽州刺史,在嶽州過年守歲時昏昏欲睡,結果被爆竹聲驚醒,於是他便將這歲末年初的守歲情景記錄了下來:“桃枝堪辟惡,爆竹好驚眠。”張說在詩中還提到了桃枝。桃被認為有辟邪的作用,因此過年不僅要插桃枝,還得掛桃符。桃符,即用桃木削成的一對木片,寫上神荼、鬱壘兩個門神的名字,懸掛在門首,據說有辟邪作用,每年大年初一都必須摘下舊的換上新的。
此外,唐朝人也有屬於自己的“春晚”。除夕夜裡,家家戶戶院子裡都會燃起火堆,唐朝人稱之為“庭燎”,將節日氛圍烘托得愈發濃烈。晚上還會上演“驅儺”儀式,即驅除疫鬼的儀式,人們會帶上青面獠牙的面具進行舞樂表演,以此來驅走鬼怪,並祈求在新的一年裡能夠平安祥和。
皇宮內舉辦的驅疫儀式就更為壯觀,被稱為“大儺”、“國儺”。詩人沈佺期有一年在皇宮裡陪皇帝守歲,看到興起的時候,皇帝就讓他記錄一下熱鬧的場面,於是沈佺期便歌詠道:“殿上燈人爭烈火,宮中侲子亂驅妖。”
年 味
唐朝人的團圓飯上要吃些什麼呢?和現在一樣,不同地區的人們有不同風味的新年特色美食,甚至於不同的酒樓還能根據各自的風格推出不同的特色菜式。唐朝韋巨源的《食譜》以及五代至北宋初年陶谷的《清異錄》裡都有提到過,唐朝時長安城裡有一家叫“張手美家”的老字號餐飲店,每個節令都有特供的節令美食,其中元日所供的便是“元陽臠”。“臠”就是肉的意思,看來,唐朝人的年桌上是少不了肉的。
在眾多的美食當中,還有幾樣是不可或缺的,其一便是“五辛盤”。這是一道用五種辛辣味蔬菜拼成的蔬菜拼盤,主要食材有大蒜、小蒜、韭菜、蕓薹、胡荽等,唐朝人認為吃這些東西可以驅疾防病,發散人體內臟中的陳腐之氣。
吃過了辛辣的,接下來就該吃甜的了。“膠牙餳”是一種用麥芽製成的糖,吃起來黏齒,所以得了“膠牙餳”的名號。古人認為過年的時候吃它可以使牙齒變得更堅固,白居易曾寫道:“歲盞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餳。”
唐朝人的年桌上,還有兩種酒非喝不可。一種是“屠蘇酒”,另一種是“椒柏酒”。“屠蘇”是由大黃、白朮、桔梗等藥材混合製成的,椒酒是用椒浸製的酒,柏酒用柏葉浸製。據說喝了這兩種酒能驅寒祛溼、驅邪解毒。杜甫四十歲那年元旦在堂兄弟杜為家中相聚守歲,就喝了椒酒:“守歲阿戎家,椒盤已頌花。”
此外,有很多唐朝詩人都在詩裡記錄了除夕夜裡喝酒守歲的情景,比如“舊曲梅花唱,新正柏酒傳”(唐·孟浩然《歲除夜會樂城張少府宅》)、“晰晰燎火光,氳氳臘酒香”(唐·白居易《三年除夜》)等等。
新年開始後,唐朝人還得開始走親戚了,親朋好友之間互相邀宴,時人稱之為“傳座”。初唐有個叫唐臨的大臣在紀實故事《冥報記》中提到過:“長安市裡風俗,每歲元旦以後,遞作飲食相邀,號為傳座。”親朋之間過年相聚,走到哪家就吃到哪家,那餐桌上不僅有酒、有美食,更有那一抹濃濃的年味。
年 趣
據史料記載,唐朝過年期間發生過許多趣事。白居易曾說:“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講的是唐太宗有一年放了近四百名囚犯回家過年,年一過,這些死囚果然都主動回來了,太宗高興之下便赦免了他們的死罪,這個故事後來還被收錄在了《資治通鑑》中。
類似的故事有很多。《新唐書》記載,中唐時有個叫呂元膺的官員,年底時視察監獄,囚犯見了訴苦說:“我有父母在,過年卻不能相見,太可憐了。”呂元膺一時起了憐憫之心,就讓牢裡的犯人都回家過年去了,過完年,犯人們全部按時回到了監獄。這些故事,歸根到底,還是圍繞著一個詞展開的,那就是“團圓”。
不過,也並不是所有人過年都想著休息,比如唐德宗就是個“工作狂”。唐德宗在位時國家問題多,德宗自己工作起來沒日沒夜,也不想給員工放假,底下人意見不小。德宗就採取了“單雙號”式放假:臘月二十八放假,臘月二十九上朝,以此類推。有一年過年,唐德宗去閱兵,寫了一首《元日退朝觀軍仗歸營》紀念。後來他又下了個規定:元旦這天不得上奏吉祥的事,不搞這一套形式主義。
不過,這完全是唐德宗的個人想法,大部分皇帝大過年的還是喜歡聽吉祥話。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年)的元日朝會上,著名書法家、太子少師柳公權第一個向皇帝稱賀。當時柳公權已經八十多歲了,年紀大記性不好,又走了很遠的路,結果還在喘大氣的他嘴一瓢,把宣宗的尊號唸錯了。御史聽到後當即彈劾,柳公權為此被罰了三個月的工資。
在“詩歌的黃金時代”的唐朝,詩人們是如何過年的呢?開元十五年(727年),詩人孟浩然在首都長安參加科舉考試,元旦時他來到田間,發現農夫和牧童們還在勞作。孟浩然聽農家推測當年是豐收年,便寫了一首《田家元日》,感慨自己已經四十歲了,雖然沒有官職但仍擔心農事,惆悵傷感之餘,聽說即將迎來一個豐收年,內心似乎又看到了希望。
詩人劉禹錫曾被貶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馬,大過年的也沒有朋友串門,心情低落的他寫下“異鄉無舊識,車馬到門稀”的詩句。後來劉禹錫遇赦,60歲那年的元日,他和白居易聚會時開心地寫道:“漸入有年數,喜逢新歲來。”可和他同歲的白居易就比較感慨了,前一夜的除夕還嘆道:“火銷燈盡天明後,便是平頭六十人。”不過,白居易晚年有一回過小年心情分外高興,原因是小外孫女滿月了。此時的他活脫脫一個和藹老爺爺形象,高興地說道:“懷中有可抱,何必是男兒。”為什麼一定要在乎是不是男孩呢?在封建社會,白居易的思想觀念的確是相當先進的了。
詩人賈島過年則有個特別的習慣。據《唐才子傳》記載,賈島每到除夕之夜必定會把這一年所作的詩歌都拿出來放在几案上,然後還要燒香拜一拜,並灑酒在地禱告說:“這是我一年來的苦心啊。”然後舉杯痛飲、放聲唱歌。
唐朝的年,雖然在許多禮儀的表現形式上有些不一樣,但是年的核心沒有變,那就是一直象徵著團團圓圓,也寄託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與憧憬。(邱俊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