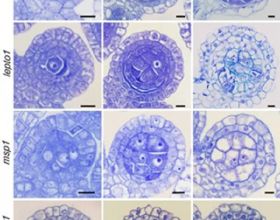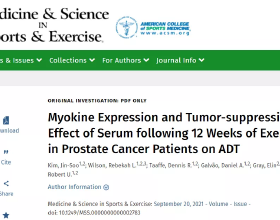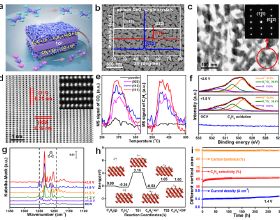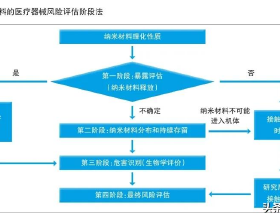澎湃新聞記者 陳若茜
《瓷器中國》是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委員、原上海博物館副館長陳克倫最新著作,通篇用權威而通俗的語言講述了中國瓷器三千年的發展歷程,是一部寫給大家的中國瓷器簡史。該書雖不追求體例上的面面俱到,但是囊括了陶瓷界長期以來富有爭議的學術問題, 比如五大名窯中哥窯的產地和鈞窯的年代問題等,作者對這些爭議問題都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此外,書中也融入作者多年來在陶瓷領域的研究成果。
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時,陳克倫追憶恩師汪慶正對其陶瓷鑑定的培養,也提到了自己鮮少談及的瓷器鑑定心得和體會。
澎湃新聞:陳館長,您是知名古陶瓷專家,曾參與組建復旦大學文博系的框架,在復旦大學教授中國陶瓷史多年,應該說這本《瓷器中國》的出版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能先請您談談這本書的寫作緣起麼?
陳克倫:因為出版社也一直約我出這樣一本書,他們覺得我從事了這麼多年的陶瓷研究,可以出一本適合大眾閱讀的,普及性的讀物。我認為專業研究要出論文集,那要另當別論,這本書跟論文集不同,裡面所涉史料、考古材料都不是以引用的形式,而是用我理解後的話語來重新闡釋,因而更易於讀者的閱讀和理解。
澎湃新聞:有藝評界人士評價您這本書是“大家小書”,我覺得這是非常貼切的。寫作這本《瓷器中國》您花了多長時間,以及您都是如何構思的?
陳克倫:寫作時間是比較快的,從去年開始,歷時一年。因為多年來從事陶瓷器的研究及其相關領域工作,有很多積累,所以寫起來很快。我首先確定它的體例,不是以通識寫作的方式,而是以瓷器的不同品種來分目錄,這樣更便於讀者理解。比如介紹青花瓷,就從青花瓷的創燒到後來的發展這是一個比較連貫的脈絡。如果按過去通史寫作來寫,一會兒介紹這個品種,一會兒闡釋那一品種,不利於讀者理解。同時我把一些瓷器的學術問題也囊括進去了,比如五大名窯中關於哥窯的窯口和鈞窯的年代等一些有爭議的學術問題,我在書中都談到了自己的觀點,以及支撐這些觀點的依據。
《瓷器中國》我請中國陶瓷界的老前輩,已經百歲高齡的耿寶昌先生作序。耿老建議我可以將本書體例大大擴充,再出一本大書,因為這本書還是比較簡略的,原先我定的書名是《中國瓷器簡史》,出版社認為《瓷器中國》更好,可以引起人們對於中國瓷器的聯想。這本書我在寫作上不追求瓷器歷史的面面俱到,而是著重解析它的文化和歷史內涵。
澎湃新聞:在具體寫作過程中,您是如何做到將專業知識通俗化闡釋?我翻閱您的這本著作,印象尤其深刻的是您選擇的文物配圖,選的都是非常典型的標準器,對照文字邏輯甚至可以透過圖片看到瓷器的細微差別。
陳克倫:我儘可能用一種比較通俗的語言來寫作,從我過去所寫文章用的那類比較生澀的專業術語轉化成一般讀者都能夠看懂的文字表達,讓讀者瞭解中國瓷器發展的這段輝煌的歷史。另外我在文物配圖的選擇上,所選瓷器全部都是有著權威出處的,公家機構的收藏,都是非常可靠的。
我們現在都在講讓文物講故事,書中300多張配圖就是文物,我寫的文字就是故事。
師從汪慶正學鑑定
澎湃新聞:過去跟您做過一個訪談,基本回溯了您的人生履歷,尤其是每一次面臨人生選擇的關鍵節點,當時對於您的陶瓷研究談得不是很深入。作為知名古陶瓷專家、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委員(陶瓷組),陶瓷研究和鑑定才是您一直以來的專業,您在專業領域主要師從汪慶正,他是如何教您學習陶瓷鑑定的?您在陶瓷學術研究方向上有沒有受到他的影響?
陳克倫:汪先生最重要的是他培養了我陶瓷鑑定,另外他很早就引入新的科技手段來論證學術觀點,這點對我後來的學術研究影響深遠。
我大學是在廈門大學唸的考古專業,但是我比較感興趣的是陶瓷考古,因為當時教我們宋元考古的老師很關注這一點。而且我在福建念大學,福建窯址很多,唸書的時候我們就去過建窯考察,廈門附近還有同安窯,我都去過。大學畢業後被分到浙江省博物館,浙江的青瓷非常出名,我又對青瓷產生興趣。兩年以後我考上了復旦大學文博碩士,我們是由復旦大學和上海博物館聯合培養的,當時我的導師楊寬先生已經去美國了,我就選了上博的導師,跟隨汪慶正先生研究陶瓷,汪先生也只選了我一個學生,當時都是有正式的拜師儀式的。
汪先生第一次授課,讓我簡明扼要得把中國陶瓷史講述一遍。我才講到一半,他就說“你可以不用講了,你講的都對。”
他還讓我閱讀上海博物館的專業書籍。汪館長說過一句話,對我影響非常大,他說,對於文物研究來說,一定要首先會看東西,然後才會寫文章。我們博物館的學者和大學的學者最大的區別就是會看東西,大學的學者洋洋灑灑寫幾萬字的論文,如果論據是錯的,那麼整個文章就廢掉了。所以要鍛鍊自己的眼力是非常重要的。
汪先生當時雖然已經擔任副館長,工作非常繁忙,但每個禮拜會有兩個半天從庫房提出20餘件文物,一件一件上手仔細看,以時代先後、不同地區、不同窯口的器物分別觀摩。開始是先由汪先生講解,我作一些認知的總結;後來汪先生要我先講,他再作一些補充,主要是看看我在鑑定方面是否有“悟性”。

2002年3月,陳克倫與汪慶正先生(右)一起在日內瓦鮑爾文物館考察成化鬥彩。
在學術上,汪先生具有很強的學術敏感,非常關注陶瓷發展史上的一些重大課題,比如他對於汝窯遺址的發現和確定。

汝窯窯址久尋不得。1931年日本學者到河南臨汝尋找汝窯;1950年中國古陶瓷專家陳萬里、馮先銘先生到臨汝、寶豐、魯山考察窯址;20世紀50至70年代,河南省文物考古學者和北京故的專家多次為尋找汝窯到臨汝及附近一帶考察,終沒有真正發現汝窯址。1986年10月,中國古陶瓷研究會在陝西西安召開年會,河南省寶豐縣陶瓷工藝廠王留現向一些專家展示了他在寶豐清涼寺採集的1件青釉瓷洗,引起了與會專家的重視。在這一線索下,上博汪館長於當年年底兩次派人前往清涼寺窯址調查,找到了與傳世汝窯一樣的瓷片標本及窯具。1987年初在上海《文匯報》釋出了發現北宋汝的訊息,並於1987年10月出版《汝的發現》一書,認定寶豐清涼寺瓷窯遺址為汝官窯窯場。1987年10月和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清涼寺次址進行了鑽探和試掘,確認窯址範圍並發現了典型的汝標本,從而證實了汝窯遺址的地點。當年清涼寺採集的這件標本後來還被上博收藏了,我們把它的口沿修放在展廳展出。
汪館長研究問題的角度跟別人也不太一樣,他在國內陶瓷鑑定方面很早引入新的科技手段。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中心的科技手段是很豐富的。比如涉及陶瓷器的斷代、窯口等爭議性問題,大家各執一詞,這時候就用科學儀器來幫忙,用科技資料來說話。
澎湃新聞:確實,我在您的書中非常多的章節都能看到您對科技手段、科學儀器的運用案例。
陳克倫:是的,我在書中談到很多有爭議的學術問題,都是用一些科技方法來論證。我們在這一方面起步是比較早的。
比如北宋官窯是長期困擾學術界的一個重要問題,根據記載,北宋官窯在河南開封,但至今尚未發現窯址。由於尋訪一直沒有結果,於是有學者認為文獻記載的所謂“北宋官窯”實際上就是汝窯,對此,汪先生始終持反對態度。1999年夏天,河南有人把在汝州城內張公巷一處建築工地發現的青瓷標本送來上海請汪先生鑑定,引起了汪先生的極大關注,它們與上海博物館收藏的4件相傳1940年代河南開封出土的青瓷標本無論在胎釉、造型、工藝等方面都完全一致,與大英博物館收藏的“亞歷山大碗”也基本相似。

2004年7月,陳克倫與汪慶正先生一起在倫敦大英博物館考察“亞歷山大”碗
張公巷窯發現之後,有學者認為窯址距清涼寺汝窯窯址不遠,應該屬於汝窯的一支;考古發掘者則從窯址中發現有金代、元代的標本,認為張公巷窯的年代屬於金代或者元代。為了解它們之間的關係,汪先生把上博收藏的標本和張公巷窯出土的標本一起交給中國科學院上海矽酸鹽研究所進行科學測試,結果發現兩者胎、釉的化學成分類同,可以認為是同一個窯址的產品,有可能是北宋官窯的產品,如果確是如此,那麼張公巷窯的發現就有可能解決僅見於文獻記載而不見實物的北宋官窯的問題,這是一個重大的學術問題。
以後我繼續研究汝州張公巷窯與清涼寺汝窯的關係,與汪先生一樣,除了利用考古資料之外,還利用科技手段測試清涼寺汝窯、汝州張公巷窯和上博青瓷標本,得出的結論是:張公巷窯與上博青瓷標本的胎、釉化學組成,不僅常量元素基本一致,而且可以判斷原料產地的微量元素也相同;它們與清涼寺汝窯則存在較大的差別,這些差別導致了兩者在外觀上的不同。雖然兩地相距約40公里並不遠,但是產品有明顯差別,嚴格地說還不能歸為一類,這就進一步證明了汪先生的判斷。另外。運用熱釋光對標本的年代進行測試,得出結論:張公巷窯的年代和汝窯的年代相差不多,如果清涼寺汝窯屬北宋產品,那麼張公巷的時代也不會到金代,更不會是元代。
此外,我在書中還提到哥窯、鈞窯這類陶瓷界富有爭議性的學術問題。比如哥窯的年代和產地問題,北宋鈞窯的年代問題等,這些都是很重大的學術問題,每一個問題都可以單獨開一個研討會。
澎湃新聞:您認為瓷器鑑定的要點是什麼?您是如何對此瓷器做鑑定的?
陳克倫:與傳統的文物鑑定方法不同,過去汪先生非常注重從陶瓷製作工藝的角度找出不同時期、不同品種器物的特點,只有瞭解了不同的工藝手法,才能認識不同特點的形成原理,才有可能總結出鑑定的要點。與汪先生不謀而合的是,上海博物館的馬承源先生在教授青銅器鑑定時也十分強調鑄造工藝的作用,青銅器陶範合範時留下的“範線”,固定內模、外模間隙的“墊片”乃至“澆口”“冒口”位置等鑄造時留下的痕跡,往往成為青銅器鑑定的重要依據。所以日後我也跟我的學生們說,你要研究陶瓷器,首先要了解瓷器是怎麼做的。因為瓷器在製作過程中會留別人不太注意的痕跡。這個痕跡很可能後世的仿造者也沒關注。這就是瓷器鑑定很重要的一方面。
比如關於元青花的成型工藝,根據文獻及實物驗證,瓶、罐類、“琢器”以陰模印坯分段成型,然後節裝的工藝,在元青花器物的內壁可見用手或布抹平溼泥留下的抹痕,與拉坯、利坯留下的痕跡明顯不同;碗、盤類“圓器”採用直接將坯泥置於陽模上,人工擠壓拍打成型的工藝,與傳統的先拉坯、後用陽模印拍定型的工藝迥異,脫模以後再置轆轤車上旋轉修正器物外壁並挖出圈足。高足器的器身和足分別以陽模和陰模成型,然後以“接頭泥”節裝。元青花大量採用模印方法成型的原因之一是胎泥中加入可塑性較差的高嶺土,增加了拉坯的難度所致。高大器物可見明顯的橫向接痕。

元 景德鎮窯青花飛鳳紋葫蘆瓶 土耳其伊斯坦布林託布卡普博物館藏
再比如雍正的官窯瓷器。翻過來用手摸它沒有釉的圈足,非常光滑。為什麼呢?因為出窯的時候打磨得非常仔細。雖然康熙和乾隆的瓷器也打磨過,但是不如雍正打磨地那麼細。
澎湃新聞:所以瓷器鑑定很注重看底部的圈足對麼?
陳克倫:一定要看底部,底部可以看出它的燒造工藝。其次要上手掂量,上手就是要掂量它的重量。
澎湃新聞:對於瓷器鑑定,您最擅長鑑定的是哪個瓷器品種?
陳克倫:對於上海博物館的工作而言,都要擅長。因為上海博物館收藏的陶瓷從新石器時代一直到清代都有。如果只擅長一個時段,具體工作很難開展。有時候眼鑑吃不準,就難免要請文保中心的同事藉助科技手段來幫忙。
鑑定也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在改變,過去我們一直說“眼學”,現在越來越多的藉助科技手段,不過即便是現在眼學還是能解決大概95%的問題,“眼學”不能解決的問題是很少的。

唐 長沙窯青釉褐斑模印貼花獅紋雙系壺 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
凝結多年學術成果
澎湃新聞:上次跟您訪談了解到您的研究方向和學術成就比較多得集中在對元青花、印尼“黑石號”沉船上的唐代瓷器的系統研究,較早開展對北宋早期龍泉窯、北宋越窯分期,而且在國內學術界很早就對明代洪武時期景德鎮瓷器進行系統研究。我關注到您這本書的寫作並不是追求宏大敘事、面面俱到,也不是均衡使力,而是將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融入其中,比如在青瓷、元青花等篇章內容特別豐富,元青花談到國內對其的認識和研究歷程、元青花的成型工藝、景德鎮生產元青花的窯址、元青花的年代、元青花的文化來源、元青花的性質等。
陳克倫:是的,我比較注重瓷器的比較研究,在陶瓷研究中關注中外文化交流。比如在元青花研究中,透過中外文化綜合比較研究,較早提出元青花主要用於出口,伊斯蘭文化對其興起與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的結論。
元青花發源於中國,無疑主要傳承中國傳統文化。但是它的出現有特殊的歷史原因,又處在元代這個多民族交融的歷史環境之中,因此元青花包容了眾多的文化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國文化和伊斯蘭文化。元青花中的中國文化因素,主要表現在器物造型和裝飾方面。典型元青花的造型大部分是繼承傳統造型演變而來,如梅瓶、玉壺春瓶、蓋罐、葫蘆瓶等。元青花裝飾中的人物故事般以元曲為本,人物形象多為中國裝束。動物和植物題材中許多內容都是中國唐宋以來傳統裝飾中所常見的。在元青花的造型及裝飾中也可以找到伊斯蘭文化因素。最多見的大盤與中國傳統的瓷器造型不同,而與中亞、西亞的陶製、金屬製大盤相似,這與伊斯蘭地區的圍坐共食的飲食習慣相符;扁壼是隨身攜帶的盛器,對於善於經商而經常外出的穆斯林是非常適宜的。
元青花裝飾上的伊斯蘭文化因素主要表現在顏色和裝飾形式方面。青花的藍色圖案不同於以往中國瓷器裝飾的傳統色彩。藍色是深遠、純潔、透明的象徵,令人感到神秘、渺茫和靜肅,這與伊斯蘭教所宣揚的教義和追求的“清淨”境界相符。因此用藍色裝飾器皿和建築就成為伊斯蘭文化的傳統。層次豐富佈局嚴謹、圖案滿密是元青花的裝飾特點,這種風格使人聯想起伊斯蘭地區的裝飾。在瓶、罐等琢器上用多層次的橫向帶狀分割槽形式裝飾在碗、盤等圓器上採用同心圓分割槽的方式多層次進行裝飾,這在13至14世紀早期西亞地區的金屬器皿和陶器上很容易找到它們的原型。
景德鎮元青花的製作或許還有西域工匠的直接參與,元青花流行還與藏傳佛教在元代的盛行有關。
還有一個關於元青花的性質,有學者認為元代景德鎮有官窯,元青花是御用瓷器,對此我是持否定意見的。
元青花當時主要作為貿易商品出去,而且典型的元青花主要都儲存在國外,國內很少。目前尚未有證據表明元青花的大量出口與朝廷的對外交往有關,亦未能證明元青花的生產與浮樑瓷局有關,因此其性質應屬商品,而生產商品的制瓷作坊的性質應屬民營。民營的制瓷作坊除了生產商品之外,也可以承擔官府和朝廷的定燒任務,其生產有餘還可以出售,甚至出口。
元朝以軍事立國,市舶收入是主要的財政來源,於是大力發展對外貿易成為國策。元青花為外銷而生產,是市舶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元青花只有作為民窯生產的普通商品輸出,才能保證市舶收入,這對元朝政府來說是很重要的。
澎湃新聞:元青花瓷器那麼有名,在普通讀者或者觀眾中認知度都很廣泛,主要因為它存世量稀少麼?
陳克倫:它存世量稀少,國內外加起來不足400件。至於它的藝術風格、工藝價值有人喜歡,也有人不喜歡。它跟中國傳統的審美風格不一樣,中國傳統風格講究文雅,追求釉色美,造型美。它是滿密的花紋。而且藍顏色不符合中國傳統對顏色的喜好,它一定是迎合了伊斯蘭文化因素。
青花瓷器從元代到明永樂,已有約70年的歷史,由於紋飾的繁複而被人視為“俗甚”的青花瓷已逐漸被國人接受。當然自永樂起青花的裝飾風格也慢慢向符合中國人傳統的疏朗、簡約的方向靠攏,這就使青花開始進入中國的主流社會,遂成為景德鎮生產的最主要的品種。
澎湃新聞:從您的角度來看,中國瓷器史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有哪幾個高峰?
陳克倫:中國瓷器從真正的成熟青瓷在東漢出現以後直到魏晉南北朝,基本上都是青瓷一統天下。到宋代開始百花齊放,出現各種瓷器品種。宋瓷是一個高峰,元代元青花瓷器可以說也是高峰。明清以後瓷器品種更加豐富,到清代乾隆時期瓷器種類是最豐富的,景德鎮的瓷器達到頂峰。撇開藝術審美不談,單從工藝技術來說,乾隆時期景德鎮窯制瓷工藝高度發展,什麼都能做,比如仿工藝釉瓷器,它以瓷為胎,透過各種高溫、低溫釉和彩繪工藝,仿製銅、玉、石、竹、木、漆、等各種質地的器物,惟妙惟肖,達到可以亂真的程度。
從藝術審美角度來看,可能又另當別論。比如清三代的瓷器,康熙的比較古樸,雍正的比較典雅,乾隆時期的瓷器比較繁複。有的人喜歡,也會有人評價俗氣。
澎湃新聞:像您本人比較喜歡哪個朝代的瓷器?
陳克倫:從整個歷史階段來講,我比較喜歡宋代的瓷器,比較文雅。澎湃新聞:您如何看待當下陶瓷的發展?
陳克倫:當代陶瓷的發展現狀,現在有兩種做法,一種是拼命仿古,一種就是要有創新。我覺得只有創新,我們中國的陶瓷工藝才有前途,不能一昧去仿古,但我們要學習古代的一些先進工藝,過去有些工藝我們到現在還做不到。我們首先要學習古人是怎麼做的,然後在這個基礎上一定要創新。無論是工藝上,還是藝術上都要創新。
責任編輯:李梅
校對: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