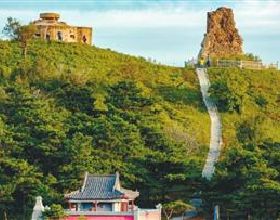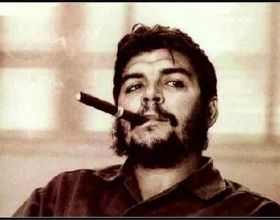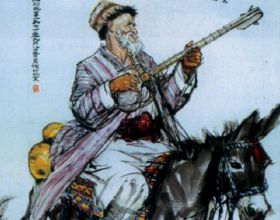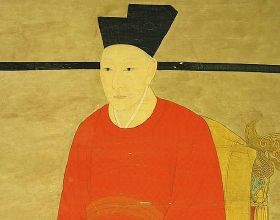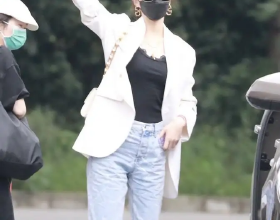大清朝曾經實施過政改,當時政改措施之一就是要撤“地級市”,即“府”這個層級。當時的清代地方行政區劃,大體上是省—府—縣三級。但在官階設定上,省、府之間,還有“道”,實際上是省—道—府—縣四級,再加上清廷中央,“展轉五級”,效率低下。數千年來,縣一直是我國最為基層的行政單位。至於鄉村的一應事務,基本由鄉紳負責、以鄉規民約為約束。
自晚清改革開放,政權迅速滲透到了鄉村基層,逐漸形成了鄉。在中央政改領導小組“官制編制館發給各省討論的方案中,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令現設知府解所屬州縣專治”,取消了知府這一級“地級市”建制,及直隸州、直隸廳對所屬縣的管轄,將所有的縣級行政區域一律歸省直屬。如此一來,縣的地位和功能大大提升。
所有州縣被分為三等,“甲等曰府,乙等曰州,丙等曰縣”。“府”一級的州縣,其長官雖然還是稱為知府,品秩也高於州、縣的行政長官知州、知縣,但他們之間並無隸屬關係,都是縣級單位,府無非是規模大一些的“縣級市”而已。
誰都沒想到,對於這一方案,最大的反對意見來自一貫以來的改革先驅張之洞。張之洞反對的第一個理由,是“各省幅員遼闊,輪舶罕通,每一府所轄少則四五縣,多者至十縣。各縣距省遙遠,極遠者至二三千里,賴有知府,猶可分寄耳目,民冤可伸理,災荒可復勘,盜匪可覺察飭緝。若盡歸省城考察,豈能遍及?待該縣稟報至省,禍亂已成;控告到院司,民命已斃矣。故裁去知府一說,萬分窒礙,勢有難行。”當時,全國總共有縣級行政區劃(州、縣、廳)1600多個,18行省平均每省88-89個。根據當時的交通、通訊條件,如果這88-89個縣,全部直屬於省,的確會出現張之洞所說的管理難題。
張之洞說的第二個理由,是關於名詞應用上的認為將一些大縣稱為“府”並不合適。張之洞的第三個理由,與其反對司法獨立相關。對於中央方案中提出的審判機構獨立,“督撫不司裁判”,張擔心,“疆臣不問刑名”,則“愛民治民之實政,皆無所施。”張之洞還擔心,如果立即推行司法獨立,首先是民眾的司法成本將大大增加,所有的“上訪”將只能到省裡、甚至中央;其次,是司法效率大大降低;第三,是督撫失去司法權之後,難以約束下屬官吏。這些顧慮,有相當程度是對司法獨立的誤解,也有相當程度的確是符合現實的。
“府”一級不可撤,在張看來,“道”一級也不可撤。清代道制,沿襲自明代。明制中,將全省劃分若干道,由主管經濟的布政司、主管司法的按察司派出“道員”駐守或巡視。屬於布政司者的,稱為“分守道”;屬於按察司的,稱為“分巡道”,實施對省內政務的督察。這個層級本非一級行政長官。到了清代中葉,“道”的劃分日趨固定,“道員”也日漸成為一級行政長官。除了按照地域之“塊”來劃分的“道”,還有一些按照職能之“條”來劃分的“道”,分別主管漕、鹽、糧、茶、馬、河、關、驛、海防、兵備等,以及改革中增加的洋務、海關、路礦、電信等。
張之洞認為:“前三十年軍務、近二十年教案等事,則道員之責較重,取其官階較崇,調遣武營較易。故地理學家之要訣,須先將一省各道之疆域分清,則一省之形勢脈絡瞭然於胸,此可知前人建設巡道之有深意、有關係矣。”針對有人擔心,“府之上添一道員,徒多層折重複”,他譏諷說,這是“未知外官例章職守,道府各有取義”,是典型的官僚主義。張之洞舉例說:“如湖北之襄陽道,則有關三省邊防教案;湖北新設之施鶴道,亦專為教案邊防,均甚有關係,似不應在裁撤之列。此外,即如湖南鎮、江南徐州、河南南汝光、四川建昌、甘肅寧夏,安徽廬鳳潁,此數處皆非糧、鹽、關、河,然豈可無道臺鎮守?”因此,他認為,“各省道員,似以不裁為尤妥”。
作為最有威望和實力的地方大員,張之洞對州縣改革,實際上幾乎全盤否定。張之洞的意見,具有相當代表性。張之洞絕非政改的反對者。在張之洞這份洋洋四千多字的長篇奏摺中,並不反對立憲政改,甚至還力推議會制度。他提出的反對意見,與其說是否定,不如說是透過提供第一線的實際情況,協助方案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