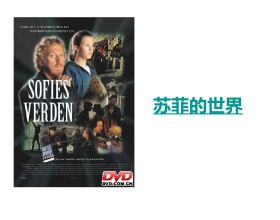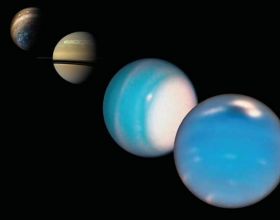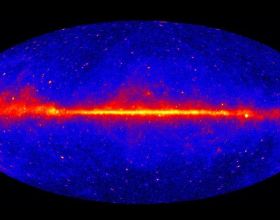中央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蔡鳳林在《日本文論》2021年第1輯(總第5輯)發表《東亞歷史視域下的日本天皇制形成過程探析》(第1-25頁)。
蔡鳳林認為,在日本政治史研究中,天皇制是核心課題之一。日本古代天皇制的確立是以律令制國家建設為政治前提的王權高度集中過程,呈現出律令制建設與天皇制建構交融並進的政治發展軌跡。天皇制形成的內因在於古代日本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以及隨之產生的國內政治發展需求,外因則是圍繞朝鮮半島問題展開的東亞國際環境對日本的深刻影響。古代日本始終和東亞大陸保持著緊密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聯絡,在古代日本統一王權的建立、律令制國家建設、王權向皇權邁進、天皇制確立的一系列過程中,均能看到古代東亞地區政治文化發展及政治局勢變化的巨大影響。其核心紐帶是朝鮮半島這一文明通道,或可說朝鮮半島問題是催生日本天皇制的主要動力之一。
在日本政治制度史上,天皇製作為重要的組成內容和表現形式延續至今,且已成為日本的象徵之一。天皇制確立後,不僅對古代日本中央集權制國家的建立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對日本近代政治及國際關係也產生了極大影響。天皇制是古代日本王權及國家制度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的產物,其形成與古代日本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以及隨之產生的國內政治發展需求有著密切的關係。同時,歷史上推進天皇制形成的動力還存在外部因素,譬如7世紀以前圍繞朝鮮半島問題展開的東亞國際環境。內因和外因的互動作用促成了日本這一獨特的政治制度。
一、日本早期王權的形成與古代東亞社會
王權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體現國家權力產生和存在的一種普遍形式,皇權則是以皇帝為核心形成的國家政權存在形式,是王權高度集中、擴大的產物。日本天皇制的確立也經歷了一個由王權向皇權發展的過程。
(一)日本國家雛形及統一王權的形成
作為由各種典章制度和組織機構支撐的政治實體,國家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的產物。古代成熟國家的本質特徵是基於一套複雜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組織實現政治權力的高度集中。日本的國家雛形“邑落國家”是在公元前3世紀或更早的時期由朝鮮半島移居至日本列島的稻作民族建立,這是日本王權雛形形成的特點之一。
中國的西漢時期,日本列島“百餘國”林立的政治局面向列島統一王權邁進,這大致發生在3世紀初。日本統一王權的雛形邪馬臺國聯合體形成的重要動力是日本列島各部族希望獲得朝鮮半島的鐵資源或經由朝鮮半島得到中國的先進物質。
軍事和外交是構成王權的兩大要素。倭王權是奈良盆地各豪族長為了共同掌控通往朝鮮半島這一文明通道而聯合起來的產物,故在王位繼承方面必然要求其繼承者具有外交和軍事指揮能力。5世紀時倭國在統一的專制王權形成道路上邁出了一步,這與得到中國劉宋王朝的政治支援並採用中國的政治制度有著直接的關係,而其根源在於朝鮮半島動盪的局勢。
(二)日本基於“血緣原理”的王位繼承製的形成
天皇制的思想基礎是由專制意識和皇位繼承原理構成。其中,皇位繼承原理是基於“血緣原理”的王位繼承製的發展形式。向王位繼承製中匯入“血緣原理”是中央集權制和天皇制建設程序中的重要步驟和環節。
“倭五王”以後,6世紀初即位的繼體天皇的父系是近江(今滋賀縣)豪族,母系是越前(今福井縣)豪族或出自近江的息長氏。繼體天皇出自地方豪族。在天皇制發展史上,繼體天皇的即位是重要的轉折點。此外,繼體天皇的成長環境及其成功即位與古代日本移民集團“漢氏”有密切關係。
7世紀末以前,日本的內政與朝鮮半島問題緊密交織在一起,外交直接影響其內政。7世紀後半葉,日本在“白村江戰役”中慘敗而陷入空前的國家危機。為了建立以倭王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制,強化倭王血統和政統的緊迫性加劇,於是倭王開始編造王位譜系,其最後的成果便是出現在《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中的“皇統譜”。
二、天皇制的確立與古代東亞社會
早期王權的形成不代表皇權的建立,但早期王權是皇權建立的政治基礎。日本天皇制的確立亦是以律令制國家建設為政治前提的王權高度集中過程,呈現出律令制建設與天皇制建構交融並進的政治發展軌跡。儘管推古朝改革尚未廢除部民制而實施真正意義上的律令制度,但開啟了日本律令制國家建設的程序,王權得到加強。在日本律令制國家和專制王權建設程序中,大化元年(645)開始的大化革新是一次轉折點,朝鮮半島問題促成了大化革新。
大化革新是日本天皇制確立的前夜。7世紀後半葉天智朝和天武朝的改革促成了日本律令制國家的確立,而這些改革的主要動力亦來自當時日本所處東亞國際政治環境的影響。天智朝、天武朝改革,使日本律令制國家建設程序出現了質的飛躍,其代表性成果是《大寶律令》。律令編纂體現的是高度中央集權制國家建設的精神,“天皇”號的啟用應是與日本律令編纂事業同步進行的。“天皇”號應啟用於天武朝。至於天武天皇使用“天皇”而未用其他專制君主稱號,這是基於他與唐朝皇帝的對等心理而仿效唐高宗李治做法的結果。
三、餘論
在古代,日本積極汲取以中華文明為核心的大陸文明,對東亞大陸呈現出一以貫之的文化“開放性”(近代以後這種“開放性”轉向歐美),其進步發展與中華文明(這裡主要指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滋育緊密交織在一起;日本傳統文化的形成與日臻成熟是和吸收中華文明同步展開的,其主因在於中日文明發展層次間的巨大落差和日本社會生存、發展的需求。人的本質特徵是社會關係的總和,人類以群體形式才能生存發展;同時,人類群體的發展往往又是不同人類群體之間互動的產物。
在日本政治史研究中,天皇制是核心課題之一,其形成固然與古代日本國內政治程序的需求有一定的關係,但作為古代日本國家體制的主要發展形式之一,歷史上推進日本天皇制發軔並走向確立的動力還需要考慮7世紀末以前日本所處的東亞國際政治環境影響這一重要外在因素。直至7世紀末8世紀初天皇制確立,日本王權的建設發展始終沒有超越與古代東亞社會間緊密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絡而獨自推進,其主要動力是日本對朝鮮半島這一攝取中華文化要素的文明通道的覬覦。簡言之,朝鮮半島問題是催生日本王權及其發展形式天皇制的主要動力之一,日本人的“大陸夢”古已有之。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文論》特稿,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如需轉載,請註明作者姓名及出處。圖片來源於網路。實習編輯孫麗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