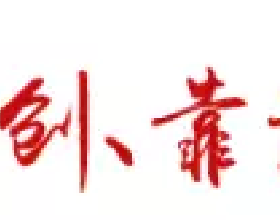我的父親生於1931年,到今年就91歲了。男性活到九十的比較少,所以,他們這一代基本上都走向凋零了。而我的父親零落得更早,他於上個世紀就離開了人世。1994年的4月19日,清明節過後不久的一個早晨,他以一種決絕的方式永遠告別了這個世界。
從1931年陰曆的七月初一到1994年陽曆4月19,他的人生只走過了63個年頭。在這63年裡,他當過農民,參過軍,打過仗,轉業回來當了工人,五十多退休後又回覆到做一個農民。工農兵他都經歷全了。如果他受過良好教育,會寫作,我相信他能將自己的一生寫成精彩的傳奇。
他一生的大致經歷是這樣的:
他出生在湖南常德市郊的一個農戶家庭,祖輩是清代從江西因做竹木生意遷移而來的劉姓家族,老家在常德桃源的陬市。據傳他的爺爺輩有七個兒子,取名“富貴雙全龍虎榜”,因是朝字輩,而我的曾祖父又是其中最小的一個,所以,就叫劉朝榜。他年青時自謀生路,從桃源陬市下到常德市郊來打拚,在大西門外的騾馬店那裡安了家落了戶。我的父親以及後來的我們幾姊妹都出生在這個地方——在我爺爺付出生命代價救下來的老木板房裡。
我父親只有五歲我奶奶就沒了,給他留下了一個妹妹,但妹妹在八歲時因為去河裡挑水淹死了。而在我父親13歲的時候,我的爺爺也因肺部灼傷吐血而亡。1943年11月日本侵略者開啟通往西部的通道,對常德發起了進攻。戰役先是在外圍一些市縣進行,到了11月24日才真正打到常德。住在市郊的民眾基本上都跑光了,但是我的爺爺沒有跑,他留了下來。這一天當日本向常德城發起進攻時,市郊的許多房屋都被炮火點燃了,我家的老屋也不例外。凝聚幾代心血的房子就是一家人的命根子,房子沒有了,一家人今後到哪裡棲身?所以,當房子燃起大火時,爺爺奮不顧身地衝了上去,用一已之力全力撲打,房子算是保住了,但我爺爺因為被焚燒的煙火灼傷到呼吸道,引起肺部感染,結果於第二年即1944年咯血而亡。他死時年僅36歲,留下不滿13歲的兒子。所以,在13歲上,我的父親就成了一個孤兒。
(老照片:爸媽結婚時與媽媽家裡人外婆、姨媽、舅舅合影)
成了沒爺沒孃的孤兒後我父親的生計從哪兒來呢,因為要去田裡舉起鋤頭挖地他實在太小了,所以,他就學著做一些小生意。其中也如中國別的地方許多失去爹孃的孤兒一樣,受盡了別人特別是眼紅他的一點小財產(其實就是我爺爺拚死救下來的那一間小房子,因為是我爺爺救下來的,所以分家時我父親就多分了一點房產)的親戚們的欺侮。我們要看過《儒林外史》,無疑不會放過這樣一個情節:有一個姓嚴的貢生,他弟弟死後留下一個男孩子,為了霸佔弟弟的那份家產,他名義上是把他弟弟的兒子接過來撫養,實際上是不給吃不給穿,把他活活折磨死了。中國古代社會就是這樣,人親不如財產親。
然而無論世事多麼艱難他仍然是一個人頑強地長大了。臨近解放前夕(1949年),物價飛漲,民不聊生,我剛滿18歲的父親沒有生路,只得參加了國民黨的部隊,開往四川去做蔣介石夢想割據大西南的炮灰。但他們剛到四川沒多久,西南就解放了,父親的部隊被收編為劉鄧大軍即第二野戰軍第三兵團的一部分。
1950年朝鮮大地燃起了炮火,金日成向中國求援,剛剛成為解放軍的父親便跟隨二野的第三兵團上了朝鮮戰場。據說當時二野參加抗美援朝的軍隊是第三兵團的12軍和第15軍,他們是在1950年的11、12月由四川開到河北進行整訓、改裝的,於1951年3月入朝作戰。而15軍和12軍正是打上甘嶺戰役的主力部隊,所以,沒準我父親參加的這次戰鬥就是上甘嶺或周邊戰役中的一場。父親從來沒有提過這個戰鬥,因為他們對過去的事基本都是保守於心的,對於他的過往我都是道聽途說。據說當時他們班打得只剩下我父親一個人,而他也負了傷,後來在哈爾濱的一家醫院住了一個多月。
一個孤兒,為了生活的出路把自己命交到了軍隊手裡,結果在戰爭的最前線幸運地撿回,了一條命,得以為老劉家的么房(我爺爺是三兄弟中的最末一個)延續香火。轉業回鄉後他被安排在常德船舶廠工作,成為一名國營職工,在電焊工的崗位上一干就是三十年。因為國家前三十年多動亂,他的四級工很多年沒有調整,一直拿著四十多元的工資,就用這工資養活一家六口人(因為我母親的戶口在農村,沒有多少收入)。從德山的船舶廠一週一次回到家裡,休息一個週日,他啥都會做,拖豬食料,餵豬,出豬籠,做藕煤,打地爐,挖地,種菜,挑糞,澆園。記得有一年春天的週日,下著細雨,他挑了一擔菜秧子去賣,到了天黑才回,走了一天,滿身的疲憊,擔子裡還剩下幾坨沒有賣完的菜秧。他給我們講述他這一天走過的地方。一天的挑擔行走!他要多勤奮有多勤奮,而家裡是要多貧窮有多貧窮,一個工農相結合的家庭,有一份穩定的收入,尚且十天半月才能吃一次肉,孩子們衣服都不夠穿,更何況其他山區的、純農村戶口的家庭。看過父母走過的最辛苦的人生路,才知道今天的時光有多麼的美好。
八十年代,由於我姐姐想接父親國營職工的班,父親五十一歲就退休回家了。他重新成為了一個農民,用他的聰明才智來種菜養殖。他給我講過他種菜的方法,如何先深挖土地,將雞糞什麼的做打底肥,先施下土地去,然後又把田壠耙得細細的等等,總之是精耕細作,所以他種出的菜總是茁壯肥美,特別是他種的菜花,又大又白,搞得人看到忍不住想偷,害得我父親半夜還要起來去巡視菜地。
1992年父親發現自己的喉嚨疼痛,後來經過檢查,是喉癌。經過一系列錯誤的治療,父親最終是在1994年4月走到了人生的邊緣。父親的去世是我最不堪回首的一幕。因為錯誤的化療,他這時身體已經極度虛弱,也不能夠再行手術,只能等死。復發的癌仍在那裡,沒法消除,疼痛每天都在折磨著他。只有吃下一顆藥力強大的安定(不知具體是什麼),在神經麻痺的情況下,他才能安睡一會兒,但更多的時候是無窮無盡的折磨。他體重變得極輕,大概只剩下七八十斤,這時候,我們才真正明白什麼叫做無奈的人生,因為看著父親受折磨,我們完全無能為力。我們不能幫他或代替他任何一點什麼。而他又是多麼留戀人世!有一次他做夢,醒來,說他做了一個很好的夢,他沒有說是什麼夢,我也沒問,因為現實是這樣,夢再好也不能改變什麼,只能越問越難受,只聽他喃喃地說“真好。”是的,如果一切能如夢中那樣真的該有多好啊,可是現實不是夢。現實是我的父親被癌症折磨得奄奄一息。終於,在一個春天的黎明,他決絕地將一把慢慢攢下的安定神經的藥吞了下去,讓自己遠離了病痛的折磨,也遠離這個塵世,遠離了自己的親人。一個平凡、普通的中國人就這樣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的經歷是千千萬萬中國人的經歷,而他的人生也是最最普通中國人普遍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