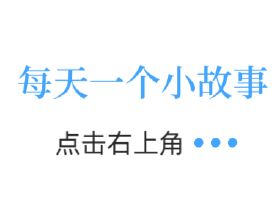前言
“要將共產主義從內部瓦解!”
這是時任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曾發出的宣言,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並不能說他失敗,畢竟東歐劇變就是最大的功績。
二戰結束後,以美蘇兩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便進入長期的冷戰對峙狀態。這種基於意識形態的交鋒,逐漸演變為軍事力量、經濟實力、文化習俗等諸多方面的較量,最終以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兩件事徹底宣告冷戰的結束。
冷戰雖然結束,可美國及其盟友擴張的步伐並未停下。近來“北約東擴”成為一個至關重要的話題,而東擴的前提便是這些國家要有強烈加入北約的“願望”。
在過去幾千年的戰爭中,往往侵略的鐵蹄是結束一切紛爭的最終辦法,而進入到“核武時代”中,這種侵略必須包裝上一層糖果的外衣。
毛主席和杜勒斯的“交鋒”
毛主席和杜勒斯一生素未謀面,但兩者在中美關係上的交鋒卻並不少。
杜勒斯,1888年2月22日出生在美國華盛頓一個政客家庭中,他的外祖父是本傑明·哈里森政府時期的國務卿,1895年的時候還被聘請為清政府的特別顧問,同李鴻章一起參加《馬關條約》的談判。1907年,杜勒斯同自己的外祖父參加清政府的外事活動。可以說,他的前半輩子就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
或許他正是見過那個孱弱、多病的清廷,才會對中國有一種莫名的優越和無禮的傲慢。
艾森豪威爾總統上臺後,杜勒斯被任命為國務卿。即便兩人都擁有著強烈的“反共”意願,可在核武上的軍備競賽讓他們不敢輕舉妄動。這段時間,杜勒斯也算得上是苦心鑽研。
在1957年4月23日,杜勒斯在紐約發表的演講時說道:“要將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要把希望寄託在他們的第三、第四代人身上。”這個時候,這一邪惡的想法還在萌芽當中,杜勒斯毫無以為是開啟潘多拉墨盒的那隻手。
此後杜勒斯因癌症住院治療,而毛主席知道此事後,倒是幽默風趣跟來中國訪問的美國學者杜波依斯說道:“如果我去美國的話,除了想去密西西比河裡游泳,還想看看艾森豪威爾總統打高爾夫球,或者去醫院探望一下杜勒斯先生。”
杜波依斯思索一下,笑著說道:“這可能會對他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毛主席擺擺手說道:“這可不是我的用意,我非常希望杜勒斯先生能康復,作為美國國務卿,他對我們很有用。同時,他對美國人民,乃至對全世界勞動人民都有用。”
身旁的人有些不解,為何一個積極“反華”的人會有用呢?
毛主席進而說道:“像杜勒斯這樣的右翼分子對世界是有用的,他越是堅持他的原則,就越有反面教材的作用。”
今天我們再來看這句話,真的驗證了一些道理。杜勒斯所推崇的和平演變,終究演成為美國人自己的笑柄。
1969年4月,杜勒斯去世,雖然他沒有親眼看見社會主義“崩潰”,但他的種種謀劃還是被美國人繼承下去並得以成功。
東歐劇變和蘇聯之殤
在美蘇冷戰對峙的過程中,歐洲成為必爭之地,同時北約和華沙兩個龐然大物也先後崛起。
所有革命的底層動力,都是因為經濟薄弱,但我們今天不側重地去談經濟、軍事等問題,而是去將西方國家是如何透過思想來使一個國家的政權顛覆。
1990年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小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一詞,他認為這是一個以文化和意識形態吸引力體現出的“實力”,在資訊時代,軟實力爭辯得比以往更為突出。
其實美國之所以能成功入侵看似銅牆鐵壁的蘇聯和東歐,靠的就是軟實力。
美國當時向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宣傳所謂的“民主、自由”等觀念,當時有兩個知名電臺,分別是“自由歐洲電臺”和“美國之音”每天以各種語言針對東歐國家進行迴圈播放同西方有關的社會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報道。當然,這種報道是具有偏向性的,只挑好地說。
當時的資訊科技並不發達,人們知悉世界的方法大多都是看報紙、聽廣播。就像喂飼料一般,人家喂什麼,你就吃什麼。結合社會主義陣營的社會經濟並不發達,吃不飽、穿不暖的地方比比皆是,自然是對西方所提出的“烏托邦”似的社會心馳神往。
試想一下,一個勞累一天的工人,每個月掙到手的工資剛夠自己解決溫飽。回家聽到廣播以後,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一個宛如天堂的地方,誰能不心動?尤其是對於一牆之隔的東柏林人們,心中的激動、燥熱更是難耐。
在西方國家的慫恿下,東德人民的不滿情緒終於提前爆發了。1953年6月15日,東柏林的建築工人們率先罷工。
東德德反抗運動
在近代革命中,罷工、罷學的浪潮如同星星之火,一旦掀起便如同燎原。同時也會引起當局的極力鎮壓,駐守在此地的蘇聯軍隊迅速出動,最後釀成55人死亡的慘案。
千萬別以為“叛亂”僅僅發生在東歐國家,蘇聯內部也是“資本主義猖獗”。
1991年6月份,有一份民調顯示,針對蘇聯內部的黨政要員中僅有大約9.6%的人具有共產主義意識形態,12.3%的人具有民主社會主義觀點,76.7%的人認為國家應當實行資本主義。
當時在蘇聯政壇上有一種人被稱作“夜間人”,即白天在政治上依然保持著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活躍,可每到晚上就捧著西方印刷的地下出版物,讀得津津有味。一時間,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為蘇聯從上至下人人得而“噴”的一種制度。曾經被奉若珍寶的馬克思主義,如今被蘇聯人踩在腳下,唾棄、踐踏、批判。在這種情況之下,蘇共政府首當其衝地成為民眾反對的前沿陣地。
連身居高位的政客都尚且如此,遑論那些“願意接觸西方思想的進步青年”呢?
同時由於蘇共政府的一系列改革,放棄一黨領導制原則,導致參與政治討論的多數黨派被資本力量所控制。在政治事務的決斷上,反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亂。
一時間,各種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利己主義在蘇聯思想界充斥,思想之間的碰撞並未造就文藝復興,反而推著蘇聯走向最終的滅亡。
毛主席曾經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
如果單從這個角度來看,在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中,美國所謂的“和平演變”只是起到一個客觀的引導作用。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他們急於求成,自己把自己給玩壞了。
蘇聯解體後,顏色革命並未停止
迄今為止,在西方國家操控下成功的顏色革命的案例不在少數。
捷克斯洛伐克的“絲絨”革命、喬治亞的“玫瑰”革命、烏克蘭的“栗子”革命、伊拉克的“紫色”革命、黎巴嫩的“雪松”革命等等。這些人大多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壓縮俄羅斯的發展空間,以達成美國的戰略目的。
這裡我們就不得不丟擲一個問題,顏色革命對美國來說是勝利了,但對於發動革命的本國群眾來說,真的算贏嗎?
有不少歪屁股的人認為,烏克蘭顏色革命之所以能成功,當局迫不及待地想要加入北約是因為普京“侵佔”克里米亞。可事實上,烏克蘭發動的顏色革命始於2013年年底,而普京是等到2014年3月份才發動的克里米亞事件。
美國發動顏色革命的慣用套路就是在該國內部挑選一個有實力的反對派,藉以“合作”之名,發動一場顛覆現有政權的暴動。當初在烏克蘭境內選中的人,就是尤先科。
此人在蘇聯時期就是銀行寡頭,獨立後更是擔任烏克蘭銀行行長。或許也是有這層金融的關係,尤先科很快便跟美國搭上線,便在2004年的總統大選中脫穎而出。
實際上,當時民選的結果是總理亞努科維奇以49.53%的優勢勝出。眼看辛苦操盤的計劃就要落敗,CIA開始在烏克蘭全境散播謠言,說亞努科維奇有著很嚴重的腐敗問題,在這次大選中存在舞弊現象,甚至有亞努科維奇打算將烏克拉重新併入俄羅斯的謠言。
CIA利用媒體技術和宗教人士在烏克蘭境內發動一場涵蓋各年齡層面的“革命運動”,其實用“民主”的噱頭最容易蠱惑的就是青年學生。
沒過多久時間,烏克蘭上下便一片群情激憤。警民之間的衝突事件也越來越多,不得已之下最高法只能宣佈大選無效,重新進行選舉。這次的結果,終於遂了尤先科和CIA的願,尤先科以52%的得票率成功當選。
自己成功坐上總統之位後,終於徹底倒向親美、親歐一方,國內的民族衝突愈演愈烈,越來越多的示威遊行湧上街頭。這還不是最糟糕的事情,最重要、最基本的是民生問題。
烏克蘭從歐洲糧倉淪為歐洲“子宮”
烏克蘭作為蘇聯第二大加盟共和國,不僅自然資源極為豐富,在農業方面,更像是老天爺賞口飯吃一樣。
我們知道烏克蘭之所以被譽為歐洲糧倉,那是因為他坐擁著遼闊的黑土地,卻很少有人知道黑土地意味著什麼?
黑土地是地球上珍貴的土壤資源,是全球公認的最肥沃、最適宜耕作的土壤,是糧食等重要農產品的生產基地。黑土地是土壤生物重要的載體,每1克土壤中含有數百萬到數億級的細菌、真菌等。在我國,黑土地也被譽為是“耕地中的大熊貓”,東北地區尤其是黑龍江省的黑土區耕地面積更是遼闊,達到2.78億畝。
蘇聯時期,烏克蘭地區的農業產值幾乎佔到整個蘇聯的四分之一,其中甜菜和向日葵的產量佔到一半之上。
在繼承蘇聯遺產的時候,烏克蘭可是一點也不少分。在軍工方面更是繼承了安東諾夫設計局、馬達西奇公司、黑海造船廠、南方機械製造廠等等。同時還擁有了1700多枚核彈頭,一度成為僅次於美俄的擁核大國。
再加上烏克蘭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氣候適宜、沿海港口居多、地處俄歐之間等等,一時間,所有人都認為烏克蘭前途必定是光明的,而美國也將自己貪婪的目光投向了烏克蘭。
在一頓忽悠之下,烏克蘭先是自廢武功,將核武器和圖-160轟炸機全部拆除。緊接著尤先科政府又將國有資本大量對西方資本敞開,另一方面為穩固自己的政權,不斷給民眾提升各項福利制度。
這種拿國家氣運賭自己命運前途的事,在近代史中屢見不鮮,一來二去幾番折騰之下,烏克蘭工業、商貿體系這折騰得奄奄一息,只能成為一個原材料和農產品的出口國。
國內經濟搞成這樣,民眾的生活自然也不好過,以至於衍生出色情和代孕這麼一個行業。
2019年,一項調查顯示在15歲-49歲的成年人中每100個人當中就有1名艾滋病患者。造成這樣恐怖資料的原因無外乎兩點,一個是濫用毒品針頭注射時導致感染,另一個就是“發達”的色情產業。
無論是尤先科也好,還是後來的波羅申科,澤連斯基之流,他們對於烏克蘭猖獗的地下色情產業從未真正下過決心治理,或許他們心中清楚,在當前的經濟背景下,烏克蘭女性並沒有太多的選擇。
如果不願意去做這種皮肉生意,還有一條出路,那就是代孕。
我們知道西方國家雖然對這項產業持較為開放的態度,但歐美女性開出的標價高到嚇人,而烏克蘭完全是以低價打入這個全球市場。給一些有代孕想法的中產家庭提供了便利,但同時也傷害了烏克蘭女性的身體健康。
長此以往,烏克蘭就被人們調笑成“歐洲子宮”。
由此可見,烏克蘭當初徹底倒向“親美”、“親歐”,完全是少數人出賣多數人的利益。
顏色革命為何在中國絕緣?
前蘇聯加盟國和中東國家屢屢發生顏色革命,而在中國卻未曾掀起過波浪呢?我個人分析,無非有以下三點原因。
第一點原因,中國經濟快速騰飛,顏色革命失去了根本的動力源泉。
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中國經濟的提升讓全世界都為之矚目,這一突出的成就取得是任何人都無法忽略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一片欣欣向榮的大好前景下,顏色革命便喪失了原先的理論依據。
第二點,文化歷史因素,中國人民對西方國家“不軌之心”有著警惕心理。
從1840年開始的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屈辱的血淚史,在革命的道路上不斷摸索,終於在1949年走上了一條光明的道路。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人民會忘記這段歷史,忘記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欺凌。
同時,中國人沉浸在儒家文化中數千年,仁義禮智信的精神早已根植于思想土地之中。西方所謂的“真善美”普世價值觀,更多的則是徒有其表。
第三點,顏色革命內部已經分崩離析。
從過去幾十年的對壘經驗中,美國的顏色革命儼然外強中乾,成為一套披著虛假外衣的理論體系。顏色革命的核心思想,無非是西方所捏造出的“民主”、“自由”,可看看美國這幾年的表現,又何來“民主”二字可談。尤其是國會山被衝撞之後,他們自己所制定下的根基制度就這樣歸於湮滅了。
現在反而有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開始研究起中國製度,這對於美國政客來說並非是個好訊息。
結語
顏色革命也好,和平演變也罷。從歷史的維度來看,它對於美國構建霸權主義制度起到了關鍵作用。特別是在經濟尚不發達,民眾對本國的文化制度不夠自信的地方,更容易給美國提供可趁之機。
從烏克蘭現在的下場就能看出,顏色革命給一個國家帶來的絕不是光明的前途,而是無盡的深淵。因此有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抵制美國顏色革命的入侵,中東、南美、非洲紛紛掀起一片浪潮。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不得不採取雙管齊下的辦法,即顏色革命和軍事壓迫的雙重壓力。
對此我們應該有個清楚的認知,不僅要對國內所謂的“公知”要及時清理,更要注意周邊國家是否會有顏色革命的苗頭。
顏色革命隨時有捲土重來的浪潮,各國不得不對此嚴加防範,在避免輿論扭曲的同時,更要加強對自身文化、制度的自信。
世界上一個整體,並非只有一種價值觀、一種規則、一個有關於“民主”的定義解釋。話語權也屬於全世界人民,而並非是美國政客和媒體的獨家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