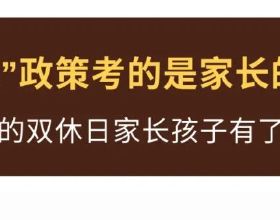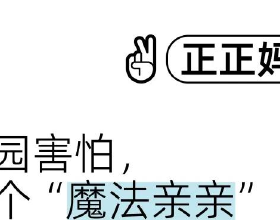「世界上只有一種病,那就是窮病」,這句出自電影《我不是藥神》中的臺詞似乎也在印證小花梅(豐縣楊某俠)曾經歷的苦難。
好在這一切在她的家鄉已成為過去。村裡唯一的痕跡,就是 1996 年前小花梅曾住過的繼父家的三間木屋,但現今木屋沒有了,剩下石頭壘砌的地基被荒草掩蓋,站在地基上可以看到村裡幾排嶄新的樓房和村裡主街上的車來車往。
現在福貢縣亞谷村像小花梅這樣的女孩都必須強制接受 9 年義務制教育。騙婚、甚至將她們拐賣到外地的事情在當地已經絕跡。一些早年遠嫁外地的傈僳族、怒族等女子近年來開始紛紛返家,一些人甚至回來後就再也不回東部的婆婆家。
不過這對於遠離家鄉 2700 公里外的小花梅來說已經不太可能。目前她的生母、繼父均已離世。唯一在世的親人是一個同母異父的妹妹,也遠嫁外地,村裡沒有她的近親屬。而像小花梅這樣早年間因拐賣而飽受心理折磨,乃至精神失常的女性該如何救助?仍是一個亟待破解的社會難題。
「偶爾治癒」在瞭解更多事實的同時,也邀請到一位醫學人類學學者,一起探討精神障礙女性普遍面臨的困境,對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的「解鎖」以及救助支援途徑。
「我們需要思考的是,精神病院,是否能成為一個人的最終去處?」
亞谷村老鄰居一眼認出小花梅
來自福貢縣的多個信源告訴「偶爾治癒」,小花梅生於 1977 年。
影片載入中...
小花梅就是小花梅,這是一個在怒江多民族聚居區正常的名字,當地很多人名字都是根據民族語言音譯過來的,不是常見的「姓+名」結構。曾有網友質疑這個「不嚴肅」名字,追問他沒有姓嗎,其實當地一些民族確實沒有姓只有名。
據亞谷村多位村民回憶,小花梅和媽媽都是怒族,而亞谷村以傈僳族村民為主。母女之前生活在福貢縣匹河怒族鄉,那裡也是全國唯一的怒族鄉。根據國家民委 2010 年的資料,我國的怒族只有 37500 多人。
對小花梅來說,人生第一個災難是他的生父在上世紀 80 年代初意外去世,這改變了她和母親的命運,貧窮的媽媽帶著小花梅,沿怒江大峽谷北上 14 公里,改嫁給亞谷村的恆某某。
亞谷村民木女士與小花梅的媽媽很熟,早年因房屋臨近常串門走動。她告訴「偶爾治癒」,當年很多村民都知道,小花梅生父是村裡的退役武幹(當地土話,武裝幹部的含義),因為救落水兒童而不幸去世。關於這一資訊,「偶爾治癒」還將進一步求證查詢。
媽媽普桑瑪改嫁過來的時就叫她小花梅,這就是她的本名。繼父恆某某喜好喝酒,有三間木屋,沒有其他手藝,種田為生。鄰居木女士、桑先生回憶,當時小花梅大概四五歲,微胖,挺活潑,頭髮稀疏。因為離得近,小花梅常跟桑先生的兒子玩。後來小花梅在亞谷小學讀書,但小學沒有唸完。
桑先生看到網上披露的小花梅的照片、影片,一眼就認了出來,他說從眼睛、臉型就認出來了,感覺比原來胖一點,但口音有變化,頭髮也濃密了。
2 月 10 日晚,徐州市的第四份調查通報證實了以上資訊。該通報顯示,經部、省、市公安機關對楊某俠、光某英(小花梅同母異父妹妹)與普某瑪(已去世,小花梅母親)生前遺物進行 DNA 檢驗比對,結果為普某瑪與楊某俠、光某英符合母女關係,結合調查走訪、組織辨認,認定楊某俠即是小花梅。
當年的亞谷村也遠不是現在的規模,30 多年前只有四五戶定居在山腳,其他村民分散居住在半山腰和山頭,在一片片的小塊土地上種玉米等糧食謀生。
而現在,幾十年來村子因擴建、易地搬遷而增加到了 2400 餘村民,村裡商店、飯店、超市等沿街開了數十家,建起了多棟易地搬遷安置樓房,不少村民開店、開公司,也開起了豪車,自建起四五層的樓房。
小花梅的媽媽後來與繼父恆某某生了一個妹妹,也即徐州官方通報裡的光某英。最終確定小花梅身份的也是用同母異父妹妹和去世母親遺物的 DNA 做了檢驗比對,官方再結合調查走訪、組織辨認,認定楊某俠即是小花梅。
村裡鄰居說,小花梅的母親大約三年前去世,繼父恆某某去世時間更早。在恆某某去世後,小花梅母親又改嫁過兩次,沒有再生育孩子。她改嫁後搬到山下更低處房屋居住,小花梅曾住過的那三間木屋就廢棄了,後來倒塌、拆掉,只剩荒草淹沒的地基。
精神異常始於失敗的第一段婚姻
在學者陳業強與福貢縣婦聯領導的訪談記錄中曾提到,「20 世紀 80 年代初,福貢的婦女最初遠嫁到保山。當時保山那邊的彩禮比福貢的高,保山那邊家庭條件不好的男性就來福貢討媳婦」。
多位鄰居記得小花梅小時候挺活潑,精神和智力沒有發現問題,變化出現在第一次失敗的婚姻後。
幾位老鄰居都不清楚是誰把小花梅介紹嫁到了亞谷村南 200 多公里的保山市,但在上世紀 90 年代,怒江大峽谷內道路狀況較差,亞谷村人至少要花一整天才出得了怒江大峽谷,出了大峽谷第一個成規模的城市就是保山市,繁華的城市對深山裡的年輕女孩無疑有著很強吸引力。
徐州官方在之前通報中提到,小花梅的親屬和同村村民回憶,小花梅 1994 年嫁至雲南省保山市,1996 年離婚後回到亞谷村,當時已表現出言語行為異常。
與此印證的是,早年住的跟小花梅一家最近的亞谷村民桑先生回憶,小花梅從保山回來後精神有些異常,比如拆洗被單,她連被子裡的棉花都一起洗了,也聽到過小花梅在屋裡有大哭等聲音。另一位鄰居也聽說過小花梅從保山回來後「精神不太正常」,但平時沒看到過激烈的言行異常。
在「豐縣生育八孩女子」事件引發網友關注時,今年 1 月 28 日豐縣釋出的通報說,家人和鄰居反映,楊某俠(即小花梅)經常無故毆打孩子和老人。經醫療機構診斷,其患有精神疾病,目前,已對其進行救治。
在央視新聞報道的畫面中,小花梅被醫院收治,其病床床頭牌上寫「偏執型精神分裂症」,入院日期是 2022 年 1 月 29 日。
對於小花梅的精神分裂症治療情況,2 月 7 日徐州釋出通報說,聯合調查組組織市縣兩級醫療專家對其精神分裂症進行會診,並實施綜合治療,目前其精神狀況趨於穩定。入院檢查結果表明:她牙齒脫落因重症牙周病所致,其他健康指標正常。經 DNA 鑑定八個孩子是小花梅和董某民所生。
據 2 月 10 日最新的通報,涉嫌非法拘禁罪的董某民,涉嫌拐賣婦女罪的桑某妞、時某忠夫妻已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有研究顯示,人口拐賣與精神障礙的關係不容忽視。一方面,精神障礙患者更有可能成為人口拐賣的受害者;另一方面,拐賣經歷也可能會導致精神健康問題的出現。而目前披露的小花梅經歷,對這兩方面都有所印證。
2019 年,發表於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的《我國拐賣婦女犯罪特點及治理策略——基於 1038 份裁判文書的分析》一文指出,他們對 1038 起拐賣女性犯罪案件的裁判文書進行分析,結果發現:超過 1/4 的被拐賣女性患有精神障礙,如精神發育遲滯、精神分裂症、抑鬱症、癲癇等。
另一份基於對 2006-2012 年間南倫敦地區精神衛生服務所碰到的拐賣受害者特徵分析的結果顯示:精神衛生服務所碰到的絕大多數拐賣受害者為女性,她們最常見的精神健康問題是應激相關障礙和心境障礙,其次為精神分裂症,有過拐賣經歷的精神衛生服務使用者更有可能需要接受住院治療。同時,該研究還發現,7% 的拐賣受害者在被拐賣前存在精神障礙。
「我女兒不見了、找不到了」
福貢縣婦聯領導曾對陳業強說「福貢婦女被拐賣的高峰期是在 1993——2000 年期間。當時,福貢這邊比較困難,所以有些外出務工的人就把這裡的婦女帶出去賣掉。被賣的女性中未成年人比較多,有的讀到小學或初中沒畢業就被賣掉了。被賣到外地的婦女,家庭條件好的,老公對她們也好的,就留在了外地,有的還經常跟家裡聯絡;有的被拐賣出去後就杳無音信、生死不明瞭。」
在早前的官方通報中,小花梅親屬透露,當時已嫁至江蘇省東海縣的同村女子桑某某將小花梅帶至江蘇治病。桑某某對警方說,當年她是受小花梅母親所託,帶小花梅到江蘇治病並找個好人家嫁了,兩人從雲南省昆明市乘火車到達江蘇省東海縣後小花梅走失,當時未報警,也未告知小花梅家人。
鄰居桑先生告訴「偶爾治癒」,對於小花梅是如何被人帶到了江蘇的,他並不知道,但那之後的幾年小花梅的母親經常哭訴「我女兒不見了、找不到了」,她不知道女兒去了哪裡。
小花梅失蹤四五年後,母親普桑瑪收到一封江蘇寄過來的信,信裡內容桑先生沒有看到過,但她母親說女兒在江蘇,她這才知道小花梅下落。
據鄰居們回憶,雖然知道了女兒下落,但母親普桑瑪和繼父恆某某沒能力去找女兒,因為他們沒有錢,身體又有病,「他們兩個都愛喝酒,天天喝,身體喝垮了。」桑先生說,他們為這個事很苦悶,但也沒路費找回女兒,那個時候電話、網路都沒有普及,母親普桑瑪也講不了普通話,讓她去幾千公里外找女兒是不可想象的困難。
王江華曾在滇西北生活支教 3 年多,此後也每年都會回去看看。他對怒江瀾滄江峽谷兩邊的風土民情十分熟悉,在他看來,棲息生活在滇西北大山上的很多百姓,由於常年生活高寒的大山裡,即便是夏季早晚氣溫也很低,外加體力勞動繁重,當地居民有早點酒和晚圍爐的飲酒習慣。「當地早年喝的是自家釀的包穀酒和蕎麥酒,由於工藝不好,對身體的傷害很大,常聽說一些常年飲酒的老人在地裡幹著幹著活就猝死了」。
在一份發表於 1989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雲南省的 25 個少數民族,除回族外,酒濫用的情況都比較嚴重 。1988 年,在怒江州六庫的傈僳族社群,慢性酒中毒患病率為 29.08‰。
雲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一篇題為《社會醫學視角下的傈僳族嗜酒行為分析——以雲南 A 村為例》的論文中稱,傈僳族多居住在高寒山區、邊境地區和貧困地區,這些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相對比較滯後,普遍缺醫少藥,他們求醫不便,至今仍然保持著「神藥」兩治的傳統習俗,飲酒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療病療傷、解乏禦寒的作用,這是驅使人們飲酒的客觀條件;另一方面由於酒精的易成癮特性,飲酒人員也有可能演變為嗜酒者。
王江華告訴「偶爾治癒」,他在當地支教走訪時知道很多當地人的飲酒已到了嗜酒的程度,而且不分男女。尤其是一些不能與外界建立資訊連線的高山居民,飲酒成為了他們生活的日常行為,常年情緒低迷、陰鬱是他們普遍表現出來的問題。
21 年前舊案可見拐賣人口之瘋狂
就像徐州官方通報的情況那樣,同村當時已嫁至江蘇省東海縣的的桑某妞將小花梅帶至江蘇,小花梅經歷了童年和婚姻的苦難,又經歷了此後 26 年的悽苦命運。
其實早年拐賣怒江婦女的人也是本地人、本村人,只有最熟悉的人有可能拐走語言不通、對外界充滿嚮往的本地女子。
透過早年的一則打拐新聞,也可反應出當時福貢當地拐賣婦女的瘋狂,根據新華網 2001 年 8 月的報道,雲南省怒江州警方搗毀一拐賣婦女團伙,抓獲犯罪嫌疑人 3 名,解救被拐賣婦女 2 名。
當年 5 月 12 日亞谷村支部書記報警,稱該村一個 12 歲的小姑娘和一個剛結婚不久的少婦於 5 月 11 日到子裡甲趕街一直未歸,四處尋找不見音信,可能是被人販子拐賣走了。5 月 16 日警方獲得線索,得知有一拐賣婦女團伙欲將兩名婦女拐賣到省外,正轉交到雲南保山地區。
警方解救了受害人桑某、都某,不久抓獲犯罪嫌疑人娜某言、娜某加、車某香。三人準備將桑、都以 18000 的價格販賣到浙江省「嫁」給大齡光棍兒。而娜某言的丈夫木某言、女兒和娜某加的丈夫阿某先後因拐賣婦女已判重刑,車某香的妻子於 1997 年被人販子拐賣到了浙江省。車某香本身就是受害者,而他也參與了販賣人口。
2 月 10 日下午,「偶爾治癒」在南安建村找到了此案中的娜某言,她出獄後在村子公路邊開過小賣部,賣飲料和米線等食品,後因修公路拆掉了她的房子,現在她借住在其他村民的兩間不到 20 平方米的小木屋裡,房子很簡陋,由很薄的木板和三角鐵搭建,平時她給放學回來的孫子做飯,她說目前沒有收入,實際上已 63 歲,但因身份證的日期不準,按身份證今年才 59 歲,她領不到每月 60 歲以上老年人才有的補助。她說拆了房子後,自己沒有地方住,也沒有錢再蓋新房。
娜某言說,以前村裡外嫁的很多,那時因為窮,女孩也願意被介紹到外地,但現在生活條件好了,沒人願意再嫁到外地。而且孩子也少了,早年間一般家裡生四五個孩子,生七八個的也有,而且十四五歲就結婚,家裡孩子多,生活困難,不少父母也願意早點把女兒嫁出去。
但對 20 多年前自己犯過的案子,她幾次說「不清楚、記不得」,拒絕說起過往。
該村村委會成員劉女士告訴「偶爾治癒」,村裡知道她曾因拐賣人口的案子坐過牢,但具體刑期是幾年不清楚,她出獄後檔案在派出所裡。
娜某言的房子拆了以後,按國家政策都根據統一標準進行了補償,至於她說沒錢蓋房、無法安置那是自己的原因,補償的錢可能給了兒子,也可能花了,那就是她自己的問題了。
經濟變好,外嫁女回家就不走了
習慣上把靠近緬甸的貢山縣、福貢縣、瀘水縣稱之為「邊三縣」。
1998 年,福貢縣的人均 GDP 1376 元,而當時雲南全省的平均水平是 4355 元;農民人均收入是 685 元,而全省人均收入是 1387 元。最近一次的統計資料顯示,2020 年,福貢縣城鎮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209 元,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557 元,比上年同期增長 8.9%。
相距亞谷村不遠的南安建村,海拔有 1700 多米,現在可以開車盤山直接進入村中。沿路是村民新建的三四層樓房,大多村民電視冰箱洗衣機等電器齊全,不少家門口停著私家車。

亞谷新建的籃球場,圖中的黃色高樓為搬遷安置樓 圖源:李華良 攝
南安建村委會成員介紹,近些年嫁到東部的女子不斷在迴流,她們以探親名義,有的帶著孩子回來,有的孩子留在了外地,也曾有東部省份婆家的人來村裡尋妻,但這些回來的女子說「在你們家裡不被尊重,沒尊嚴,所以不回去了。」來尋妻的人也沒辦法,因為早年很多人沒有領取結婚證,即使領了證的,外地遠道來的人也不敢強迫村裡女子回去。
根據學者陳業強 2015 年出版的《怒江傈僳族婦女跨省婚姻遷移研究》,他多次做田野調查的村莊,總人口 2100 多人,嫁到外地的女性就有 100 多人,而福貢縣公安局記錄,福貢縣從 1988 年到 2009 年,共有 4005 名婦女外流,被拐賣外流的有 1750 人。
小花梅就是這 4000 多名女子其中之一。
遠嫁外地不能保證獲得幸福生活,尤其是,很多女子是被欺騙、拐賣到了外地。
根據陳業強的調查,來怒江討媳婦的男性往往採取欺騙的手段,有的怒江傈僳族婦女由於對外面的世界存在著美好的幻想,以為嫁到東部就會過上幸福的生活。當嫁過去後,才發現現實與想象的差距很大,她們的丈夫一般是在本地找不到妻子的「剩男」,要麼是家庭條件差,要麼是身體有殘疾,要麼是犯過錯誤、口碑不好的男人。
近些年,情況有了巨大變化。很多嫁到外地的傈僳族、怒族等女子返家後再也不回東部婆家,她們發現家鄉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怒江大峽谷的路通了、旅遊景區和農家樂遍地開花、村民普遍建起了三四層的樓房、高山上的貧困村民易地搬遷免費分了樓房,村民自建房政府還有補貼。
2020 年 1 月瀘水、福貢、貢山三縣市交通扶貧的重點建設專案怒江美麗公路的通車,駕車數個小時就可以穿行怒江大峽谷。
而據新華社 2021 年報道,怒江州 98% 以上土地為高山峽谷,貧困發生率曾高達 56%,是全國最高的州市之一,可謂「極貧之地」。但怒江州消除了貧困,26.96 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全部脫貧,4 個深度貧困縣全部摘帽,傈僳族、獨龍族、怒族和普米族整族脫貧。
路通了,大量遊客和物流通暢帶來的就是收入快速增長,亞谷村有多處村民正在新建樓房,村民說一般建樓房要 20 多萬,甚至三四十萬元,大部分資金來自近年打工、開店、跑運輸等賺到的錢。
救出了小花梅,然後呢?
馬志瑩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工作學院的一位醫學人類學家,自 2008 年開始,她開始以人類學視角研究中國的精神衛生體系,走訪多家精神衛生機構,採訪過《精神衛生法》的立法者、公益律師、基層精神衛生工作者、患者和家屬。
在過往的調研中,馬志瑩注意到精神障礙患者面臨的困境,在她的經驗裡,「精神障礙與性別、貧富,三者關係互有交叉」。
被拐賣的農村精神障礙者
「在城市或者一些經濟條件較好的地方,女性精神障礙者往往被看作是一個『危險的母體』,因為被認為會有遺傳的風險,從而在『婚姻市場』中受排擠。但奇怪的是,在男性精神障礙者身上大家好像就會忘記這件事。」
根據研究,父母中的一方患精神分裂症,其子女患精神分裂症的機率大概是 4% ~ 14%,約是一般人群的十幾倍。
「父母一方」並沒有任何性別上的指代,但由於女性生理的功能,因此在「優生學」的話語中,女性被認為需要為後代生理意義上的正常和質量負責。
也因此,「女性精神障礙者往往被認為不適合當母親,即使她們生下孩子,在家庭中也處處被排擠,人們認為,她是沒辦法教孩子的。」
但在農村,一些欠發達、女性比例較低的地區,可能就會出現不一樣的景象,比如此次事件中的豐縣。
「人們會只關注這個女性是否能生育。甚至家庭都會視她作負擔,急切希望推她出去。一些研究者也發現,農村的精神障礙者很容易進入婚姻,而這個容易,往往不是自己的意願,而是透過拐賣或者強迫來進行的。」
2017 年的一份研究對 770 位被拐賣婦女進行分析,其中,法院根據精神疾病司法鑑定書等相關證據認定的患有精神疾病的女性有 202 位,佔被拐賣婦女總量的 26.2%。其中主要以被陌生路人「順手牽羊式」和被熟人嫌棄後出賣,同時,也存在被「接力式」轉賣和「退轉式」轉賣。
「解鎖」嚴重精神障礙患者
在豐縣女子事件中,根據目前披露出的資訊,首先引起馬志瑩關注的是,「即使這個女性現在是一個精神障礙者,對她的『關鎖』,也並不應該被視作理所當然」。
根據早期影片和豐縣調查組第一份通報,豐縣女子的丈夫董某民的解釋為,因為妻子病情加重,發病期間經常摔打東西,毆打老人和孩子,因此,董某民會用鐵鏈進行約束。
《2018 年全國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管理治療現狀分析》顯示,截至 2018 年底,我國在冊患者 599 萬例,其中在管患者 568 萬例。病情穩定患者 442 萬例,病情穩定率 80%。
在 2004 年之前,很多精神障礙患者大多遊蕩於社會邊緣,或被家人用鐵鏈、鐵籠鎖在一隅。但這不僅使患者獲得醫學治療的權利受損,導致病情延誤甚至遭受明顯的軀體損害,也無法從根本上減輕家庭照料負擔。
十多年前的媒體報道曾稱,僅河北一省,被鎖者約 10 萬。
2004 年,中國借鑑澳大利亞的模式,推出「中央補助地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療專案」,因為首年獲批 686 萬元經費,人們也將其簡稱為「686 專案」。
該專案打通醫院和社群,提高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療率,降低肇事肇禍率 ,其中實施很重要的一項措施便是「解鎖」。
而「解鎖」並非簡單的開啟鎖鏈,需要一整套配套措施和流程,需要由包括精神科醫生和護士在內的專業團隊在關鎖現場對患者實施解鎖,將患者接到指定的精神專科醫院進行診斷和住院治療(系統藥物治療,同時配合心理治療、工娛治療或改良電休克治療等綜合治療手段),患者病情好轉或穩定後出院,回到社群繼續接受隨訪、服藥、康復和健康教育等一系列干預措施。
「解鎖」推行多年,為什麼還是會有上鎖行為出現?
「其實這個問題不僅僅是政府要不要給患者解鎖的問題,而是大眾和社群如何接納或者跟精神障礙患者相處。我們不能把這些患者當做潛在的風險存在。」
此外,馬志瑩說,在「機構-家庭」的二元模式下,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如果除了家庭和醫院,精神障礙患者還能去哪裡?
她曾在走訪中遇到許多「關鎖」個案,有的是因為當地精神病院的床位有限,所以患者被鎖在家裡。也有一位父親,考慮到自己的兒子已經進出十幾次醫院,因為在醫院被其他病人打過,兒子非常不喜歡那個環境,這位父親說,「寧可直接鎖在房間裡,不讓他出來,也比去醫院捱打好。」
「在整個精神服務系統裡,應該有家庭之外的社群居住的選項。比如『中途宿舍』,一些嚴重的精神障礙患者從精神病院出來之後,可以去這裡過渡。對於獨立居住的精神障礙患者,也可以有社群護士或社工定期隨訪。」
「偶爾治癒」透過資料查詢,發現在江蘇徐州豐縣也有為嚴重精神障礙患者免費提供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其中需要家庭提交資訊材料,之後進行隨訪。其政府網也提及,在 2020 年,豐縣政府進行摸底,對轄區內 3852 名持證精神障礙患者進行核查,併為 1737 名困難精神殘疾人提供服藥救助。
但在豐縣女子事件中,相關資訊並未被充分披露出來。
精神病院難道就是她的終點嗎?
在第四份通報中,徐州調查組稱,董某民涉嫌非法拘禁罪。有公益律師稱,「如果豐縣女子確有精神疾病,這可能是首次關鎖精障者被刑事檢控」。
對此,馬志瑩稱,「這確實是一個進步」。因為在其中,會涉及一個問題,公眾在談論精神障礙者,尤其是嚴重的精神障礙者時,會普遍認為,因為患有精神疾病,就沒有同意能力。
「如果有關部門認為這涉嫌非法拘禁,尤其在承認她有精神障礙的情況下,某種程度認為,在這個事件中,他們承認這位患者是有表達自己意願的能力,她對自己的處境是有自主選擇權。」
但馬志瑩強調,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只改其中一部分,因為可能會帶來未預效應。如果只強調「關鎖」的非法,而不給精神障礙患者及其家庭提供支援,那麼一些家庭會擔心涉嫌犯罪處於兩難境地,「可能偷偷把人送走,也可能把患者遺棄」。
「我們需要給家庭照料者更多支援和關注」。
在豐縣女子的問題上,我們還面臨的一個問題是,把人救出來之後,怎麼辦?
馬志瑩丟擲一個問題,「精神病院難道就是她的終點嗎?」
她援引國內外的救助案例,「首先解決的是住的問題」。
「要解決他們的處境,首先是要從物質條件開始著手,因為無家可歸的狀態就會導致精神壓力。因此,這在許多救助專案中,住處是很重要的一項」。
馬志瑩舉例,在美國,能夠獨立生活的精神障礙患者是有租金補貼的。無法獨立生活的,也有中途宿舍、集體之家。另外,對於遭受虐待和暴力風險的女性,也可以自行或者帶著孩子到庇護所藏身。而在中國,廣州和深圳也在開始嘗試中途宿舍,但「規模還是很小」。
此外,還有經濟來源的問題。對於豐縣女子來說,脫離現在這個環境之後,她需要依靠什麼才能生活下去?
「在國內外,也有一些嘗試去解決精神障礙者的就業問題,指導患者做一些就業技巧的訓練。在農村,可能會有一些農業生產互助小組」,馬志瑩說。同時,由於精神衛生資源匱乏,對於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的治療,更多被壓縮成「藥物治療」。但馬志瑩指出,從生物、心理、社會全方位角度去理解一個人的話,「藥物治療只是其中一方面」。
因此,我們需要考慮如何去給這些精神障礙患者提供社會支援網路,進行心理創傷治療。
「過去很多拐賣事件中,有人會提問,說你把人救出來又怎樣呢?回答者說,兒童有福利院,精神病人有精神病院。但我們應該去思考,精神病院是否就能成為一個人的最終去處?」
(師捷、蘇子涵、張璐瑤對此文亦有貢獻。)
撰文:李華良 蘇惟楚
監製:李晨
首圖來源:李華良 攝
參考文獻
1.高燕.西部地區貧困與經濟可持續發展[J].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01):36-41.
2.福貢縣統計局 《2020年福貢縣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徵求意見稿)》.
3.李建華,朱華,萬文鵬.雲南省幾個不同民族社群酒濫用狀況調查[J].中國神經精神疾病雜誌,1991(01):39-40.
4.李申昇.社會醫學視角下的傈僳族嗜酒行為分析[D].雲南大學,2011.
5.溫丙存. 被拐賣婦女的型別分析[J]. 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44(4):54-58.
6.陳業強.怒江傈僳族婦女跨省婚姻遷移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7.張萬洪.殘障權利研究(2014)[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8.黃忠良,翁文國,翟彬旭.我國拐賣婦女犯罪特點及治理策略——基於1038份裁判文書的分析[J].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33(05):19-27.
9.王勳,馬寧,吳霞民,張五芳,管麗麗,馬弘,於欣,陸林.2018年全國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管理治療現狀分析[J].中華精神科雜誌,2020,53(05):438-445.
— Tips —
如果您有與醫療健康相關的線索
或與疾病、衰老、死亡有關經歷
歡迎投稿給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