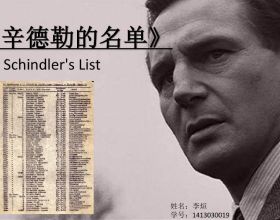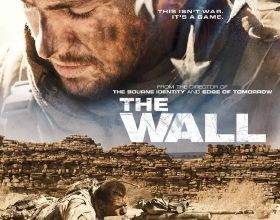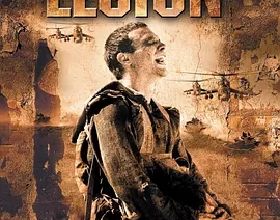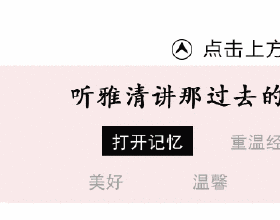苗子秋走出樓門,走進淅瀝瀝的秋雨中,又習慣性地回望一眼六樓的視窗,一股悲涼便伴著冰涼的秋雨落進心田。
自從他把娘接進城後,那個視窗就多了一尊雕像。
娘患白內障,眼睛幾近失明,聽力也差了,卻能準確分辨他的腳步,每次開門離家,娘都會不動聲色地站在他身後,日復一日地重複道:“秋兒,在外面少喝酒,沒事早點回家呀——”
起初,他總嫌娘囉唆:“娘,瞧您,孫子都上大學了,還拿我當小孩子不是?”他話音裡透著不耐煩,娘卻不惱:“唉,你就是長到七老八十,在俺眼裡,也是那個長不大的秋娃兒。”
他每次下樓,只管徑直往前走,從沒回頭張望過。娘卻痴痴地站在視窗。
小時候,他愛讓娘帶著放風箏。望著空中的風箏一會兒驟然騰起,一會兒又滑翔而下,一會兒打著旋子,一會兒舒緩徐行,飛高飛低,總離不開手中那條線。他不解地問娘:“為啥要用線牽著風箏,咋不把它放開呢?”娘笑著說:“俺的傻娃兒,風箏沒有線牽著,就會從天上掉下來,就找不到娘了。”
上學後,他每天步行幾里路去學校。放學途中,頑皮的同學約他下塘游泳,或上樹掏鳥窩,只要他動念頭,娘就如有神助站他眼跟前,他為這沒少跟娘賭氣。
那年冬天放學後,他趁娘不在家,結伴去村邊池塘滑冰,不小心掉進冰窟窿,幸被好心人救起。當夜高燒的迷迷糊糊,覺得自己變成一隻風箏,一會兒騰雲駕霧在空中盤旋,一會兒又忽地滑向谷底,他驚叫著找娘。娘邊用白酒擦他滾燙的身體,邊心疼得落淚,安慰道:“乖娃兒,別怕,有娘哩!”
年復一年,伴隨著孃的嘮叨,他漸漸長大了。
到省城上大學的頭天晚上,娘為他整理行李,穿得用的,樁樁件件,交代幾遍。沉浸在憧憬中的他,一句話也沒聽進去。
他提行李出門,娘跟在身後,邊走邊囑咐。走出衚衕,他勸娘回,娘白他一眼;走進車站,他又勸娘回,娘沒有挪步。直跟到上車了,還在車下交代:“秋兒,娘說的話,記住啊——”他怕人笑話,趕緊扭過頭去。
等車啟動了,他扭頭一看,娘還站在那裡,用袖子擦著眼淚。他不解地搖著頭。
後來,他參加工作;再後來,他在城裡安家。為便於和他聯絡,娘學會了使用手機。他每次回鄉或返程途中,娘總要一遍遍打電話問:“秋兒,你幾點能到家啊?”“秋兒,這會到哪裡了?坐車可別瞌睡。”……聽著娘不厭其煩地嘮叨,他無奈地苦笑著一次次關機。
多年過去,孃的身體越來越差,小腦萎縮,聽力下降,眼神、記性也不好了。可娘放在床頭的那隻葫蘆,卻畫滿了粗粗細細的道道。娘說,粗的是記著他回來的次數,細的是記著在家住的天數。娘想他了,就去摸那隻葫蘆上的道道,原本是黃色的葫蘆,已被娘母摩挲得變成深棕色。
那年的一場大病,孃的腿腳不靈便了,生活難以自理。在他再三苦求下,娘答應隨她來城裡住。
孃兒倆見面機會多了,娘也像孩子一樣愛黏他。每次離家時,娘總要在他身後接二連三地問:“秋兒,你去哪?”“秋兒,你做啥哩?”“秋兒,你啥時回來?”
……
他不由得頓生煩悶,沒好氣地懟道:“娘,你天天這樣問,煩不煩啊?”娘惶惶看他一眼,不知所措地低下頭去。
為避開孃的囉嗦,再上班他總是開門就走,不給娘說話的機會,他覺得輕鬆了許多。
那天也是無意,他走出樓道後,突然感覺臉上一陣清涼,天下雨了。他仰起頭朝上望的一瞬間,竟然發現娘站在六樓自家視窗,一動不動朝下望。他鼻子一酸,眼眶溼潤了。他想,等忙過那一段時間後就休年假,好帶著娘看景緻。娘來城裡半年了,還沒有走出過小區。
可惜,他依然很忙,轉過身就忘記自己的打算。而娘沒有忘記他,早上在視窗送他,傍晚在視窗等著他。前年冬天下頭場雪那天,娘見他出門忘帶圍脖,拿起圍脖去追他。腿腳不利索的娘,一下子摔倒在樓道里,再沒醒來。
娘去世後,他感覺心被掏空了一樣。打那起,他養成一個習慣——走出樓門,總要回望六樓的視窗。可視窗是空的,再也不見孃的身影。
那時,他感覺自己像只斷了線的風箏,孤獨地在空中飄飄悠悠……(薛培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