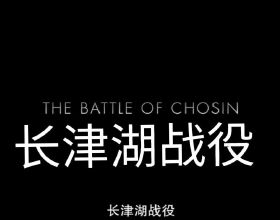一個社會的任何族群,都無權為了自己在某方面的絕對安全,讓另一個族群處於絕對風險中。
1
1991年,美國曾經發生過一起震動一時的“肯尼迪強姦案”。
案件的被告威廉·肯尼迪,是美國前總統約翰·肯尼迪的侄子,聲名顯赫的肯尼迪家族的孫輩。時年僅僅31歲,其未來被家族寄予厚望。
這年三月,威廉和他的幾個朋友在佛羅里達泡酒吧,期間結識了一位名叫帕特西亞·鮑曼的姑娘。兩人相談甚歡,隨後一起離開酒吧,前往肯尼迪的別墅。
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變的撲朔迷離,據威廉的描述,兩人隨後一起散步,聊著聊著,就情不自禁,在海灘上露天席地發生了關係。
但帕特西亞姑娘說的卻是完全另一個版本:肯尼迪一回到豪宅後,就兇相畢露,對她欲行不軌,姑娘雖然奮力掙扎、但最後還是被這小子捉住,被按在草地上遭到了長達一刻鐘的強暴。
這個事情發生後,立刻在全美炸了鍋,警方在帕特西亞下體中確實提取到了肯尼迪的精液,證明兩個人的確發生過關係。但關係究竟是自願還是強迫或半強迫發生的呢?孤男寡女,夜深人靜,這種事沒辦法說得清。
事實的迷霧當中,更多的人還是本能的同情弱者,認為姑娘不會冒著自己名譽受損的危險平白無故的誣告肯尼迪,何況肯尼迪家族那是什麼身份?一家都是非富即貴。而且威廉他舅舅總統約翰·肯尼迪當年就有風流之名,威廉自己過去也很風流。兩相對比,公眾當然更願意相信帕特西亞的描述。
於是威廉被告上了法庭,志在必得的檢方收集了大量間接證據要把他送去吃牢飯。而陪審團與普遍公議一樣,是同情女方的。
危難之中,肯尼迪家族想到了華人神探李昌鈺,花重金請他出山進行調查。
出人意料,簡單調查後,李昌鈺很輕鬆地就破解了這個懸案:
在作為專家證人出庭時,李向陪審團介紹了法國物證技術學家洛卡德在本世紀初提出的“微量物質交換定律”:如果兩個物體接觸過,必定會留下微量物質交換的痕跡。而本案依檢方說法,女方先被威廉撲倒在水泥地上,再壓倒在草地上,她的衣裙和內褲應該相當猛烈地摩擦現場的水泥地面和草地,並且留下明顯的微量物質轉換痕跡。
而後李昌鈺拿出之前自己在泥地和草地上摩擦過的一塊白手帕,給陪審員們傳閱。再將高倍顯微鏡下放大的痕跡照片展開給陪審團,照片顯示這塊手帕上留下明顯的與草地的摩擦痕跡;而接觸過水泥地表面的手帕上,也可以看到灰色的摩擦痕跡,以及部份纖維還有破損的跡象。
接下來,李昌鈺將女方的衣服、內褲及胸罩的高倍放大照片展示給陪審團看,告訴他們,經過徹底的查證,都沒有發現任何破損的纖維及草地的痕跡,這表示女方並沒有在草地上待過,也沒有在水泥地上掙扎過。
檢方聽到李這樣一錘定音,立刻就急了:“李博士,手帕和內褲材質不同,你為什麼要使用手帕,而不使用女性內褲來進行對比呢?”
李昌鈺從容地說出了那句日後被人們稱之為法庭名言的幽默語句:“不好意思啊,我是個正常的男人,沒有隨身攜帶女士們的內褲的習慣。”
原本嚴肅的法庭鬨堂大笑,不久之後陪審團做出裁決,判決威廉·肯尼迪無罪。
這是李昌鈺斷案經歷中頗為有名的一段奇案,但更為耐人尋味的,是此案的後續影響——威廉·肯尼迪雖然成功脫罪,但案件之前的報道,已經讓很多人形成了威廉是強姦犯的印象。即便案件結案後,仍有不少人堅持認為,他跟之前同樣聘請李昌鈺破案的辛普森一樣,是依靠“鈔能力”才逃脫法網。女方帕特西亞此後也一直堅持自己遭遇了強姦,不斷提醒公眾把此人釘在恥辱柱上。
有一種陰謀論認為,肯尼迪家族在美國一直在某個秘密組織所針對。從約翰·肯尼迪遇刺到威廉·肯尼迪被起訴,都是該組織的手筆。而如果這種陰謀論屬實,該組織的目的似乎達到了——威廉雖然脫罪,但他的政治前程卻徹底被毀了,強姦案成為了威廉一個無法洗脫的人生汙點。
這是距今30年前的事情。今天我們回看這起案件,會覺得威廉和帕特西亞究竟到底誰才是該案的受害者,成為了一件永遠無法講清的事情。
但幸運的是,當時的美國主流社會還是認法律的。在法槌落下的那一刻,威廉至少在法律和社會意義上脫罪了,政治前途雖然沒了,但好歹沒有到社會性死亡的程度。
2
可是30年後的一些美國倒黴男性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2018年10月,美國康涅狄格州法院判處了一起看似比“肯尼迪強姦案”簡單地多的案子。
該州聖心大學的女生尼琪全程帶著不屑、輕蔑而厭煩的神情聽完了法院的宣判,法庭以她誹謗他人為由,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緩期兩年執行——以其罪名定性而論,法庭顯然已經從寬處理。但尼琪和庭外她的支持者們顯然對此並不領情。對兩名控告尼琪誹謗的男性的聲討持續了很久。
2017年,美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MeToo運動,尼琪在該運動中指稱在一次校外聚會中遭遇了同校兩名男同學的性侵。警方在調查後,根據痕跡證據,認為該指控毫無事實根據的,但尼琪依然在推特上堅持自己的主張,並得到了MeToo運動者的助力。
輿論被引爆後,被指控的兩名男生隨後一人轉學、一人長期休學。忍無可忍的兩人在不久後將尼琪告上了法庭,其中一位匿名受害者委託法庭宣讀了自己的控訴:“過去的一年是我人生中最困難的時刻,我的大學生活全毀了……她出於自身的想法對我提出的指控,在我看來是那樣的不可理解、不義而又可怕。”
但MeToo運動的支持者們並不這樣認為,比如發起該運動的好萊塢女星艾莉莎·米蘭諾就對判決結果嗤之以鼻,她說“男性社會”不應該“苛求”女性在指控性侵時提供可以在法律上定罪的證據,因為MeToo運動的主旨就是為了鼓勵女性們勇敢的說出自己曾經受到的性侵害——哪怕證據不足。
是的,允許甚至鼓勵無證據指控,這是MeToo運動有別於之前歷次反性侵運動的區別所在。
從公眾心理層面講,MeToo運動的發動原理十分類似於美國民間早已廣泛存在的一種互助會組織——在這類組織中,有過相似記憶創傷的人會被鼓勵勇敢的說出自己的遭遇,大家彼此安慰,一起走出過去的陰影。
在這種”互助會“上講的話,當然是不需要講證據的,它們只是同病相憐者之間的訴苦,治療心理創傷。
而MeToo運動最開始,只是把這種模式搬到了網上,將整個網際網路變成了一個龐大的”反性騷擾互助會“,所以運動的主旨是”說出“而非”證明“,目的是引發社會關注和女性覺醒,而非法律追索。
所以受過性騷擾甚至性侵的女性,只要說出自己印象中的故事,運動就完成了。所以MeToo運動其實很少引發真正的性侵害訴訟,大部分女性敘述時,證據早已滅失了。
其實如果只是停留在引發社會對性侵問題重視的層面,MeToo運動的作用還是正向的。
但真理前進一步就是謬誤。而一個組織中,總有激進主義者想要不斷強行。於是這種照搬的兩個漏洞就隨著運動的發展凸顯了:
第一,與普通的互助會存在於私域空間中不同,該運動的主戰場是推特、臉書等公共社交網路。一旦運動參與者所言不實,甚至惡意誣告,對被指控者產生的名譽損害是很巨大的。
第二,與互助會的主要目的是意在幫助受創者走出困境不同,MeToo運動至少在發展後期,成為一種外向的、旨在讓受指控者付出重大代價的網路輿論攻勢。這個時候,運動參與者再說“證據不重要”,就很站不住腳了。
當然,MeToo運動的支持者為這兩個邏輯漏洞打了很多補丁,比如她們往往強調性騷擾只有零次和無數次的區分,認為多名女性站出來指認一個受控者性騷擾,就可以補足個體案件證據上的不足。
但就像一個人的回憶未必可靠一樣,一群人的眾口鑠金,也未必能人們看來那麼可靠——美國曆史上就曾發生過著名的“塞勒姆獵巫案”,高峰時期整個塞勒姆鎮上的人都一口咬定自己收了女巫的蠱惑和侵害,此案先後導致200多人被指控犯有巫術罪,19人被處死。
而事後證明,這場獵巫鬧劇,其實是一次“群體癔症”,當一種偏見形成氣候時,人們有時就是會在壓力下修改自己的記憶,一口咬定一些從未發生過的事。這是塞勒姆案給人類的教訓。
而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眾口鑠金“的思路其實違背了司法精神,從法律上講,如果沒有完整的證據鏈支援,即便無數個嫌疑湊在一起,也無法得出一個有罪判決。但在被MeToo運動主導的時下美國左翼輿論中,這樣“積零為一”、據無數個指控為一個定論的遊戲卻通行無阻——這其實是美國社會舊有的法制精神瀕臨淪喪的徵兆。美國人已經忘記了他們昔日凝聚精神的法制與道德基礎。
3
說回肯尼迪強姦案,在李昌鈺博士的幫助下,該案在美國形成了一個司法成例:美國法院此後在審理類似案件時,都會更加重視”痕跡物證“。錄影監控可能沒有,他人目擊也許會作偽,但兩個人如果發生了劇烈的肢體接觸,不可能沒有微量物質的交換。
檢測技術的進步,讓過去孤男寡女、瓜田李下的羅生門,變得清晰、可追溯了起來。在越來越多的條件合適的案件當中,我們應該相信這些證據一錘定音的說服力,而不是無視它們。
但與之相對應的,MeToo運動所主張”無證據亦可控訴“、以及”女性性別共識“,卻走了一條相反的道路。它在鼓勵受害女性不信任法律、不相信證據,單純為了男女對立、以及對性侵害的恐懼、厭惡而行動,試圖在網際網路上用輿論製造一個”寧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反性侵無菌箱“社會。
這種烏托邦表面上看對女性當然是極為有利的,但實際執行中,卻一定是所有人的地獄。一個常識是,性別不可能單獨存在,那些主張”性騷擾指控不需要證據“的女性,自己也有父親、甚至丈夫、兒子,也無法保證哪一天誣告不會落到自己家人頭上。
就像物理學上機械只能轉換能量的存在形式,而不能製成永動機。在社會學上,單純的法律和道德只能調節一個社會當中哪個群體多承擔一些風險、哪個群體多享受一點安全。
一個對性侵害完全沒有管束的社會,男性的安全和自由是被極大保障的,可是女性卻要承擔極大的受侵害風險。可能走在路上就會遭遇性侵害。
而一個對性侵害嫌疑管束極為嚴厲、指控不需要證據的社會,女性固然能享受最大程度的保護,但男性卻會面臨平白無故被誣陷、身敗名裂的風險。
這兩種社會走到極端,都會是人間地獄。
真正在降低兩性博弈整體風險的是”微量物質交換定律“這樣的技術進步。而在技術進步徹底拯救人類兩性關係之前。法律和道德能做的,只是儘量在兩性之間達成平衡,讓雙方都分擔一定的風險,都享受一定的安全。
換句話說,女性必須承受極小機率的受到騷擾卻求告無門的風險,而男性者要忍受極小機率的被誣告卻無法洗冤的風險。
法律和道德能做的,只是將這兩種風險同時降到極小值,因為單方面消滅其中一個,必然造成另一種風險的極大化。
而無論男人、女人或者任何群體,都沒有權利說:請讓我們只享受安全,而風險你們來擔。
基於上述認識,而並非男性的主觀偏見,我反對MeToo運動所鼓吹的那種任意指控。正如我同樣厭惡連性騷擾概念都沒有的古代男權社會一樣。
權責需要自負、風險卻需要共擔,無論男女之間、貧富之間、公私之間,這都是人類的宿命——必須妥協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