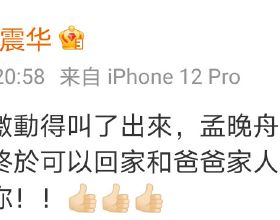不走宏大敘事的老路
北青藝評:首先請您簡單介紹一下《狙擊手》劇本創作的緣起吧。
陳宇:這個劇本是張藝謀導演的一個創作邀約。當時,我已經跟藝謀導演合作了一部電影《堅如磐石》,正在進行第二部戲的合作。有一天突然接到他的電話,說要做一部抗美援朝題材的影片,讓我把第二部戲的創作先暫停一下。當時,藝謀導演提出了大致的創作要求:第一是抗美援朝題材;第二希望是一個具有高密度情節、全程無尿點的型別片;第三是希望能夠以小見大,從一個小切口去展現抗美援朝精神,而不是全景式書寫,不走宏大敘事的老路。
北青藝評:後來您是怎麼確定狙擊手題材的?
陳宇:抗美援朝後期,志願軍開展了冷槍冷炮運動,湧現出了張桃芳等一批優秀的狙擊手個體以及群體。在深入瞭解這段歷史後,我們討論認為狙擊手題材影片作為戰爭片的一個亞型別具有對抗性、可看性、傳奇性,又是以往國產電影中少有的,很值得做。於是我很快出了比較詳盡的大綱給藝謀導演,我記得他當時還立刻給我打了一個電話,語氣很興奮,說這個方向對了。藝謀導演很嚴肅、令人敬畏,很少說這種鼓勵的話,一個故事構思一上來就能得到這種認可其實很難得。
北青藝評:與劇本相比,最後成片有哪些比較大的改動呢?
陳宇:改動並不大,主要有三方面內容作了刪減:一是片中朝鮮小孩的戲份,原本更豐滿一些;二是省略了一些表現主人公大永和偵查員亮亮情感關係的情節;三是劇本中對美軍人物形象的刻畫剖析更多,影片為保持敘事的緊湊性也進行了刪節。
北青藝評:您在北京大學任教多年,身兼導演、學者、編劇等多重身份,怎樣處理不同身份之間的差異?
陳宇:我心中的榜樣是謝飛老師,他是我在北京電影學院學習時的老師。我希望自己能夠像他一樣結合不同身份,在理論與創作上相輔相成。電影理論、電影產業以及電影創作原本應該是扭結在一起、沒有界限的,而現在的情形是,似乎彼此之間都有一些很難跨過的鴻溝和壁壘。我這些年一直持續用理論方法去指導實踐,再用創作回頭印證理論,同時也會帶著許多學生到創作一線中,以此希望形成一種理論與創作、教與學的良性互動。
陳宇
講故事是有技術含量的
北青藝評:《狙擊手》是張藝謀導演繼《懸崖之上》之後又一部非常強調敘事性的型別片,而且風格剋制、簡約。您怎樣理解導演的這種創作變化?
陳宇:這當然有整個影視產業大環境變化的影響,比如國產電影型別化的發展、網路流媒體的影響等等。從藝術本身上說,藝謀導演本人近些年是明確地迴歸到講故事、迴歸到敘事本身。我經常說,一個人可能最後都會走向自己的反面。對於藝謀導演這樣不斷尋求創新、突破自我的人來說可能更是如此。這個我覺得是好事,這並不是一種自我否定,而是一種升維。在這部影片創作過程中,他有意識地把以前最擅長營造的那些吸引觀眾的視聽奇觀和形式感去除,追求純粹的戲劇本體的內容。
北青藝評:《狙擊手》電影是一個很典型的按照“三一律”創作出的作品,兩支狙擊隊伍的遭遇戰全部發生在一個限定的時空中。這種限制時空的故事其實對編劇敘事能力要求很高,為什麼選擇這種挑戰難度?
陳宇:我的觀念是作者給自己的限制越大越好,如果能把它攻克下來,觀眾的獲得感、滿足感就越高,觀影感受就像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創作者千萬不能圖自個兒舒服,自己舒服了,觀眾就不舒服。因為觀影活動,本質上是一種觀眾和創作者的良性的心理較量。
北青藝評:那在這個過程中,除了一開始給您設定的大概方向之外,張藝謀導演還有沒有一些比較具體的要求?
陳宇:我們會一起討論每一場戲。要獲得作品較高的工藝性,就必須“打磨”。我們會就每場戲進行爭論、分析和修正。由於這部影片是一個高度緊張、情節性特別強的型別片,所以創作者要控制好每分每秒觀眾心理的變化,這就要對每一個情節點的情節轉折、人物邏輯、情感變化等進行明確的梳理。藝謀導演有個很形象的“捋繩子理論”,他說看電影就像拿一根繩子順著往後捋,成功的型別片應該是順暢到底的,如果中間捋著捋著遇到疙瘩或繩結,就是觀眾敘事上感覺困惑或者情緒上感覺不舒服,如果一部片子有三個以上的疙瘩,那這個片子就失敗了。這個“捋繩子”的工作我們花了很長時間。
北青藝評:您似乎特別注重劇作的邏輯性、科學性。
陳宇:這跟我的求學經歷有關。當時北電碩士畢業時,導演系畢業生人數很少,在產業中還是比較吃香的。但我靜心梳理後,發現自己的知識和能力系統中還個特別大的短板,就是實在不知道好劇本是怎麼寫的。所以後來決定去中央戲劇學院讀博,主要就是為了回到最原始的戲劇領域夯實自己的敘事能力。那些年的研究與創作,我在劇作原理層面也做了一些比較深入的研究,建構了自己的方法論。我自認為是一個講故事的人,而講故事是有方法、有規律的。很多人覺得誰都可以講故事、寫劇本,但我並不這麼認為。越是看似門檻低的領域,其實難度越高,寫劇本就是這樣一種有技術含量的事兒。對我來說,創作就是儘量用科學的方式去陳述內心中那些“不科學”的主觀感受,用確定性來對抗不確定性。我在創作中是比較反對依賴靈感的,靈感固然也重要,但你不能依賴它,你可依賴的只有原理和邏輯。
這實際上是一部青春片
北青藝評:您在創作《狙擊手》時,想借這個故事傳達一些什麼理念?
陳宇:我們跟導演商量到最後,確定下來的心態,就是要做一個儘量純粹的電影,一部做減法的電影。這部電影其實就是用戰爭片和青春片相雜糅的方式譜寫青春之歌,展現那個時代年輕人的精神面貌以及他們對信仰、對祖國的態度。我是希望把它當成一個青春片來寫,青春片就要展現那種個體的青春熱血。我們有意地減少作品包容的其它命題和思考,減少其他吸引觀眾注意力的要素,哪怕是初期設計中一些覺得比較驚豔的東西,為了整體效果也去除了。
北青藝評:這部影片其實是雙主人公設定:班長劉文武作為文武雙全的導師在前半段是核心人物,愛哭的陳大永則在他犧牲後變成了主角。其中,大永這位”愛哭的英雄”似乎是以往國產戰爭片人物序列裡少見的,為什麼有這樣的設定?
陳宇:剛剛講了,這部影片既是戰爭片,也是青春片。青春片要幹嘛?青春片就是講述一個人從不成熟狀態或者不完全成熟狀態最後到達成熟狀態。這個影片本質上呈現的也就是陳大永從一個愛哭的青澀計程車兵,走向一個勇敢堅定的戰士的成長過程。
北青藝評:其實影片在寫青春成長上有一個先天限制:在這種限定時空裡,很難寫出一個人的蛻變。
陳宇:確實是這樣,這一點一開始時我跟導演也有討論,而且最初劇本里的人物弧光做得更大,人物性格的起伏變化幅度更強烈。藝謀導演也曾提出,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人物不太可能完成特別大的變化。但是我仍然堅持,一定要展現出人物弧光,所以最終實際上是一種折中的做法。在我看來,這次戰鬥對於陳大永而言,一定是他人生中的一個重大的時刻,一次血與火、生與死的考驗。面對親密戰友們的犧牲,他從愛哭鬼向堅強戰士的變化我認為還是可信的。
北青藝評:既然是一部青春片,您期待影片能跟當前青年們形成一種怎樣的情感或精神連線?
陳宇:我覺得一個創作者基本上創作心理有兩種,一種是對某種價值的肯定,一種是對某種價值的質疑。懷疑是知識分子的特質,我們也需要懷疑的電影。不過這部影片是一部主流電影,主流電影一定符合當代主流人群某種共同的、最大公約數的價值觀,而不是寫少數人的價值觀,這是電影工業的劇本原則。我經常跟學生討論舉例,比如說好萊塢電影裡的主人公可以是個常規意義上的壞人,比如是個殺手,這沒關係,因為在美國大眾的語境中,這個“壞人”只是抽象的壞,甚至是一種異於普羅大眾的“酷“,是不會讓觀眾產生價值觀層面的反感的,但他一定不能做一些事情,比如一定不能拿起一隻小貓殺掉,一定不能欺負孩子。如果這麼做,他就直接與主流價值觀產生了劇烈衝突,就不可能成為主流電影的主人公。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這個時代和世界其實已經不缺獨特的思想與個性了,在網際網路的推動下,分歧已經遠遠大過共識。當我在進行主流電影的創作時,我願意去書寫蘊藏在當代社會中,無數人、無數種思想中的共識之處,每一次書寫都是對某種共同價值的肯定,進一步使大家,尤其是年輕一代凝聚在一起。
北青藝評:這部電影不僅有青春成長,還帶給觀眾一種類似通關升級的爽感。
陳宇:創作時確實是有這個意識的,甚至原始劇本里表現得更明顯。我在創作時一定程度上借用了武俠小說中的典型故事模型:一個小白在機緣巧合下得到武功秘籍或高人指點,最後成長為一代宗師。原始劇本里還有類似於主人公突然開悟、小宇宙爆發的設計。但後來考慮到真實性、嚴肅性是這部電影的基礎,如前所述,要做減法,最終就降低了這個成分。
北青藝評:說到嚴肅,片中有一些在戰場上很嚴肅的場面,比如美國士兵說中文的片段,觀影時卻引發了不錯的喜劇效果。
陳宇:說起來挺有意思,當時內部觀影時大家在這個地方也笑了。我們後來花了很長時間來想這問題,到底是好還是不好,最後大家覺得效果似乎還不錯,也就保留了下來。從理性角度分析,我覺得可能有兩個好處:第一個把角色都還原成人,不能把反方塑造成魔鬼或者概念化的工具人;第二,在那種全程緊繃的故事裡,需要稍微鬆弛一下,在心理節拍上進行一些調節。一張一弛,文武之道。
北青藝評:這也說明影片對於反方人物的塑造還是非常成功的。
陳宇:對。我記得首映式那天蔡國強老師也去了,他就說我最喜歡這個影片的就是對美軍的塑造,認為處理得非常準確。我也覺得如何在塑造美軍形象上把握好一種微妙的尺度,其實很難,美軍的戲是張末導演具體拍攝的,做得相當成功。我舉兩個細節,一個是片中每個美軍的名字都是經過認真考究的;其次,每個人說的英文都是帶有口音的。普通觀眾可能聽不出來,但當時張末導演做了很多功課。
北青藝評:片中五班的三次點名場景負載著不同的含義,令人印象深刻,同時似乎也處理了個體與集體的關係。您是怎樣理解個體與集體關係的?
陳宇:這是我當時想的比較多的一個問題。我覺得一個完善的人,他的情感態度以及對愛的理解,往往會經歷三個層級或者境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裡面討論過這個問題,我覺得挺有啟發。第一個層級,是我們可以愛抽象的人類,但不愛具體的人;第二個層級,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透過書中長老之口倡導的:去愛具體的人,不要愛抽象的人,去愛生活,不要愛生活的意義。
除此之外我覺得還應該有第三個層級,就是既愛具體的人,也愛抽象的人;愛生活本身的柴米油鹽,也愛生活的意義。但這第三個層級,一定是經歷了第二個層級之後才會到達的,先愛一個個具體的、不完美的人,才去愛群體的、抽象的精神和美德。集體與個人,不再是一種對立的觀念,主義不再是對個體的壓迫。這第三重境界,我覺得是一種更完善的情感,一種見天地、見眾生、見自我的境界。
回到這部影片,我要處理的最重要問題就是集體和個人的關係,這也是新主流電影創作中最難處理的。群體就是抽象的人,群體的情感就是抽象的愛,這往往容易寫;具體的人和具體的愛更難寫一些,我們也有很多商業片做的不錯。但既要把每個個體的獨特性與價值立住,還要觀眾愛上集體、抽象的精神價值,特別難。這部片子的創作,我主要就是要攻克這個難點。片中三次點名場景就是這種思考下的一個設計,一方面展現五班的集體精神,另一方面凸顯個人價值,呈現一種抽象與具體的關係。
北青藝評:近年來我國主旋律創作引人矚目。如果把《狙擊手》放到這個序列裡,您怎樣定位它?
陳宇:相對“主旋律”這個概念,我比較認同學界、業界近年來流行的“新主流電影”這個概念。我自己對“新主流電影”的發展有個脈絡梳理:新世紀之前,我們將比較符合官方意識形態的電影叫做主旋律電影,它更多的是一種類似於做硬廣告方式,從藝術性和娛樂性角度看往往比較欠缺。新世紀以後發生了某種程度上的變化,“新主流電影”的樣貌開始形成,大概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就是以《建國大業》為代表的明星制、大導演、大投資、工業化水準較高的電影;第二階段就是在主旋律表達的基礎上吸取型別化元素,比如《中國機長》等,這一類是目前市場的主體;第三階段,就是型別片階段,在型別片的基礎上引入一些主旋律的要素,《狙擊手》就是試圖這麼做的。我覺得這可能是未來很多新主流電影會走的一個方向。
好萊塢的問題很嚴重
北青藝評:從您談劇本創作與“新主流電影”的發展,可以看出您特別注重型別片與敘事性。
陳宇:因為型別片體系是電影產業專業化、市場化的體現,也是獲得觀眾較高認同的一種必然產生的體系。我特別主張,目前的中國電影要加快型別片體系的建設。目前雖然大家都在談型別片,但是型別片理論建設還比較弱、沒有系統化,型別片的實踐也往往存在很多似是而非的地方。
北青藝評:很有意思的是,在新時期之初,創作者們渴望“電影語言現代化”,當時的潮流是“丟掉戲劇的柺杖”、“電影要與戲劇離婚”等。近些年,電影創作似乎有迴歸敘事的潮流。
陳宇:這話可以稍微說遠一點。我認為今天我們迴歸的這個東西叫“經典敘事”,什麼是“經典敘事”呢,其實就是人類千百年來形成與傳承下來的比較穩定的講故事的方式,一種具有普適性和有效性的敘事方法論。經典敘事的真正廣泛發展與現代化程序開啟後小說、電影、電視等大眾娛樂形式的傳播有密切關係,比如經典好萊塢時期的型別片創作可以被視作經典敘事的一種相對成熟的代表。但這個經典敘事會遭受現代性的不斷挑戰與衝擊,比如“二戰”後的“新浪潮電影”等。但各種新鮮的潮流往往曇花一現,但經典敘事恆在。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各個國家各個時期湧現出的各種新電影運動基本都是這種模式:用現代性的觀念和現代性的形式去衝擊傳統方法,新鮮一陣後,經典敘事吸取了部分現代化的思想和手法,但整體創作樣貌還是又迴歸到大眾歡迎的這種經典的講故事的方法上。經典敘事其實是在應對各種挑戰中不斷拓展自身的,新好萊塢電影的形成就是一個典型例證。
北青藝評:怎樣理解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電影中經典敘事所遭遇的衝擊?
陳宇:我覺得可以歸納為這樣幾波吧。第一波就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湧現的“第五代”,他們是從影像創新、影像的現代性發起對經典敘事的一種衝擊。說起這種路徑的形成,其實是一個偶然。之前在上海電影節期間跟藝謀導演聊天,聊到這個問題:那時候電影人尋求中國電影的現代化為什麼不是如法國新浪潮那樣,從文學的角度進入,而是從影像的角度進行革新?藝謀導演挺認同北電倪震老師提出的一個觀點:可能就是因為張藝謀是攝影出身,加上在同一波人中年齡較大、人緣較好,很多人願意跟著他的這條影像創新道路進行電影的現代化革新。緊接著第二波衝擊就是來自“第六代”導演,他們是典型的法國“作者電影”的路數,是透過文學性進行電影的現代化革新的,比較曲高和寡,但塑造出一代“文藝青年”的電影觀。那麼,第三波對經典敘事的衝擊,就是這些年我國流行的來自美國的所謂高概念電影。我認為這種創作模式實際上是以大衛·奧格威為代表的現代廣告業的一種思維,就是把電影當做一個廣告專案來運作,以電影中的某個要素為核心,所有的創作是圍繞著這個要素進行的,而不是著眼在敘事本身。
北青藝評:就像迪士尼模式和“漫威電影宇宙”的流行。
陳宇:是的。我覺得好萊塢傳統幾大製片公司的電影創作問題現在比其他國家可能要嚴重,甚至可能會產生系統性崩潰。就是因為它的這種高概念電影的邪路,它脫離了電影原創性和敘事性的本體屬性,走到最後就變成了自我綁架。明知道這條路不能往下走,但又非走不可,所以導致續集氾濫、原創性匱乏、投資尾大不掉。我覺得國內近幾年相對可喜的一個狀況,就是大家似乎在往敘事性上回歸。我們之前也按照好萊塢的模式演練過一遍,什麼流量明星電影、IP電影、綜藝電影、各種視覺特效電影等等,最終還是得回到這個這門藝術最本質的功能和特性上,也就是說,一個電影人創作一部主流電影的低階目標是:講清一個故事,高階目標是:講一個精彩的故事。
文/李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