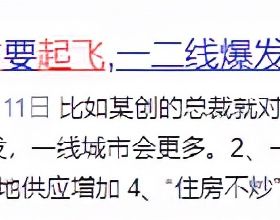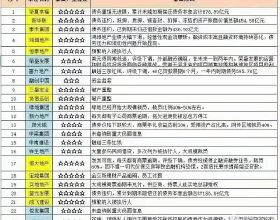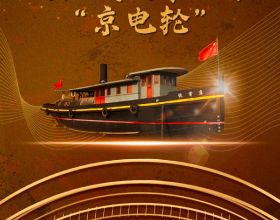✪ 李文珍 |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
【導讀】近日,中國計劃生育協會公佈2022年工作重點,其中提出,將開展未婚人群人工流產干預專項行動,引發公眾熱議。那麼,目前我國的未婚懷孕趨勢究竟到了什麼程度,以至於需要有關部門直接干預?
本文分析全國249922個樣本,呈現了1957年以來出生的女性群體未婚懷孕的新趨勢。研究顯示,總體而言,1957年以來出生的中國女性中,超過兩成曾發生未婚懷孕。分佇列和年代來看,年輕世代、改革開放後出生的世代未婚懷孕更多發,20歲及以上女性發生比例迅速增加。尤為引人注意的是樣本中1986年出生的女性的未婚懷孕比例高達33.1%,也就是3箇中就有1個有過未婚懷孕。但同時,未婚懷孕在我國仍有較高的婚姻轉化率,近六成“帶孕結婚”、近七成婚內生育;與OECD國家相比,中國仍處於非婚生育比例最低的少數國家行列。雖然同屬儒家文化圈,中國女性未婚生育的比例略高於日本、韓國,總體水平與希臘、土耳其更接近。
作者指出,作為自由主義、個體主義、性解放觀念的一種後果,未婚懷孕在中國確實有增多的趨勢,且正在由“受關注的青少年問題”轉向一種具有較高普遍性的群體選擇,但高婚內生育比例表明,與歐美社會出現的“婚姻-生育”關係弱化甚至斷裂不同,在中國的現代人口轉變中,“婚姻-生育”之間的關聯並未被打破。在“家”文化的強大作用下,未婚懷孕多數轉化為婚內生育。懷孕可以是一種婚前行為、個體行為,但生育仍然是一種婚內行為、家庭行為。未婚同居、未婚懷孕只是正式婚姻前的一個次多項選擇,成為向結婚和生育過渡的中間形態或過渡形態,而非替代形態。
本文原載《人口學刊》2020年第6期,原題為“1957年以來出生女性群體的婚孕新趨勢——以未婚懷孕為中心的分析”,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讀者思考。
1957年以來出生女性群體的婚孕新趨勢
——以未婚懷孕為中心的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禁慾主義文化的退卻,性觀念、性行為的個體主義取向逐漸對中國社會產生影響,人們的性觀念邁向了開放和寬容,未婚性行為變得多發。雖然如此,在早年的研究中,人們發現作為未婚性行為的結果,女性未婚懷孕後多數選擇流產。
然而隨著市場化、城市化、現代化的進一步深入,以上趨勢正在改變。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對未婚懷孕現象的認知正在由視其為“越軌行為”轉向“能理解”“也沒啥”。
在國際環境中如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所預期的,非婚同居成為家庭這種關係形式的替代之一。與非婚同居相伴隨的非婚生育已經成為歐美社會人口生育的重要來源之一,婚姻與生育之間的連線被打破。在全球化的時代,一方面,這種現象為中國社會的未婚同居和未婚懷孕提供了一種觀念上的背景;另一方面,梁漱溟等人所言的中國“倫理本位的社會”、儒家文化的特徵是另一種帶有約束性質的文化背景。
在這種觀念差異的背景中,當中國被置於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現代化程序並舉的情境中,傳統婚孕觀念和現代觀念碰撞是否會導致中國女性的婚孕狀況出現一些獨有的特徵?相對於此前中國人的婚前性行為——也就是婚姻與性之間的關係被打破成為研究重點,在此背景下,未婚懷孕作為可以用來考察性、婚姻、生育之間關係的一種重要現象,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呈現什麼樣的特點和模式?未婚生育會不會成為婚內生育的重要補充?中國和歐美社會是否呈現同樣的後人口轉變所描述的婚育模式變化?本文將首先對1957-2002年間出生女性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到2017年40餘年間的未婚懷孕狀況進行分析,然後對比OECD國家的非婚生育情況,最後討論中國和西方國家在第二次人口轉變婚育關係上的差異,為了解中國女性婚孕趨勢變化提供更多參考。
▍文獻回顧
中國學界目前關於未婚懷孕的文獻主要圍繞未婚懷孕的基本狀況、特徵、婚育模式間的關係進行梳理,也有一些對未婚懷孕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
對未婚懷孕總體狀況的研究中,學界對未婚懷孕發生比例的推算差異較大。由於所考慮群體的不同,這一比例推算的分佈區間在5%~40%左右。僅對未婚青少年的研究顯示未婚懷孕發生率不到5%。但在全年齡段的大城市已婚人口中未婚懷孕發生比例更高。徐莉對7省市的研究發現1987-1991年的結婚佇列中發生婚前懷孕的比例達16.8%。但這些和21世紀第一個10年後流動人口群體的未婚懷孕比例仍然不可同日而語。2013年15-59週歲的全國流動人口夫妻中未婚先孕的比例高達30.5%,2011年的調查還發現1980年以後出生的已婚且有子女的新生代農民工中第一胎為婚前懷孕的比例高達42.7%。
在未婚懷孕的年齡特徵上,大城市已婚群體和全國流動人口群體中都顯現出較年輕的出生佇列比年長的出生佇列更容易發生未婚懷孕的特徵,有的研究認為未婚懷孕發生年齡峰值為20歲左右,也有研究認為未婚懷孕具有明顯的“低齡化”趨勢。
在性、婚姻和生育的關係上,較多的研究集中在性觀念、性行為方面。劉汶蓉的研究認為中國農村社會對待性的態度仍然處於高度一致的低寬容水平,吳煒的研究認為70、80、90後群體的性觀念邁向了開放和寬容,但整體上仍然偏向保守,城市的態度相對多元。對於未婚懷孕和未婚同居的研究也在增加。比如,對區域性地區的調查發現婚前同居和未婚懷孕在區域性地區城鄉居民中是較為普遍的現象。還有的研究指出同居是一種“試婚”和婚姻的前奏。
也有少量公共衛生領域的研究聚焦未婚先育。有研究者對廣西來賓、廣東佛山、深圳龍華新區等地已婚女性或者參加婚檢的已婚女性進行調查,發現未婚先育在這些女性中的發生比例在10%~17%之間。不過這些調查的發生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比如廣西來賓壯族人口占多數,而佛山、深圳則都屬於流動人口較多的地區,在未婚生育方面的表現可能與全國存在差異。
已有對於區域性地區、區域性群體的研究顯示年輕的出生佇列未婚懷孕的發生機率更高,不同年代的未婚懷孕也隨著時間的推移存在著上升的趨勢,那麼,對於中國女性整體來說,是否確實存在這種趨勢?對於未婚懷孕和未婚生育之間的轉化狀況,以往的研究關注的較少,僅有針對少數特定地區的研究,很難據此推斷全國的狀況。
本文將使用“2017年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的生育史回顧資料詳細瞭解中國1957-2002年出生女性的未婚懷孕狀況以及未婚懷孕與婚姻、生育之間的轉化狀況,就未婚生育的狀況進行國際比較,以判斷正處於現代化程序中的中國是否呈現出和“第二次人口轉變”一樣的婚育關係特徵。
▍定義和資料
關於未婚懷孕一詞有不同的稱呼,有的使用的是未婚先孕,有的使用的是婚前懷孕,從內涵上來看錶達的是同一個意思。但是由於中國婦女不斷推遲婚姻,不婚的可能性也在增加,結婚可能未必是一個婦女一生中的必選項。考慮這一點,本文使用未婚懷孕來表述這一概念,不使用“先”或“前”這樣的字眼,但是內涵仍然是一樣的。
本文中的未婚懷孕指的是未發生婚姻事件的婦女發生懷孕事件。未婚懷孕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是當下未婚群體中發生的未婚懷孕事件,二是懷孕時未婚,現在已婚或曾婚群體的未婚懷孕事件。在婚和曾婚群體的未婚懷孕狀況需要借用兩個事件的發生時間來判斷,即初婚時點和懷孕結束時點。考慮小於32孕周的早產比例較低以及避免高估,本文沿用李丁、徐莉一般懷孕週期為8個月的假定,將未婚懷孕定義如下:未婚群體的懷孕;在婚或曾婚群體中,懷孕結果為活產者,其結束懷孕的時間減去初婚時間小於8個月;在婚或曾婚群體中,懷孕結果為非活產者,其結束懷孕的時間早於初婚時間。
“2017年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資料是原國家衛計委組織開展的對全國有代表性的專門的生育調查資料,調查了2017年7月1日零時年齡在15-60歲,即1957-2002年間出生的女性,調查樣本249 946人。調查提供了1957-2002年間出生女性的生育史情況回顧,出生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的女性多數在70年代後期、80年代初發生婚育行為,故該調查的生育史回顧能夠反映中國女性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至2017年40餘年間的未婚懷孕狀況。比較本次調查與2018年中國統計年鑑中的2017年末女性人口年齡結構發現二者在年齡構成上基本一致,但在25-29歲組統計年鑑所顯示的比例略高於調查比例1%,在55-59歲組2017年的本次抽樣調查高於統計年鑑2個百分點,這種差異影響較小。女性月經初潮年齡一般最早為12歲,因此,在計算中對初孕年齡小於12歲的個案進行了刪除,獲得有效樣本249 922名。
▍1957-2002年出生中國女性的未婚懷孕特徵與趨勢
1. 兩成15-60歲女性曾發生未婚懷孕
按照婚姻狀態、懷孕與否、懷孕時間、初婚時間劃分,所有女性的歷次懷孕狀況可以分為五類:未婚懷孕、婚後懷孕、不曾懷孕以及雖然懷孕過但無法判斷是否未婚懷孕、無法判斷是否懷孕。無法判斷是否未婚懷孕指在已婚群體中,雖然報告了懷孕,但懷孕結果為非活產,懷孕結束時間與初婚時間間隔7個月以內;沒有報告懷孕結束時間、初婚開始時間。無法判斷懷孕指在調查中未婚(同居)者報告有過懷孕,但是其至今懷孕次數為0且並未填答懷孕史,無法判斷是否懷過孕。此外,對於調查中報告了懷孕次數、懷孕結束時間,但是對問題“是否懷過孕”答案為“否”的,校正為懷過孕,並判斷是否未婚懷孕1。加權統計如表1所示。
表1 2017年15-60歲受訪者的懷孕狀況
資料顯示2017年15-60歲,也就是1957-2002年出生的249 922名女性受訪者中,有21.5%的女性發生過至少一次未婚懷孕。這些發生過傳統意義上“越軌行為”的未婚懷孕人士,91.9%在調查時都已婚,只有8.1%在調查時並未或尚未走入婚姻。這與中國社會普婚的文化觀念有很大關係。
15-60歲女性中未婚者佔22%,在這些未婚者中發生未婚懷孕的比例為7.9%。在(曾)婚女性佔78%,其中發生過未婚懷孕的比例為25.3%,婚後才發生首次懷孕的比例為69.9%。在(曾)婚女性中發生過未婚懷孕的比例高於目前未婚者。在(曾)婚女性中25.3%的未婚懷孕比例高於徐莉對1992年中國7省市已婚女性調查資料的推斷,她推斷1987-1991年結婚的佇列中,發生未婚懷孕的比例為16.8%。說明至少在已婚群體中,隨著時間向現在推移,未婚懷孕比例在升高。
為了與李丁、齊嘉楠等的研究結果對比,本文也計算了流動女性的未婚懷孕發生比例。結果顯示流動女性的未婚懷孕發生比較戶籍女性高6個百分點。這與已有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在具體數值上,本文計算的流動女性未婚懷孕發生比是28.7%;李丁用2011年流動人口監測資料推算流動女性未婚懷孕比例為28.1%,2013年資料推算為28.9%,2015年資料推算為30.6%;齊嘉楠、楊華用寬口徑推算2013年流動女性未婚懷孕比例為30.5%。這些推算表明2017年流動女性的未婚懷孕比例至少在28.7%~30%之間。隨著時間的推移,未婚懷孕比例在流動女性中呈上升趨勢。
2. 年輕世代、改革開放後出生的世代未婚懷孕更多發
一般認為50歲女性已完成其懷孕行為,所以在分年齡考察15-60歲女性的懷孕情況時,也以50歲女性(1967年出生)的未婚懷孕比例作為一個比較的基準線(見圖1)。
圖1 15-60歲女性分年齡懷孕狀況
由圖2可見,在31歲以上的群體中未婚懷孕比例隨著世代的年輕化而上升。
圖2 未婚初孕發生的年齡構成
注:1985-1989年、1990年後出生的兩個世代尚處於懷孕生育旺盛期,未婚初孕較低年齡段比例會隨較高年齡未婚懷孕發生數增加而繼續降低
未婚懷孕比例存在四個明顯的區間:第一區間,15-25歲女性的未婚懷孕比例不斷升高,但仍然低於50歲女性未婚懷孕比例;第二區間,26-38歲女性的未婚懷孕比例已經超過50歲女性;第三區間,39-52歲女性的未婚懷孕比例在50歲懷孕比例水平線附近波動;第四區間,53-60歲女性的未婚懷孕比例低於50歲水平線。
從年齡來看,第二區間的女性處於懷孕和生育旺盛期,在生育年齡結束之前未婚懷孕比例仍有可能繼續升高。這個區間內年輕世代的未婚懷孕比例已經超過50歲及以上更年長的世代。
從時代特徵來看,第四區間群體未婚懷孕比例最低,這一區間的群體出生在1956-1965年之間,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頒佈,規定廢除包辦強迫的封建婚姻制度,實行男女婚姻自主、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權益。思想觀念從舊的束縛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自主觀念逐漸普及,這可能是當時未婚懷孕比例緩慢上升的最主要原因。但是總體上當時的社會觀念仍然是禁慾式的、集體主義壓制個體主義的時期,故而未婚懷孕比例最低。
第三區間覆蓋了動盪十年時期出生的群體,未婚懷孕比例在23.6%附近波動,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升降趨勢。推斷社會環境的動盪可能使得此時期出生的世代更傾向於生存和自保,所以未婚懷孕比例並沒有維持第四區間的上升勢頭。
第二區間的女性出生於1979-1991年間是改革開放以後出生的群體,這個群體完全成長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環境中,經歷了經濟的騰飛、自由觀念、個體主義以及性解放觀念的傳入。這是第二區間未婚懷孕比例高企的最大社會背景。
尤為引人注意的是1986年出生的女性的未婚懷孕比例最高達到33.1%。也就是3個1986年出生的女性中就有1個發生過未婚懷孕。考慮31歲女性尚處於懷孕生育旺盛期,調查時還存在有未孕未育狀況,因此現年31歲女性在其50歲以後終身未婚懷孕比例可能高於現在的33%。同樣,現在也無法判斷調查時15-31歲女性到婚育期結束時,哪一個年齡段的女性的未婚懷孕比例最高。
第一區間女性也出生在改革開放以後,但是由於受教育年限的延長等,15-25歲女性多數還在學校接受教育,多數還未考慮懷孕或生育,因此,調查時未婚懷孕比例仍比較低。
從圖2也可見,即使在40歲以上年齡的世代,未婚懷孕和婚後懷孕隨著世代的年輕化,落差越來越小。隨著世代年輕化,未婚懷孕比例增加,婚後懷孕比例下降,但是總體懷孕比例也有微弱減少,沒懷孕過的比例在增加。
3. 未婚初孕發生年齡構成:20歲以下女性發生比例先升後降,20歲及以上女性發生比例迅速增加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1980年)規定,男22週歲、女20週歲為法定結婚年齡。也就是說法律認定20週歲的女性已經具備結婚及孕育的時間合法性。按此規定,本文將第一次發生未婚懷孕時的年齡段劃分為:12-19歲、20-24歲、25-29歲、30-34歲、35歲及以上。
在以往的研究中有文獻認為未婚懷孕存在“低齡化”傾向。本文對女性未婚初孕發生時所在年齡段的分析發現女性在12-19歲的低年齡段發生未婚初孕的比例經歷了先升後降,尤其在1970年以後出生佇列中,未婚初孕低年齡段發生比例持續降低,20歲及以後(尤其是25歲及以後)發生的未婚初孕迅速增加。
排除仍處於懷孕生育旺盛期的90後女性,80後及更年長女性在12-19歲較低年齡段發生的未婚懷孕,隨出生時間的推移,經歷了先升後降的趨勢。接近完成生育時間的1980-1984年出生的女性在12-19歲未婚懷孕比例最低(18.6%),比1965-1969年間該比例低了8個百分點,在20歲及以上年齡發生未婚懷孕的比例達到81.4%。
20歲以上年齡成為發生未婚初孕時的年齡主體。圖2顯示1970年以來出生的佇列中20歲及以上年齡的未婚懷孕佔比持續上升。
在20歲及以上的未婚懷孕比例中,25-29歲時發生的未婚懷孕比例表現出了明顯的上升趨勢。1965-1969年出生佇列中,25-29歲時發生未婚懷孕的比例為7.4%,但1980-1984年出生佇列中這一比例劇增至20%,是前者的將近2倍。30-34歲更高齡時發生的未婚懷孕佔比也有增加。1964年前出生世代中該比例為1.1%,1975-1979年出生佇列該比例增加到3.3%。
20歲早已過了成年年齡,可以排除年幼對避孕方法缺乏瞭解等狀況,在1970年及以後出生的佇列中,20歲及以上未婚懷孕比例的迅速增加,更不可能是無意識的行為。比較意外的是在1956-1964年間出生佇列,20歲及以上的未婚懷孕比例高於1965-1969、1970-1974年兩個出生佇列。推測有兩個原因,一是由於當時禁慾式的社會文化,12-19歲的未婚懷孕發生比例本來就較低;第二,與婚姻政策的變化有關,我國20世紀70年代推行“晚、稀、少”政策。這一政策提倡晚婚,鼓勵男性和女性分別在25歲和23歲以後結婚。當時結婚需要單位批准,很多單位只批准達到晚婚標準的人結婚。直到1980年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規定只要符合法律要求就可以結婚,男性不得早於22週歲、女性不得早於20週歲。計算不同出生佇列女性的初婚(同居)開始時間也發現(見表2),1964年及以前出生群體的未婚同居年齡、初婚年齡明顯高於1965-1969年出生佇列。所以在1970-1980年間可能存在大量青年男女已經有了結婚打算,但是尚在等待批准的情況。這個時期發生的未婚初孕就存在年齡偏高現象。
表2 不同出生佇列的初婚(未婚同居)年齡狀況
4. 平均未婚初孕年齡、婚後初孕年齡不斷推遲
分年度來看,隨著時代的發展,平均未婚初孕年齡、平均婚後初孕年齡都在推遲,且平均婚後初孕年齡推遲幅度大於平均未婚初孕年齡。
圖3描述了2006-2016年各年度15-49歲女性的未婚初孕、婚後初孕發生時的平均年齡。
圖3 2006-2016年15-49歲女性未婚初孕、婚後初孕平均年齡
2006-2016年間平均未婚初孕年齡經歷了2006-2010年的一段平穩期後較快上升,到2016年時,6年間推遲了近1歲,達到22.73歲。
2006-2010年間平均婚後初孕年齡也經歷了一段平穩期,在24~24.3歲之間波動,此後經歷了快速上升,6年間推遲了1.89歲,達到25.94歲。
平均未婚初孕年齡與平均婚後初孕年齡的差值也在擴大。11年間二者的年齡差從2.27歲擴大到3.21歲。
平均未婚初孕年齡、平均婚後初孕年齡的推遲反映了中國育齡婦女生育年齡普遍推遲的狀況。在女性普遍推遲生育的背景下,婚後初孕年齡的推遲幅度更大。
5.多次未婚懷孕明顯減少
出於對女性生理及心理健康的關注,多次未婚懷孕也是未婚懷孕受到關注的方面。調查發現未婚懷孕的多次重複發生減少,而僅發生過一次的未婚懷孕增加。越年輕的世代這一趨勢越明顯。
如圖4所示,隨著世代的年輕化,在發生過未婚懷孕的群體中平均未婚懷孕次數逐漸減少。1964年及以前出生群體中未婚懷孕者平均發生過1.48次未婚懷孕,1980-1984年出生佇列未婚懷孕的女性平均未婚懷孕次數為1.288次,下降了13.2%。
圖4 不同出生佇列未婚懷孕女性的未婚懷孕次數構成
在發生過未婚懷孕的女性群體中只發生過1次未婚懷孕的佔78.7%,發生過2次未婚懷孕的佔13.96%,二者合計佔92.7%。
2次以上的多次未婚懷孕比例下降。分不同的出生佇列來看,3次、4次及以上未婚懷孕的發生比例顯著下降,4次及以上未婚懷孕比例從1964年及以前出生群體的5.67%下降到1980-1984年出生佇列的1.84%,下降幅度67%。3次未婚懷孕的發生比例也有下降,從1964年及以前出生佇列的7.17%下降到1980-1984年出生佇列的4.04%,下降幅度43%。
上升的是僅發生一次未婚懷孕的比例,這一比例從1964年以前出生佇列的74.12%上升到1980-1984年出生佇列的79.95%。
多次未婚懷孕的比例下降,一方面與高孩次子女生育的減少有關;另一方面與避孕用具的普及使用有密切關係。
▍同居、懷孕與婚姻、生育間的轉化狀況
在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的描述和西方社會的現實演變中,同居成為了婚姻替代形式之一,婚姻和生育之間的關係發生了斷裂,婚外生育大量出現,成為生育的重要甚至主要來源。但在中國1957年以來出生的女性中,未婚懷孕、未婚生育狀況表現出了與西方社會有一定趨同性但又有明顯差異的特徵。
1.“同居-懷孕-生育”關係:同居伴隨高未婚懷孕率、高活產率
如已有研究指出的,同居是一種“試婚”,在無法律認可的狀況下潛行婚姻之實。同居行為使得同居關係中的女性完全暴露在懷孕風險之中,極大增加了懷孕的可能性。未婚同居關係也較好地保障了活產生育行為。
未婚同居狀態下,未婚懷孕的可能性大到什麼程度呢?圖5資料顯示九成以上(92.6%)的未婚同居者都發生了未婚懷孕,而未婚(未同居)者這一比例僅為2.7%。
圖5 婚姻狀態與懷孕情況構成
未婚同居狀態下未婚初孕活產的可能性也大幅增加。在未婚(未同居)狀態下的懷孕,其懷孕結果為活產嬰兒的佔比為70%,未婚同居者懷孕結果為活產嬰兒的比例為93.4%,在所有的婚後懷孕的懷孕結果中,活產嬰兒佔比96.3%。未婚同居為未婚懷孕提供了更接近於在婚狀態下婚後懷孕的生育結果。
未婚(未同居)懷孕女性的人工流產比例達到25.7%,流產比例超過了所有其他婚姻狀態。考慮可能會有未婚(未同居)懷孕女性不報告懷孕及流產情況,人工流產比例可能更高。
2.“懷孕-婚姻-生育”關係:未婚懷孕伴隨較高的婚內生育
為了考察懷孕、生育、婚姻三者之間的關係,本文根據在(曾)婚者中發生過未婚懷孕者的生育結果(活產、非活產),懷孕結束到結婚之間的時間間隔,計算了在(曾)婚者未婚懷孕的四種情況:(1)帶孕結婚。未婚懷孕後結婚,在婚後發生活產的即為帶孕結婚,這種情況包括第一次未婚懷孕後的帶孕結婚以及初次或多次未婚懷孕皆流產,第一次活產是未婚懷孕所致但是活產行為發生在結婚事件後的狀況。(2)先生育後結婚。指不僅發生了未婚懷孕,還發生了未婚活產。(3)婚前流產,婚後懷孕並生育。指未婚懷孕後流產,第一次活產系婚後懷孕和婚後生育。(4)無法判斷生育和結婚順序的未婚懷孕。
其中第(1)和(3)兩種情況都是雖然未婚懷孕過,但是初次生育仍然發生在婚內的行為。
考察發現未婚懷孕過,但是初次生育系婚內生育的情況佔近七成。其中,帶孕結婚貢獻了59.64%,未婚懷孕後流產未生育、然後結婚並在婚後懷孕者貢獻了7.17%。二者合計66.81%。
在帶孕結婚中也分兩種情況。一種是初孕時帶孕結婚,貢獻了59.64%中的56.19%,另有3.45%系初(多)次未婚懷孕流產後再度懷孕並帶孕結婚。第一種帶孕結婚,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此時結婚的伴侶有極大的可能是發生未婚懷孕行為時的伴侶。存在兩種可能性,第一種可能性是在懷孕的情況下,以前無明確計劃的婚姻事件被提上日程;第二種可能性是伴侶間本就有意願結婚,懷孕並不算是在規劃外的。不管哪種都是未婚懷孕事件催化了婚姻事件。第二種帶孕結婚則包含了未婚初孕後婚姻談不攏而流產的狀況、結婚伴侶與初次未婚懷孕的伴侶有可能並非同一人。
另有32.24%的未婚懷孕轉化成了未婚生育,在這一部分未婚懷孕中,在孩子1歲以前走入婚姻的佔了三成,比較難判斷這一部分帶著1歲以內孩子的未婚懷孕者的伴侶身份,也有一定的可能是未婚初孕的伴侶。
表3 在(曾)婚者中未婚懷孕者的育-婚時間間隔
注:育-婚間隔即以懷孕結束時間減去初婚開始年月。不確定是否懷孕的個案佔總懷孕個案的2.8%,本處略去,不予計算
雖然帶孕結婚和婚前流產、婚後懷孕並生育的狀況有很大差異,但二者同屬婚內生育,其背後邏輯是一樣的,即生育都發生在婚姻事件後,生育行為仍然出現在婚姻內,初次生育的子女仍然在傳統的家庭秩序中。 對中國人來說,“家”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社會秩序的核心節點,人們透過“家”來獲得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社會身份。撫養子嗣和傳承是“家”最重要的目的和任務,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和文化傳統會促使未婚懷孕轉化成婚內生育。
這種文化和傳統的影響力之大,與西方社會有非常大的差異,仍以前文提到的美國為例,美國國家健康統計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的2006-2010全國家庭成長調查(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Growth)顯示,18%的未婚懷孕在孩子出生前發展為未婚同居,5%發展成了婚姻。與中國的轉化率相比差距極大。
3. 活產構成:未婚生育佔所有活產數的比例不足9%
在西方社會的第二次人口轉變中,非婚生育是生育的重要來源,甚至是主要來源。在中國的情況則有所不同。
本文根據歷次懷孕發生時的婚姻狀況、懷孕結束時間與結婚時間間隔、活產情況,甄別出歷次懷孕是否未婚生育的5種情況:(1)未婚狀態下的所有活產,為未婚生育;(2)在(曾)婚、懷孕結果為活產、懷孕結束時間早於初婚時間,為婚前生育;(3)在(曾)婚、懷孕結果為活產、懷孕結束時間減去初婚時間大於0但是小於8個月的,為帶孕結婚的婚內生育;(4)在(曾)婚、懷孕結果為活產、懷孕結束時間減去初婚時間大於等於8個月的,為婚後懷孕及生育;(5)在(曾)婚、懷孕結果為活產,但是缺乏懷孕結束時間或初婚時間的歸入無法判斷類別。
(1)和(2)都是未婚時發生的生育,(3)和(4)都屬於婚內生育。
計算發現在所有396 022個活產嬰兒中,生育是在未婚時發生的狀況佔全部活產數的8.96%,活產系婚內生育的佔91.02%,另有0.01%無法判斷是否婚內生育。
圖6 15-60歲女性活產事件中的未婚生育狀況
注:活產總數=396 022。
不到9%的未婚生育中調查時未婚者的未婚生育貢獻了2.73%,調查時在(曾)婚者的未婚生育貢獻了6.23%。
前三次懷孕活產嬰兒數佔全部活產嬰兒的92%。前三次懷孕活產數中,初孕中的未婚生育佔比最高,約為10.8%,第二次懷孕和第三次懷孕的活產生育中,未婚生育的比例降到7%及以下。
圖7 2006-2016年15-49歲女性活產事件中的未婚生育比例
注:活產總數=106 463。
分年度來看,未婚生育在所有活產中的發生率高峰出現在2009年,未婚生育佔當年所有生育的10.4%,此後逐年降低,2016年時未婚生育佔當年生育總數的4.3%。
2009年以來未婚生育的下降與近年來一孩生育率不斷下降有密切關係,如圖7所示,50%的未婚生育都是一孩生育,晚婚、生育推遲等導致的一孩生育下降也影響了未婚生育的逐年走低。
4. 中國與OECD主要國家的非婚生育狀況比較
為了考察在世界環境下中國未婚生育的相對地位,本文對比了主要的OECD國家的非婚生育狀況。OECD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起步更早,相對而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更高,其主要國家更多地呈現出第二次人口轉變中婚姻與生育關係變化的特徵。
OECD各國非婚生育比例分佈差異較大,第一類以智利、北歐五國、法國為代表的國家,其非婚生育比例都在50%以上,也就是說2016年出生的孩子中有一半以上都是非婚生子女。南美洲的智利是全世界非婚生育比例最高的國家,2016年的非婚生育佔總出生的72.7%。
第二類是以西歐國家及美國、英國、德國等老牌發達經濟體為代表的國家,非婚生育比例都在30%~50%之間。
第三類是東歐劇變後產生的轉型國家。進入2000年以後,非婚生育比例也一路飆升到30%以上,斯洛維尼亞等更高達50%以上。
第四類是2016年非婚生育比例低於30%的國家,一部分是宗教影響力強大的國家,如波蘭、瑞士、希臘、土耳其。義大利則是個例外,20世紀80年代中期義大利在世俗化方面有了較大的變化,其未婚生育比例在2000年後上升較快,已經超過了20%。另一部分是同屬於儒家文化圈的日本、韓國,非婚生育比例低於10%。第四類國家總體上屬於非婚生育比例起點低、增長極緩慢的狀況。1960-1980年的20年間非婚生育比例增長都不足5%,2000年以後非婚生育比例雖有上升,但上升幅度仍然很小。從50多年間的變化來看,儒家文化圈國家的非婚生育比例上升速度顯著低於波蘭、瑞士。
圖8 1960-2016主要年份OECD國家及中國的非婚生育比例變化
圖9 1960-2016年非婚生育比例低於25%的OECD國家及中國
中國也處於最低非婚生育比例的國家行列。不過,雖然同屬儒家文化圈,中國女性未婚生育的比例略高於日本、韓國,總體水平與希臘、土耳其更接近。
▍討論:中國女性的“性-婚姻-生育”關係模式
1. 未婚懷孕多發揭示了“性-婚姻”關係的進一步分離
如前面的分析中國女性“性-婚姻”關係的進一步分離已經成為一種顯著的趨勢。這不僅表現在婚前性行為上,更進一步發展和表現為中國15-60歲女性人口中超過兩成曾發生未婚懷孕,年輕世代的未婚懷孕更多發等方面。
與早前研究中未婚懷孕被視為“越軌”行為、更多發生在青少年身上相比,發生在20歲以上成年女性身上的未婚懷孕迅速增加且多次未婚懷孕明顯減少。說明多數未婚懷孕並不是無意識的行為,而是女性對於婚姻和性的觀念已經發生了變化,並不嚴格遵循傳統的“婚姻-性”的時間順序。尤其在改革開放以後出生的女性中,未婚懷孕發生比例劇增,都表明了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推行,個體主義觀念影響了人們對性和婚姻的觀念,這與第二次人口轉變中所描述的是一致的。
在中國女性的未婚懷孕行為中未婚同居行為伴隨著極高的未婚懷孕發生率,未婚同居所發生的未婚懷孕也具有極高的活產比例,較少發生人工流產行為,也發揮了類同婚姻形式的作用,但如於嘉、謝宇根據CFPS調查資料的發現中國無論男女,每次未婚同居的平均持續時間不到11個月,時間較短,是一種“試婚”行為和婚姻的前奏,並不是傳統婚姻形式的替代。第二次人口轉變中所描述的以及西方社會中的現實則是非婚同居長期持續、具有類同婚姻形式的屬性、成為婚姻形式的一種替代,中國的狀況顯然與此不同。
2. 高婚內生育比例揭示了“婚姻-生育”之間關聯並未被打破
傳統婚姻形式並不能被代替的最重要原因是“婚姻-生育”之間的關聯仍然較為牢固。一方面,發生過未婚懷孕的女性,其初次生育系婚內生育的情況佔近七成。這部分女性雖然打破了“婚姻-性”之間的固有次序,但在面對生育時仍然遵循了“先結婚後生育”的傳統觀念,保證了自己的頭胎子女在婚內出生。
另一方面,在所有活產嬰兒中九成以上的嬰兒都是婚內生育,未婚生育佔所有活產數的比例不足9%。分年度來看,在近年一孩率下降的背景下,2010年以來每年未婚生育佔所有活產的比例已經低於這一總體水平。
對比OECD國家的非婚生育情況,無論是相對於北歐國家、西歐國家、東歐劇變後轉型國家,還是宗教信仰氛圍濃厚的國家,中國的未婚生育比例都處於十分低的水平。介於比例最低的日、韓和土耳其、希臘之間。
3. 傳統“家”觀念地基上的“第二次人口轉變”變奏:“性-婚姻-生育”關係的部分解放
不斷上升的未婚懷孕發生比例表現出了中國女性日益開放和自由的性觀念,揭示了中國社會也在呈現出第二次人口轉變的部分特徵,“婚姻-性”的先後次序已經被打破,但是第二次人口轉變所描述的“婚姻-生育”關係的斷裂,以及傳統婚姻形態弱化甚至被取代的狀況未必會出現,生育對於中國家庭和社會仍然具有重要的特殊意義,使得“婚姻-生育”的關係仍然遵從傳統的次序。
費孝通從功能角度所解釋的“婚姻的意義……,是在確立雙系撫育”指明瞭婚姻之於生育的功能性意義。在被現代性不斷滲透的社會中,保證婚姻對於生育的功能性意義,則歸因於中國傳統的“家”的觀念及“家”在中國社會秩序中的核心節點位置。
按照金耀基、梁漱溟等的分析,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中國主流文化思想中,“家”是連線修身、治國平天下的節點,“治國”對個體來說是一種理想、“修身”主要靠自律,“家”則具有共同體特徵,共同體內部的力量使得“家”倫理的規範和約束在實踐中具有了可操作性。
也因此,“家”被賦予了諸多功能。“家”是構成國家、社會的重要秩序。個體在“家”中獲得身份認同,從而獲得社會位序。個體從出生開始,就被納入“家”中相應的位置,從而獲得社會體系上的某個位置。個體死亡以後,則進入“宗廟”中的某個位置。即使到了現代,宗廟的具體形式衰落,但其意義核心、文化抽象仍然存在。
生育雖然仍然是發生在個人身上的行為,但其意義早已超出個人、夫妻甚至小家庭的範圍,生育既是繁衍,又具有上承祖宗、下啟未來的功能。
從這個角度來看,個體主義、自由化的觀念可以在個體層面影響人們的行為,比如性行為和懷孕,但涉及生育時就超出了個體意義,而變為“家”領域內的決策。無論是要“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家”“認祖歸宗”的觀念,還是“結婚以後孩子再出生”的面子觀念,或者是未婚懷孕多數轉化為婚內生育、未婚生育比例極低,未婚者沒有相對穩定的同居伴侶(無法結婚)時相對更高的人工流產率,都是類似上述的“家”文化長期作用的結果,不支援非婚生育的相關制度規範也是這一文化長期作用的結果。
這種文化底色使得中國女性的婚孕、婚育選擇呈現出混合了第二次人口轉變和傳統模式的特徵。一方面,在個體層面,婚姻-性(懷孕)關係出現更進一步的分離,另一方面,生育與婚姻並未明顯分離,未婚同居、未婚懷孕是正式婚姻前的一個次多項選擇,成為向結婚和生育過渡的中間形態或過渡形態。中國一直以來傳統的婚育模式:“戀愛-結婚-性行為/懷孕-生育”仍然佔主流之外,一支具有混合特徵的婚育模式支流“戀愛-性行為/未婚同居(未婚懷孕)-結婚-生育”也正在顯現。
▍結語
作為自由主義、個體主義、性解放觀念的一種後果,未婚懷孕在中國確實有增多的趨勢且正在由“受關注的青少年問題”轉向一種具有較高普遍性的群體選擇。但是基於“家”文化的深刻底色,人們仍然在遵循或維護著生育和婚姻之間的固有聯絡,懷孕可以是一種婚前行為、個體行為,但生育仍然是一種婚內行為,必須考慮家庭訴求、社會文化規範的行為。相較主流的傳統婚育模式“戀愛-結婚-性行為/懷孕-生育”,支流模式“戀愛-性行為/未婚同居(未婚懷孕)-結婚-生育”已經有所變化,但仍然在遵循“先結婚後生育”的傳統次序。未婚同居、未婚懷孕已成為正式婚姻前的一個次多項選擇,成為向結婚和生育過渡的中間形態或過渡形態,而非替代形態。
當然,除了從未婚懷孕到婚姻的高轉化率,仍然有相當一部分未婚產子的狀況,關注這部分群體的狀況,尤其是未婚生育對母親、嬰幼兒在生理、心理上的影響都將有益於提高母親和嬰幼兒的福利水平。
本文原載《人口學刊》2020年第6期,原題為“ 1957年以來出生女性群體的婚孕新趨勢——以未婚懷孕為中心的分析 ”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絡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