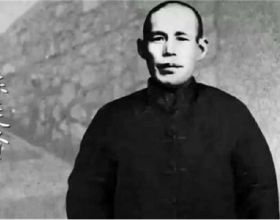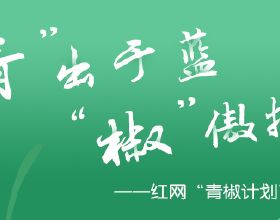12世紀蒙古興起於漠北,1206年其領袖成古思汗建立蒙古汗國。旋即對外連續展開徵戰活動。亡西遼、伐金朝、滅大理,四次西征,五戰西夏,席捲中亞,橫掃欽察,重創非洲東北角……蒙古汗國成為橫跨亞歐地區的龐大政權。
遼東和吉林東南部,歷來是中國與朝鮮半島的陸路通道。這裡的政治形勢,對蒙元與高麗關係相當重要。成吉思汗六年(1211年)第一次南下伐金。早已腐敗的金朝節節敗退。翌年汗國軍進入東北地區,襲取重鎮東京(今遼陽)。不久,東北地區同時存在四種軍政勢力:除汗國和金朝外,還有以耶律留哥為首契丹等族的反金勢力;蒲鮮萬奴領導的東真國,繼之改稱東夏國。其中,能夠執形勢之牛耳者,非蒙古汗國莫屬,但很長時間裡其注意力不在東北戰場。不久,耶律留哥投降汗國,進而急劇壯大汗國在東北地區的勢力。蒲鮮萬奴領導的東夏國反金是明確的,但對汗國叛服不常。
是時,朝鮮半島中南部是高麗政權。該政權系918年由王建創立,故常以“王氏高麗”相稱。定都開城即王京。這是個政治、經濟、文化相當發展的國家,並在東北亞具有一定影響。遼朝和金朝相繼將高麗納入天朝體系秩序中,但不隨意干涉其內政,自身保持相對獨立性。與此同時,高麗還與五代、北宋、南宋保持密切關係。高麗對遼金,大體是“事強”關係,同時帶有“事大”因素;對兩宋,基本是“事大”關係。
高麗政權建立不久,重文風氣漸盛。文臣受寵,武臣受壓,文武臣僚矛盾日漸尖銳。毅宗二十四年(1170年)以武臣鄭仲夫為首發動政變,殺文臣,廢毅宗及其太子,擁戴毅宗同母弟昕即王位,史稱明宗。武臣間幾經爭奪,最後崔仲獻勝利,成為勢傾朝廷者。繼之,崔氏子孫怡、沆、竩連續專權。崔氏專權後期,嚴重影響內政、外交。致使矛盾重重,國勢不振,王權衰頹,軍隊贏弱乃至不可用。
蒙古汗國,正值朝氣蓬勃;王氏高麗,恰是日益衰敗。二者向相反方向不斷運動。蒙元與高麗的關係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展開的。為此,高麗必然付出一定的代價。
成吉思汗六年(1211年),金朝遣完顏惟孚來高麗“賀生辰”;高麗熙宗“遣將軍金良器回謝”。良器一行“至通州,遇蒙古兵”,“中矢而死,下節九人亦遇害”。良器和下節九人的死亡情節不一樣,前者可能誤中流矢,也可能被有意射殺;後者大體有意被殺害。這是汗國與高麗的較早之接觸。使團被害,在雙方關係中雖不算大事,但汗國卻給高麗君臣留下不好的印象。
背離留哥的契丹人乞奴、金山等樹起反對汗國的旗幟。在汗國等的打擊下,1216年率眾東撒,進入高麗。這些人帶有流竄、就食、避難的性質。他們攻佔城鎮,掠奪食物,甚至南下到開京之南。建立許多據點,其中江東城是主要據點。高麗朝野為之震動,不斷派兵圍追阻截。在香山之戰中雖取得很大勝利,但也多次吃敗仗。疲於奔命的高麗軍,面對這支軍政勢力,一籌莫展。
汗國正想取代金朝控制高麗,此際便以追殲契丹叛軍為藉口,遣元帥哈真率蒙古軍、東真軍和留哥軍於1218年冬進入高麗。哈真致高麗諜:“皇帝(指成吉思汗)以契丹兵逃在爾國,於今三年未能掃滅,故遣兵討之。爾國惟資糧是助,無致欠顏。”契丹軍內部矛盾重重,互相殘殺,削弱實力。汗國聯軍攻下許多據點,直指江東城。在高麗軍配合下進攻該城。翌年初,契丹將士及其家屬五萬餘開城降,平定了這支契丹勢力。
當時汗國主力軍正準備西征,無暇顧及高麗。哈真與高麗軍首領趙真等結盟:“兩國永為兄弟,萬世子孫無忘今日。”高麗“請歲輸貢賦”,汗國答應“每歲可遣使十人入貢”。隨之汗國撤軍。汗國在高麗的這一軍事行動,既消滅契丹反蒙殘餘,又取得高麗臣服,可謂雙收。汗國與高麗初步建立外交關係,不平等性非常明顯。
第一次徵高麗
汗國督索貢賦量大而又苛刻,並且沒有回賜,實是掠奪。同時,東夏也插手高麗,與汗國爭利。高麗反感情緒日增。權臣崔怡主張增兵,加強防守以備蒙古汗國。汗國使者著古歟多次去高麗,辦理貢賦事宜。十九年(1224年)被殺於返歸途中。此際東夏國已與汗國絕好,企圖聯麗抗蒙,多方挑撥蒙麗關係。並在著古軟事件上製造假象,嫁禍高麗。汗國果真認定系高麗所為,隨斷絕國交。
7年後即窩闊臺大汗三年(1231年),命撤裡塔率兵徵高麗,以報殺使背約之仇。高麗在重臣崔瑀操縱下,政治腐敗,戰略失誤。汗國鐵蹄踏人高麗境,其麟州都領洪福源率所部投降。汗國軍攻佔鐵州(今鐵山)等許多城市,包圍開京,繼續南下,攻楊州、廣州等。雖取得很大進展,但在一些地區卻受高麗軍民頑強抵抗。金慶孫守靜州、崔椿命守慈州,都有應當肯定的戰跡。應特別提及的還是龜州之戰。汗國軍包圍龜州城(今大寧江上游),使用創車、大床、雲梯、砲車、地道等方法攻之,均被樸犀領導下的軍民打退。同時,多次拒絕勸降。一位身經百戰,年近七十的蒙古將領嘆曰:“吾結髮從軍,歷觀天下城池攻戰之狀,未曾見被攻如此而終不降者。”
汗國畢竟具有強大的軍事潛力,高麗在其連續打擊下,何能招架!其王高宗屢遣使請降,撤裡塔允之。在京府等重要地區置達魯花赤72人監之。達魯花赤,蒙古語,監督官,但掌握實際權力。次年五月,撤軍。
第二次徵高前
武臣崔瑀深知,若蒙麗議和維持下去,王室與汗國將進一步結合,進而必然排斥自己,則崔氏專權難以繼續。於是挾持國王和群臣遷都江華島以避。在江華島修築兩道城牆,加強防衛,又建宮殿以供享樂。是時,汗國無專業水軍,不善水戰。在這裡,高麗可揚長避短。於是江華島就成為崔氏專權下高麗的臨時首都。同時,利用人們對達魯花赤的不滿情緒而殺之,以消除汗國對高麗的統治勢力。
非常明顯,遷都海島是對抗汗國的重要手段,殺達魯花赤系對汗國的直接宣戰。意味高麗方面撕毀和約。1232年年底,窩闊臺大汗命撤裡塔再徵高麗。汗國軍陷開城、漢陽等,但對臨時首都江華島未敢輕易觸動。同時遣使責高麗背約,要求棄島上陸。正值此際,在水州處仁城戰鬥中,高麗金允侯射殺撤裡塔。汗國軍主帥死,軍心亂,遂回師。高麗抗蒙派大振,對主張投降汗國一派進行清肅、整治。
第三次徵高麗
汗國於1233年亡東夏,擒萬奴;1234年滅金朝,統一北部中國。隨之便抽出精力,於1235年派唐古、洪福源率兵徵高麗。數年間,汗國騎兵從北到南,幾乎踏遍高麗。偏安於江華島的高麗政府不斷遣使乞降。汗國堅持的條件可歸納為二:出水就陸即首都從江華島回到開京;國王親赴汗國朝覲。從當時言,哪一條高麗都做不到。戰爭延續下去。1238年底高麗遣使到汗國上表,承認錯誤,願“僻陋之小邦……庇依於大國”,深表“誠服”,“通和”,甚至稱大汗為“君父”。翌年汗國撤軍。
汗國仍堅持上述要求,雙方使節往來穿梭,時有小規模衝突。高麗經長時間計議,於十三年(1241年)四月決定“以族子永寧公綽稱為子,率衣冠弟子十人入蒙古,為禿魯花”。禿魯花,蒙古語,質子意。仍依前例,向汗國繳納貢賦。
第四次徵高麗
蒙古汗國大汗之位的繼承,不斷髮生問題。每當此際,都是蒙麗關係“寬鬆”之時,隨之高麗得以喘息。一旦大汗之位解決,雙方關係便緊張起來,不是遣使急催貢賦,就是發兵入境騷擾。1251年蒙哥取得大汗之位。翌年10月,命諸王也古徵高麗,後來又調整、加強這支軍隊的領導班子。汗國堅決要求高麗政府“出水就陸”。作為人質的永寧公王綽隨軍而來,致函權臣崔沆:“今,國之安危在此一舉。若上不出迎,須令太子或安慶公出迎,則必退兵。”高麗王在權臣崔沆控制下,迴避汗國要求,堅持對方先撤兵。雙方僵持不下。
汗國軍佔領許多州城,掠奪財富、人口。但在忠州受到高麗軍民頑強抵抗,圍攻70餘日不下,負責守衛該州城者就是二徵高麗時射殺汗國軍統帥撤裡塔的金允侯。是時,允侯激勵將士:“若能效力,無貴賤悉除官爵。”當眾焚“官奴薄籍”即解放官奴,故“人皆效死赴敵”。
高麗國庫幾近空虛,無力支援戰爭。1253年高宗離江華島到對岸新宮,迎見汗國使者。同時派安慶公淚去蒙古,換得汗國於1254年初撤軍。
第五次徵高朋
高麗政府並沒有“出水就陸”,其王也沒有朝覲汗國。這是1254年7月汗國以車羅大為主帥第五次徵高麗的主要原因。此外,又增加兩個原因:掌權者崔流、李應烈等一直“不出面”.不是“真降”;高麗政府“責誅”降蒙官員王徽、趙邦彥、鄭臣旦等。更不是真心求和的態度。
當時,高麗看不起蒙古,常稱蒙古為“醜虜”。1254年安慶公淚出使汗國歸來,不願立即拜見父王高宗,因為“久染腥羶之臭,請經宿進見。”高王曰:“悉焚爾所著衣,更衣即來。”這父子兩人輕視蒙古的心態實是有些過分。如此,何能真心求和。並且又公開承認:“我朝之與〔汗國〕好,非必出於本意。”
汗國軍指揮部屯駐開京附近。雖在忠州山城、尚州山城等連續受挫,但仍繼續南下,殺掠人口財物。高麗用大量財物賄賂汗國軍將,求其手下留情和撤軍,何能奏效!“一年之間,死莩已滿於閶巷”。當年“蒙兵所虜男女無慮二十萬六千八百餘人,殺戮者不可勝計。所經州郡皆為煨燼。自有蒙兵之亂,未有甚於餘此時也”。翌年正月,車羅大退兵。其因不清。
第六次徵高麗
汗國撤兵後,國王與權臣們“宴於內殿作樂,徹夜而罷”。平日“剝民橫斂……民甚苦之”。為此民“反喜蒙兵之至”。1255年“京城大疫”,患病死亡者日多。這夥決策者,既不知自強,又拿不出對付汗國的策略。仍舊燒香拜佛,求其保佑。
汗國對高麗的消極、拖延的辦法,允諾、反覆的態度,極為惱火。於是蒙哥大汗五年(1255年)八月,車羅大率兵再次徵高麗。
人質永寧公王和洪福源等隨軍而來。汗國騎兵深入半島南端,繼續打擊高麗有生力量。陷忠州,屠城;在笠原出城受挫。是時,汗國除善用騎兵外,還積極造船,準備進行水戰。高麗多遣使賄賂將領,並求和。車羅大言:“若國王出迎使者,王太子親朝帝所,兵可罷還,否則以何辭而退乎!”1256年8月,來到江華島對岸,“大張旗幟,牧馬于田,登通津山,望江都,退屯守安縣”。似有渡海攻江都之勢。幸好大汗令其班師,9月車羅大收軍北還。
第七次徵高麗
1257年正月,在權臣崔沆控制下,高麗“宰樞議,以蒙國連歲加兵,〔我們〕竭力事之,無益,停春例進奉”。無疑是對抗汗國的行為,很可能成為汗國第七次徵高麗的直接理由。是年5月車羅大又率兵進入高麗境,駐安北府(安州)。是次,對汗國軍紀有所約束,“禁侵柔禾穀”,又招回南下的汗國軍。對此,國王和永安公信均表示滿意。車羅大再次伸述:“王若親來,我即回兵;又令王子入朝,永無後患。”高麗百般周旋,盡力款待,然而仍遲遲不敢邁出這兩步。許多朝臣對既不真心和,又不盡力戰的憂心仲忡,寡斷不謀的做法頗反感。甚至連宰樞都公開表示“請遣太子以活民命”。對此,國王一方面受權臣控制,另一方面連自己也猶豫起來。不久,車羅大受命退兵,駐電鹽城(黃海道延安),以觀動靜。
雙方的沉思1211年在通州,汗國軍射殺高麗赴金朝的回謝使,雖系雙方最早接觸,但純屬個別、偶發性事件。1218年汗國軍踏入高麗,旨在追殲反對汗國的契丹等殘餘,並非打擊高麗。真正征伐高麗的戰爭,應從1231年開始。在其後27年中,小的衝突不算其內,頗具規模的征戰多達7次。毫無疑問,就整體性質言,均屬不正義戰爭。隨著戰爭程序,雙方均有需要沉思的事情。
蒙古汗國不僅要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而且還要建立天朝體系秩序。這種對內、對外的計劃,隨著事業的擴大越發堅定不移。為此,從地理位置言逐漸感到朝鮮半島的重要性。隔海,與南宋相望,狹窄的對馬海峽,連線日本。特別是半島南端的濟州島即“耽羅,海道往南宋、日本甚易”,“於宋得便風可三日而至,日本則朝發而夕至”。汗國將南宋、日本均列為下一步重點拓展、征服的物件。防止高麗與南宋、日本暗通,阻止東北亞地區締結反對汗國的聯盟是必要的。然而更重要的還是將高麗作為徵日本、南宋所需人力、物力的供應地和戰爭基地。解決高麗,不只是高麗問題,而且與其後兩個戰略目標緊緊相連繫。在這種情況下,汗國對高麗寧肯投人、耗費相當的人力和物力,也決不放手。
高麗雖是小國,但多山傍海,故而山城體系較明顯,海洋文化較突出,又民風既柔且剛,具有許多特點。驍勇善戰的汗國騎兵在多山的高麗國度裡,其功能不可避免地遭到削弱。龜州之戰、慈州之戰、忠州之戰、處仁城之戰和笠巖山城之戰……反覆說明這一點。必要情況下,高麗政府還可躲進海島,這對不習水戰,更無海戰經驗的汗國騎兵是非常困難的。曾在亞歐大陸戰無不勝的蒙古汗國,在小國高麗雖取得許多戰役性勝利,但卻陷入泥潭數十年,並付出相當的代價,甚至連統帥都被擊斃。即使如此,也沒能很好解決高麗問題。汗國有識之士提出,真正征服高麗,談何容易!本文後面提及的趙良弼、廉希憲等人的議論,頗有代表性。再次證明,歷史並非完全按照強者的意圖發展,常常要受到弱者的影響。有鑑於此,汗國不能不沉思,對高麗僅用戰爭征服,武力統治等高壓手段是難以如願的。第七次徵高麗時,其統帥強調軍紀,約束某些軍事活動與此不能不有一定的關係。
高麗被迫進行數十年戰爭,再加上時而發生的自然災害、瘟疫等,致使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田園荒蕪,水利失修,人口流亡,“飢疫相仍,殭屍蔽路”,“死者暴形骸,生者為奴虜”。1259年遣太子倎一行40人去汗國奉表,連費用都不足,不得不採取如下措施,官員中“四品以上出銀各一斤,五品以下出布有差”,因馬匹“不足”,買“路人馬”充之。國庫枯竭、經濟崩潰並非虛言。山城體系對付騎兵,雖易守難攻,但只是消極保守的行為,何能支援曠日持久的戰爭!
長期以來,武臣專權,危害日重。他們收刮包括土地在內的豐厚財物,上下結成黨羽,豢養大量家兵,並且形成世襲。利用特權動輒誅殺大臣,甚至恣意廢立國王、太子,致使王權旁落。對此,國王無能為力。在武臣挾持下,偏居江華島已數十年之久。雖可避開一時之險,但總不是長久之計,何況汗國已注意造船技術和水上作戰訓練。在未來戰爭中,攻克江華島已不是不可能的。武臣跋扈已成為高麗王室心腹大患。是時,內政、外交已走上絕路:王氏高麗政權處在憂憂終日,發發可危的地步。面對這種情況,王室不能不考慮自身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