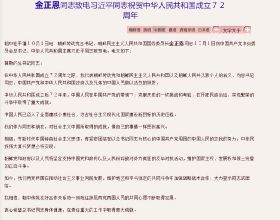3月6日晚,連隊為我們要復員的老兵開歡送會,也就是舉行晚宴。這頓晚宴將是我們在部隊的最後晚餐。
晚上,在連隊會議室裡用小凳子支了幾塊鋪板,上面擺上飯菜,飯菜很是豐盛,平時不擺的酒也上了餐桌。
所有復員的老兵和連隊幹部參加了歡送會。老奸巨滑的指導員讓連長主持會議,連長樂呵呵地登臺發表了演說。演說很簡短,也就是回顧了老兵們對連隊的貢獻,希望大家回到地方繼續發揚光榮傳統,做出更大貢獻。
連長講完,便開始喝酒。連長指導員和排長們,端著酒碗挨個為復員老兵們敬酒,楊平新等不走的老兵跟在他們身後。指導員很會自我保護,他知道這時候有些不滿的老兵會說些難聽話,甚至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來,這會使連隊的幹部們很尷尬和難堪。有不走的老兵護駕,即便有什麼不雅言行,能夠制止的也就是這些平時相處的老兵們了。會議室裡人聲鼎沸,指導員滿臉堆笑,嘻嘻哈哈地敬著酒,樂呵呵地與大家搭著話。

(1976年,仍留在連隊的老兵楊平新{右}和王建華在新疆奇台8847部隊農場。)
73年要走的兵沒多少,這些兵也老實,對幹部們構不成威脅,74年兵走的更少,好像只有師學友,所以74年兵更無從談起找事。最難對付的恐怕是我們這些71年兵,也就是常說的老兵油子了。因為走的人多,在部隊幹了5年,5年中的恩恩怨怨,愛恨情仇這時會毫不留情的爆發出來,所以連隊幹部們對我們格外客氣,生怕給他們鬧得下不了臺。
其實,對付這些老兵也很簡單,就是儘可能滿足他們的需求。指導員就能把握住這一點,你想入黨,就儘可能讓你入黨,只不過在早晚上為難你;你今年要走,就滿足你的要求,大意見沒有,也就沒了怨恨,所以那年我們這批兵走的很安分,沒有鬧事的。
幹部們敬酒完畢,歡送會開始。就是自己上臺表演節目,唱歌說笑話,什麼都行。來之前,我找到柳文軍,商量著我們兩個表演個節目,他說不會,我把要演的內容一說,他笑了,說願意配合我。這時,我們兩人登臺,我對大家說我和柳表演個魔術,外行看個熱鬧,內行別揭穿就行了。
大家鼓起掌來,楊平新喊道:“球,你還會表演魔術?從來沒見過。”王弟家咧咧嘴:“他又在說夢話哩。”
表演開始,我對柳說會氣功,一發功能將頭上的皮帽子頂起來。柳搖搖頭說你吹牛,我就裝模作樣地發力跺腳,滿身用力。果然,我頭頂上的皮帽子動了下,開始逐漸升高。頓時,臺下一片驚訝聲。
我一高興,反覆發力,讓頭頂上的帽子升升降降。指導員奇怪了:“三班長,你狗東西還會騙人這把戲。”一排長喝著酒,笑眯眯地看著我不說話。柳這時得意忘形,為表現自己,將我頭頂的帽子拿去,我這才原形畢露。
原來我身後的棉衣裡藏著一根小竹竿,從腦後伸進帽子裡,頂起帽子的秘密就在這裡。大家終於看到了秘密,轟地一聲哈哈大笑起來。柳在笑聲中跑了下去,我卻興致未滅,對臺下的周新慶喊道:“老周,上來為我伴奏,我要唱支歌。”
周新慶正在笑著喝酒,不願上臺來。他身邊的人將他推上臺,他把手中的笛子揮了揮,吹響了悠揚的曲調。
我記得那晚我唱的是電影《豔陽天》裡的主題歌,歌名是《長春歸來》:
燕山高又高,
金泉水長流,
群雁高飛頭雁領,
書記帶咱向前走。
貧下中農的主心骨,
敢鬥風浪的好帶頭。
和咱心貼心,
汗水往一塊流。
啊——
迎來豐收心歡暢,
爭得山河似錦繡。
唱完歌,回到酒桌前,與要走的、不走的開懷暢飲。
那晚,心裡有著說不出的滋味。五年來在連隊學習、訓練、生活;經過農場、奇台、烏魯木齊、西山;送走了一批批老兵,迎來了一批批新兵;要走了,對連隊突然充滿了情感和眷戀,心中難捨難分;部隊五年也使我厭倦了,老兵們都走了,感到很孤獨,思鄉心切,非常想早早離開連隊。
我的歌聲與魔術表演給會場帶來了歡樂與安詳,指導員李清林特別高興,端著酒碗滿臉菊笑地站到我面前:“三班長,你的魔術演的不錯,為啥以前藏而不露哩?”
我避而不答,也真誠地笑道:“我的歌唱的怎樣?”
知音者少,和音者寡。連長李文恭繃著臉,牛吃牡丹道:“好屁。難聽!”
指導員李清林開天闢地的挺身護我:“雖然四五處唱跑調了,但這歌我愛聽。唱的不錯。”已聽出韻味的指導員舉起端著的碗,朗朗道:“三班長,幹!”
我也舉起酒碗開天闢地地與指導員脆生生一碰,仰頭咕咚咚將碗裡的酒喝的乾乾淨淨。但我那時真的沒有料到,我這一次與指導員的喝酒,竟成了悲壯的訣別。
那晚,我在情感錯綜複雜中喝了不少酒,說了不少話,晚宴怎麼結束的、我怎麼回班裡睡覺的都記不得了。
那夜,是我在連隊睡的最後一個夜晚。覺睡得格外香甜!
第二天一早,廖清平將我推醒,我看看窗外的天,天空陰沉沉的。班裡的戰士們都在準備為我送行,我今天就要離開連隊了。
注:
附:

(2015年11月26日,在河南三門峽與戰友潘建中四十多年後重逢。)
謝謝你的閱讀和欣賞,敬請關注《綠色印痕》的下一章節:“告別連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