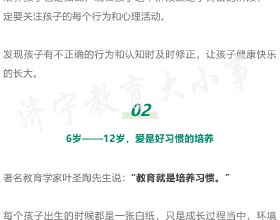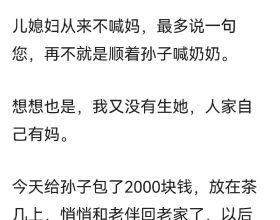古村和古村的面貌大致是相似的,立春那日,當我在瓦子峪鎮龍灣村那硬得像刀子一樣的山風裡遊走,腦海裡突然跳出的卻是京郊的爨底下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一些東西,可以互通有無,取其精華。雖塵封已久,但記憶猶新。古老的東西,能夠給人的便是千篇一律的懷舊吧。
某一年的春節,我是在爨底下村度過的,看過除夕夜晚古城牆上的繁星點點,看過初一早晨才躍出地平線的朝陽,聽過靜夜裡此起彼伏的犬吠聲,早晨在長長短短,深深淺淺的雞鳴中睜開惺忪的睡眼。
不回家過年的原因,是我的婚事成了父母的心病,他們並不像別的父母催命似的催婚,但是他們會在這個萬家團圓的節日裡黯然神傷,尤其是老爸,會一邊喝酒一邊掉淚。
而我是根本見不得那樣的場面的,或者說不回家,裝作看不見,繼續我的四海為家,閒雲野鶴。是有些自私吧,但我知道父母之深愛子,為之計深遠。然而,深遠這個東西,若你親眼見不到,未必真實,有些時候,親眼見了,也未必真實,不是嘛。
倒不如就在一個陌生的村落裡,面對一些陌生的面孔,他們會給你陌生而親切的笑,還有親切到骨子裡,妥帖著你的每一根神經的拉家常。
一個旅遊性的古村落,它的包容性是海納百川的,體現於沒有人問你,你去誰家呀,或者過年你怎麼不回家呀,父母不會惦記嘛。他們只會衝你淳樸地一笑,很自然,那自然裡面藏著的是一個歷史性古村落的文化自信,他們會發自肺腑地覺得,異鄉人,留在村子裡過年,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或者說是一件值得他們驕傲和自豪的事。
一樣的石頭牆,或者是泥巴牆,我偏愛上面經年的青苔,被風雨剝蝕到花白的青石,還有卷邊翹沿的老屋一角。
某一個瞬間,我是有些羨慕這隻小貓的,它趴在牆頭上,尾巴自然地耷拉下來,大橘色點綴著黑色的斑點,甚至臉部點綴得有點嚴重,像一個生而帶來的胎記,但是那沒有妨礙它展示自己的美,安靜地,自信地,面對著扛著相機咔嚓半天的我。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古村落,並不是簡單的古老,它的古老除了歷史的悠久,常常還伴隨著文化底蘊的深厚。在那個村子裡,你隨處的轉角,抬頭的一瞥,每一個弄堂的盡頭,哪一家的影壁,或者簡單的牆頭牆根,都能瞥見文化的影子。無處不在地提醒著你,這裡,曾是貴族權勢的聚集點,曾是聲噪一時的官宦人家聚居所。
腳踏車,馬燈,流轉著童年的縮影。牆壁上的斑駁陸離,卻是印證著日子的歷久彌新。我與清風皆過客,你攜秋水攬星河,有一些邂逅,本就是五百次回眸換來的一次擦肩而已。所以,如清風般灑脫,才可能在秋水入眸中燦如星河。
骨子裡固執地喜歡一些老舊的東西,似乎是它經歷了我所未曾經歷的,它記載了我未曾知曉的,也或許將見證我無法見證的。那樣神秘且無垠的存在,總會在一瞬間觸發我的思緒萬千,一發不可收拾地傾瀉於一輪明月之下。
不說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主人家出門就是簡單地在門鼻子上插一根小樹枝,不管是財主家還是福祿壽家,都是開門納客,喜迎四海賓朋。他們沒有謝客過年的說法,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有客人,便是最好的年。
爨底下村位於北京西郊門頭溝區齋堂鎮,川底下村,實名爨底下。因在明代“爨裡安口”(當地人稱爨頭)下方得名,大部分為清後期所建(少量建於民國時期)的四合院、三合院。依山而建,依勢而就,高低錯落,以村後龍頭為圓心,南北為軸線呈扇面形展於兩側。爨底下村的弓形牆圍繞,使全村形不散而神更聚,三條通道慣穿上下,而更具防洪、防匪之功能。
爨(cuàn)是漢語二級通用字 ,此字最早見於戰國 ,古字形上部模擬雙手拿著甑,中間是灶口,下部表示用雙手將木柴推進灶口。本義指燒火做飯。村民將爨編成順口溜:興字頭,林字腰,大字下面加火燒。大火燒林,越燒越興,豈不很熱,而爨底下人全姓韓,取諧音(寒)則為冷意,冷與熱在五行之中可以互補。直白地說,就是大鍋底下的村子。人間煙火味,最撫凡人心,爨底下寓意著農家日子的紅紅火火,興旺累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