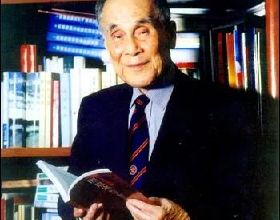國學成語,濃縮歷史精華;曲徑通幽,遇見不一樣的“中國”。
引子:曹操
這裡要說的是中國古代的一個人物——曹操。
曹操被稱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他起於亂世之中,透過大力延攬人才,挾天子以令諸侯,將袁紹、袁術、劉表等封建割據軍閥一一平定,並降服南匈奴、烏桓、鮮卑等邊境隱患,統一了北方,讓曾經“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中原地帶再次雞犬之聲相聞,人民安居樂業,可謂功高蓋世。以至於他曾經自負地說:“念自討董卓,剿黃巾以來,除袁術、破呂布、滅袁紹、定劉表,遂平天下……如國家無孤一人,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但是壞就壞在他挾天子以令諸侯,壞了“政治規矩”,而且不止一次赤裸裸地干涉別國內政,所以千百年來被人罵來罵去,動輒以“賊”稱呼,反倒是那個佔了人家荊州不還,跑到西川不走的著名“老賴”劉備成了大好人。
平心而論,曹操是有點冤,但也不算太冤。所謂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行高於眾,人必非之”,做事多了,難免犯錯多,當然捱罵就多。
一個人如此,一個國家也是如此。就拿咱們一而再再而三提及的“春秋五霸”來說,他們之所以被周王室和各諸侯國認可,成為“帶頭大哥”,除了國力雄厚之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關鍵時刻捨得出錢出力、主持正義,甚至保全了一個又一個面臨生死存亡的國家,讓這些國家的國民重新過上了正常人的日子。但是時人和後人在評價他們時同樣褒貶不一,甚至罵得厲害。
一人難趁百人意,大概就是說的這種情形吧。
前文不止一次說過,春秋時期的小國活得很可憐,因為它們國力弱小,不得不在列強的夾縫裡求生存,幾乎整日過著戰戰兢兢、朝不保夕的生活。而《左傳》顯然也注意到了小國寡民的不容易,並透過一封發自鄭國的“外交郵件”,給我們做了形象展示。
故事發生在公元前609年夏季四月的一天。這天晉國的國君晉靈公夷皋在黃父練兵,並在扈地會和諸侯,與剛剛發生了弒君之亂的宋國簽訂和平條約。
但是,晉靈公拒絕會見鄭穆公,認為他背叛晉國而投靠楚國。看到自己被“帶頭大哥”冷落,執政大臣子家(就是成語食指大動裡提及的歸生)很憂慮,為緩和與晉國的關係,子家就派通訊使者去晉國,給執政大臣趙盾送了一封信,當然啦,信名義上是寫給國君夷皋的,但能拍板的,卻是趙盾。
信寫得言辭懇切、充滿委屈,又軟中帶硬,因此這封信的效果很好,不僅使鄭國和晉國修復了關係,還簽訂了長期友好合作條約。所以,弱國無外交是相對的,除了國家本身有實力做後盾外,關鍵還要有外交人才,否則好事可能辦砸。
信中說:我們國君繼位三年,叫上蔡國國君一起事奉貴國君主。九月份時,蔡國國君從我們這裡去貴國“訪問”,本來我們國君也要去的,由於發生了內亂沒有成行。但是到了十一月份,內亂平息後,我們國君立即和蔡侯去貴國朝覲。這三四年來,我們國君和大臣們一直沒有間斷去貴國朝見。
還有,陳、蔡兩國與楚國接壤但是對晉國沒有二心,還不是因為我們鄭國在裡面起了重要作用?為什麼我們這樣侍奉貴國君主,反倒不能免於禍患呢?
我們國君在位時,曾經一次朝覲先君襄公、兩次朝見現在的君主,我和幾位大臣也緊隨著到絳城朝拜。我們鄭國雖然是小國,但也沒有比我們更有誠意的了。如今大國說:“你沒有讓我稱心如意,”那麼我們大不了只有等待滅亡,也不會再增加什麼(災禍)了。
古人說得好:“畏首畏尾,剩下的身子還有多少?”又說:“鹿要死的時候,顧不上選擇蔭庇的地方”。小國事奉大國,如果大國以德相待,那麼小國就以人道相奉,否則,小國就會像要死的鹿一樣鋌而走險,哪裡還顧得上選擇地方?現在貴國的命令沒有止境,我們也要滅亡了,只好派出傾國之兵等待貴國前來。何去何從,你們就看著辦吧。
還有,我們在(鄭)文公二年曾到齊國朝見,四年二月,也曾因為齊國攻打蔡國,和楚國講和。處在齊、楚兩個大國之間而屈從於強國的命令,難道是我們的罪過嗎?如果大國不加以諒解,我們沒有地方逃避了。

信的大體意思就這些,信雖然不長,但饒是現在看來,信寫得也很有水平,可謂有理有據有節,即表達了對晉國的必要的尊重,給足了面子,又軟中帶硬地指出,如果晉國欺人太甚,我們鄭國將不再畏首畏尾,而是要鋌而走險,出動傾國之兵嚴陣以待,與晉國拼個魚死網破。
此外,信件還特地指出,我們此前已經和齊國和楚國簽訂了和平條約。這幾句話的潛臺詞是,我們鄭國還有別的靠山。你真要來進攻我們,他們不會坐視不理。
趙盾也非凡品。所以在讀完子家的信後,特地派大夫鞏朔到鄭國講和修好,而且還派出自己家族的“要員”趙穿和晉靈公的女婿池到鄭國做了人質。
人們常說,弱國無外交,但這並不是絕對的,筆者以為,這是在毫無規則的叢林社會才有的現象。尤其是現在,國際社會中政治和經濟執行規則已基本成熟,靠武力打天下已經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還有國家不論大小,如果被很多國家怒懟,肯定是有欠收拾的地方,這和小混混讓人討厭一個道理。
國學經典欣賞:
晉侯合諸侯於扈,平宋也。
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
“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chan,完成)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
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tiao,地名),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朝於齊;四年,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有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
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婿池為質焉。
——《左傳•文公十七年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