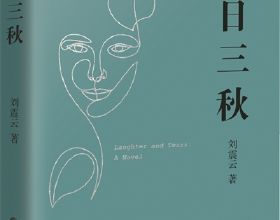《三打白骨精》,關良,1978年,中國畫,179cm×96cm,廣東美術館藏。

《武劇人物》,關良,1960年,46.5cm×35cm,紙本水墨設色。
關良(1900—1986),字良公,生於廣東番禺,中國近現代畫壇上一位不可或缺的大師。其一生的藝術軌跡由中西兩條線交織而成,西方現代藝術的傳播耕耘和中國傳統水墨畫的創新並重。20世紀初期,大批留日、留法畫家歸國是西方現代藝術在中國的濫觴。在此環境中的關良,用其西畫學習的背景成為西方現代藝術在中國傳播最早的播撒者之一。在中國畫的變革大潮中,關良融西學而內化,又在水墨畫中探索出一條簡拙至美的戲曲水墨畫之路。
近日,“遊藝東西:關良的風格史研究”在廣東美術館展出。展覽以“影象證史”為研究方法,深入以關良為核心的個案研究,以關良及其友人的作品、文章、歷史文獻、照片等資料,串聯整個展覽的大事記。
本次展覽是文化和旅遊部2021年全國美術館館藏精品展出季的展覽專案之一,展覽由廣東美術館自主策劃,廣東美術館館長王紹強擔任策展人。“這是廣東美術館歷年來難度最大的展覽之一,關於關良長期以來沒有一個系統性的課題展,廣東收藏的關良作品也不多,很多材料缺失,難度很大。”策展人王紹強館長說。
20世紀以來廣東美術走在全國前列,從油畫、新興木刻、近現代美術到廣東國畫改革,許多藝術思潮從這裡發起。2017年,廣東美術館舉辦“廣東美術百年大展”,關良位列21位大家之一。2020年是關良誕辰120週年,廣東美術館的策展團隊開始計劃籌備,對關良的整個藝術脈絡進行系統梳理。本次展覽的策展團隊之一,廣東美術館展覽設計部副主任武鵬飛介紹,過往公眾對於關良的認識存在標籤化,討論集中在他的戲曲畫,今人討論關良的藝術,更多地看到他帶來了“戲曲入畫”這樣一個新題材,除此之外,還要用一個歷史的眼光去看待關良,去看待關良風格史的構建。
“關良是很立體、很豐富的一個人。他不僅僅在作品的風格語言上足夠深入地打通了中西脈絡,而且他的輻射面足夠廣,他的整個藝術生涯和音樂圈、文學圈、戲曲圈都有很豐富的聯絡。這次展覽的作品覆蓋了關良的每一個時期的藝術的面貌,可以說是最豐富、最完整的一次呈現。”武鵬飛說。
關良早期學習西畫,痴迷水墨、戲曲、文學、音樂,擁有非常全面的知識結構,他在教學的同時廣交朋友,在他身上,有著廣東人開放、包容、不斷進取改革的精神和性格,這些在關良的藝術生涯裡體現得淋漓盡致。
王紹強本人也是關良的粉絲。他說,希望透過本次展覽,更多美術院校、年輕學者加入關良的研究,讓廣東觀眾更多認識關良,“他是廣東近現代美術史上非常值得我們驕傲的一位藝術家。作為20世紀初最早的一批留洋畫家,關良從西方繪畫裡吸取養分,與中國傳統藝術結合,他應該作為當下文化自信的代表更多地被人認識。”
改良思潮下的“洋畫家”
1918年5月14日,剛從日本歸國的徐悲鴻以《中國畫改良之方法》為題在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上發表演講。他所謂的改良之法,在於對古法和西方畫之揚棄,即“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絕者繼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畫之可採入者融之。”
當然,肇始於19世紀中葉的改良主義,絕非僅限於繪畫與戲曲等藝術門類,這種思想幾乎輻射到了整個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留日的關良也投身於學習西方繪畫的行列之中。他求教於日本畫家藤島武二和中村不折,系統地學習了西洋畫和素描;留日期間,又學習了小提琴,使得關良對西方音樂、藝術見解獨到;作為資深的票友,關良自幼嗜好皮黃,老生戲尤其唱得爐火純青,又拉得一手嫻熟的二胡,實可謂是最通“戲”的畫家。
此時的關良作為一個東渡日本學習西洋畫的藝術家,他看待西洋的藝術,看待本民族的傳統,很有獨到的見解:“我們學習外國的藝術,主要也是學習一些基礎知識,關鍵是創造自己的表現形式。即使運用外國的工具和某些技法,來表現我們民族的思想、感情、愛好的東西,也要令人一看就是中國的。油畫也是這樣,應具有中國民族的風格和氣派,比之外國的油畫作品,要並不遜色,要各有千秋,要有過之而無不及。”
從日本學畫歸國之後,關良在藝術學校教授西洋畫、水彩、素描、油畫,並沒有去教中國畫、水墨戲曲畫。在當時的他看來,這些都只是本業之外的興趣愛好,並不成系統。此時,媒體也好,藝術界也罷,認識關良首先是從其“洋畫家”的身份開始的。
在展覽的第一板塊“改良思潮下的‘洋畫家’”(1900-1949),觀眾會見識到關良對西洋繪畫的造型能力和基礎知識之紮實。展覽中有一張黃少強先生的肖像,這件作品用極為簡練的筆墨去描繪,盡顯功底,“他的造型功力極強,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他才能夠進行自己的所謂的改良和創作。”武鵬飛說。
時代塑造的“國畫家”
1949年7月,新中國成立前夕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上進一步確立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思想作為新中國文藝的指導方針,同時強調該指導對新中國美術創作的重要性。對此,美術工作者作出積極響應,1950年《人民美術》(《美術》雜誌的前身)在創刊號開始關注國畫創新問題,李可染、李樺、洪毅然等對於國畫如何在思想、內容和形式上進行改造創新更好地為新時代服務展開討論。
此時,關良在浙江美術學院擔任西畫系基礎教學的同時,在自己的繪畫實踐中則繼續嘗試各種新的不同表現方法,在油畫、國畫這兩種不同媒介之間持續滑動。其間創作的戲劇人物畫,也在早期淡彩水墨的畫法基礎上,融以西畫的用色技法,摻以國畫遲滯、遊移的線條,造型上以簡代繁,形成具有“稚拙、率真”,“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特點。
早在1942年,關良的這種融合了東西文化的現代繪畫形式,已在戰時陪都重慶獲得文藝界領袖郭沫若的肯定與讚賞,認為其發揚了中國作風,中國氣派,是具有“民族特徵”的繪畫形式。新中國成立初期,在美術領域倡導國畫改造和油畫民族性的時代背景下,關良戲劇水墨人物畫所體現的創新性和民族性特徵,為其在中國畫領域積累了名聲和讚譽。
1957年,文化部與東德簽訂中德文化交流協議,在東德舉辦中國展覽會,關良和李可染作為代表團成員赴德參加開幕式,東德出版社為其編選出版德文版的京劇人物畫冊,繼齊白石之後入選該公司《世界美術》叢書系列。從此,關良“國畫家”的形象已逐漸蓋過了他“洋畫家”的本業。1960年開始,關良供職於上海中國畫院,以這種非寫實主義的繪畫實踐耕耘創作。展覽的第二板塊“時代塑造的國畫家”,著重勾勒出關良86載的藝術人生與時代的緊密聯絡。
武鵬飛介紹說,當國家有文化輸出、文化宣傳的需要時,關良拿出來的水墨戲曲畫題材正好是我們的國粹京劇,成為我們宣傳國粹的一個很好的路徑。
戲曲入畫,點睛之筆
戲曲畫古已有之,但地位非常低,很多大畫家不屑為之。關良愛戲,也在不斷思考如何將戲曲入畫。
在專業人士看來,關良的戲畫“很準”“很懂”,初看似不經意,像隨筆揮寫,實則賦神於形,形神兼備,堪稱絕技。這得益於他對戲曲的訓練。
關良不僅是一個戲曲愛好者,甚至是一個戲曲方面的專家。從小父親就帶著他去戲院聽戲,耳濡目染,從小就浸淫在戲曲、皮黃的世界裡。除了愛戲,他還學戲,拉二胡,曾經系統地學習過老生戲,《捉放曹》《失空斬》都能整段地自拉自唱。
關良認為,京劇動作一舉一動含有歌舞奏態,變化極快,作品不容許從容地去描寫。作畫時必須先起一個完整的腹稿,如果對被描寫的物件沒有極透徹細緻的理解和敏感性,就不可能把京劇的神采傳達出來。也就是說,每一幅作品都應該是長期觀察、領會和思索後,所得的產物。
細心的觀眾還會發現,關良的戲畫,以武戲居多,主要呈現武打、運動的場面。戲曲畫描繪靜態動作不難,描繪動態卻很難。武鵬飛說:“我們知道戲曲演員登臺亮相是:崩、登、倉,到倉的時候,演員就定了睛,底下觀眾拍手叫好。但是關良畫戲呢,就不到倉,通常在崩和登的時候就落筆了,這正是打鬥動作最激烈的時候。你會發現他的畫面非常生動,能夠把戲曲中的緊張感留到紙面上。他其實也回答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也就是戲曲如何入畫,他找到了一個非常好的路徑,這些都源自他有自己獨到的戲曲訓練。”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關良的戲畫更加爐火純青、遊刃有餘,進入到了一個全新的境界。戲曲演員特別講究眼神,關良的點睛之筆,從上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以至於70、80年代,都有風格上的變化演繹。他的點睛之筆也開始更加有“戲味”。
關良的點睛之筆,如同蓋叫天的戲,講究眼神的運用:瞪、瞟、掃。當這些在京劇裡的功力轉嫁為影象語言的時候,關良的戲畫藝術層次又上升了,從早期典型的“芝麻點”眼神,到《武松打虎》裡武松的眼神,都是他的精心設計。
關良作畫,往往最後才畫眼睛。他說:“眸子兩點,焦墨一戳,看來全不費功夫,卻是精心之極的一筆。有時我把畫好的一幅畫稿,高懸牆上,朝夕相對,斟酌再三,一旦成熟,即刻落筆,一揮而就。眼睛不僅反映著人物的動態、神態、情緒,而且更反映出戲劇在特定環境中的特定思想感情、氣質。”本次展覽中有兩張未點睛的“半完成作品”——《未點睛的貴妃醉酒》和《未點睛的武劇人物》,特別值得玩味。在關良看來,作品若是感情沒到位,就不點睛。可見關良對“點睛之筆”極其重視。
迴歸自我的“遊戲筆墨”
生於世紀之初、與二十世紀共同生長的關良,經歷時代的諸多變革。1977年後,此時遠離紛爭,迎來了平靜安逸的晚年生活。
晚年的關良,在藝術上更加豁達自由,更加遊刃有餘地去“玩弄”藝術。所以“遊戲筆墨”成了關良的一個藝術的新境界。恢復創作激情的良公拿起畫筆,一揮而就,以一幅《三打白骨精》開啟了他最後十年的創作高峰。
悟空戲在關良的創作列表裡佔據十分重要的比重。上世紀60年代,六齡童主演的《孫悟空三打白骨精》技驚四座,毛澤東主席觀戲後寫下著名的“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的詩句。
關良對這齣戲也很有感覺,此後“三打白骨精”成為他時常描繪的場面。在展覽梳理的作品中,這個題材多次出現,而畫家對白骨精的姿態形象也經過了長時間推敲、研究,才最終確定。
廣東美術館館藏的這幅《孫悟空三打白骨精》是少見的大尺幅作品。關良讓悟空高高騰起,形成對白骨精的強烈壓迫感,整個畫面大開大合。這種上下的空間感在戲曲舞臺上是很難實現的,關良卻把它在畫上實現了。
晚年的良公心境更添閒適,在水墨戲曲畫創作領域遊刃有餘,形成了至簡至樸、拙趣遲重的風格。他筆下活靈活現的人物形象,精妙傳神的眼神刻畫,雖然大多是留白的背景,卻在他虛實相生的經營佈局下給人身臨其境之感。《捉放曹》《白蛇傳》《打漁殺家》……一出出好戲正在上演,已是耄耋之年的良公以老練的風格與純熟的筆墨功夫盡情揮灑,開始了迴歸自我的“遊戲筆墨”。
他不再討論古法與西洋、改良與創造,他的作品迴歸了一種本源的、天真爛漫的境界。正如遲軻對關良的評論:“關良藝術的稚拙之美所以親切宜人,在於他雖運盡匠心,卻毫無劍拔弩張,賣弄才華之意,在於大巧若拙、熟後轉生,在於‘百鍊鋼化繞指柔’。”
訪談
廣州文史學者、書法家吳瑾:關良的戲曲畫 本身就是時代精神的產物
吳子復先生(1899-1979)是廣州著名的篆刻家、書法家,他與關良是藝術上的知音,兩人有過半個多世紀的交往。據吳子復之子、文史學者和書法家吳瑾先生回憶:“父親與關良相識於二十世紀20年代中,其時關良留日歸來,先後在上海美專與廣州‘市美’任教,是父親的老師,其後兩人先後參加北伐。後來兩人又同在‘市美’任教。由於性格愛好相近,談得很投契。抗戰時期分開,一直都有通訊聯絡。”
在“遊藝東西:關良的風格史研究”大展舉辦之際,就關良研究等問題,吳瑾接受了南都記者的專訪。
南都:你幼時見過關良先生,有什麼印象呢?
吳瑾:在我印象中,良公話不多,總是笑眯眯,是個和藹慈祥的老人。我八歲那年就擁有了關良的一張畫,依稀記得畫的是一個黑麵將軍,據說是竇爾敦。妹妹也有一張,畫的是一個手舉茶杯托盤的小姑娘。兩張畫並排掛在我家客廳東北角壁上。
我還親眼目睹過良公作畫的全程,只見他略為審視一下宣紙,先用濃墨勾出人物面譜輪廓、依次畫眼鼻、須口、上衣等,再用淡墨寫手腳動態,然後上淡彩,眼睛是最後用焦墨小心翼翼地點上的。用筆緩慢悠然,筆筆全神貫注,沒有絲毫鬆懈。他絕沒有恃才傲物肆意猛戳的所謂名家氣派。
南都:作為廣東美術的重要人物,針對關良的研究其實並不多。你認為目前對關良研究有怎樣的認識?
吳瑾:我早兩天看了一個報道,說關良是一個玩家。今天我們說玩家好像很輕浮、“搞搞陣”。其實關先生的東西跨界跨得太厲害了,京劇、西洋畫、國畫、水墨畫、音樂……他集合得太豐富了,甚至他對石濤畫的鑑別也很精準。
今天我們對他的理解還很不夠,研究也不到位,也是因為他的跨界。來看展覽的一些觀眾可能看不明白,感覺他的畫好像每一張都差不多。其實就算一個美院畢業的人,你做不到關先生的跨界,你就沒有辦法完全理解他。比如你對京劇沒有了解,他的戲曲人物畫題字又比較少,形象很簡略,你怎麼能完全看懂呢。
還有一個現象,關良有很多張《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網上能搜出很多一樣的構圖,這反映什麼問題呢?關良的畫,筆墨不多,模仿的成本太低,沒有一定的眼光是分辨不出來的。
南都:關良的水墨戲曲人物畫,在20世紀中國繪畫史上留下別開生面的一頁。你認為關良的獨特性體現在哪裡?
吳瑾:他在中國美術史上是一個特例。你可以拿他跟丁衍庸比較一下,可以看出兩人的不同之處。丁衍庸的背景和他一樣,但是我個人認為,對丁衍庸的評價基本是沒有關良的高。丁衍庸的東西比較淺,他畫得飛快。李育中老先生曾對我回憶,在廣州解放的前一天,丁衍庸的教室裡滿地都是他的畫,誰要就誰拿。
而關先生不是這樣的,每張畫之前他都有一段深思熟慮的思考,然後再下筆。他用筆很微妙,作品量並不很多,到後來80年代才多一些。至於他對後世的影響,按照目前藝術評論界的看法,韓羽、朱新建等畫家都多多少少受他的影響。
南都:對關良作品的評價,是否經歷過一個變化的過程?有批評說在風雨飄搖的近現代中國社會,關良的畫缺少了“時代意識”,對此你怎麼看?
吳瑾:這是藝術家的個人選擇問題,不一定非要在畫面上顯示激烈的東西。他本人參加北伐做宣傳工作,而不是躲在家裡畫畫,這本身在行為上就是一個時代的反映。抗日戰爭時期,他在成都、重慶開畫展、募捐,也在用自己的藝術品參與時代,不是直接畫槍畫炮才叫有時代意識。他用現代藝術觀念來表現京劇藝術,本身就是時代性的體現。京劇以前沒人敢這樣畫的,他就敢這樣畫,這和他對現代藝術、對時代的理解有很密切的關係。
筆墨,必須為表現劇中人物服務,與劇情、人物相配合,決不能單純地追求“筆情墨趣”,而玩弄筆墨,只有筆墨為作品的主題服務成功了,筆墨也才有感人的藝術效果,也才有一種雋永、含蓄,蘊藉風流的韻味。 ——關良
專題採寫:南都記者 朱蓉婷 實習生 陸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