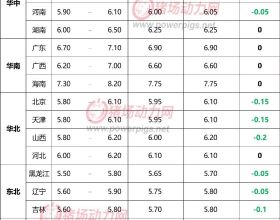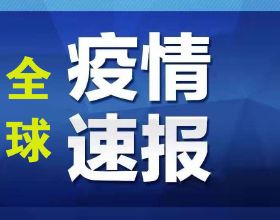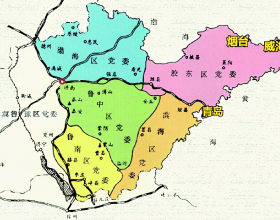歷史固然不能割裂,但並不意味著不能進行總結性對比。然而需要釐清的是:對比不是為了否定什麼,而是要總結成績,修正不足,促進發展。
鑑於今昔在發展方略上存在著一些差異,因此對比總結似乎意義更大。
基於曾經發表過很多相關方面文章的原因,今天發文,旨在釐清一些被混淆的事實。
首先當年實行的是“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
現在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經濟形式。差別顯而易見。
其次,當年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
如今則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第三,當年沒有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而如今卻在踐行著這一國策。
第四:當年奉行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基本方針;
而如今選擇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同時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科學論斷。
以上種種差別,現實存在吧?
然而,展示這些差異,並非為了展示而展示。而是為了求證一些被歪曲的事實。
儘管,對改開以來中國社會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業已達成了社會共識,但仍有部分人只是承認這一事實的結果,不認為這是開改之功,而是認為完全取決於當年艱苦奮鬥打下的基礎。這讓人不禁發問:難道以上種種改變,沒有貢獻?
對於這種無視改革而發生改變之事實的論調,我甚是不以為然。特別是那種“沒有過去基礎,絕對不會有今天改開成就的極端論調,更是不屑。
他們的根本謬誤在於:
一方面無限放大基礎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卻在不遺餘力地突出著如何在“一窮二白”中“白手起家,”創造了當年的輝煌。
我不知道,這是想要證明基礎重要性,還是不重要呢?
實事求是講:當年儘管不是“白手起家”,基礎十分薄弱卻是不爭事實。同時創造了不凡成就,也不可否認。基於這一事實,我們是不是可以推匯出這樣的正確結論—-基礎固然有用,但絕非不可或缺;
同時,客觀講:當年的歷史成績固然不凡,但與改開相比,確實差距不小;
就GDP而言,78年GDP總量是3678億人民幣,人均385元(是當年人口9.6億人的平均水平);世界排名:總量第11位,人均134位;當年世界人均水平約5000多人民幣,是我們的13倍;而日本以人均8800多美元(當時實際匯率大約是2.4人民幣)位居世界第22位;大約是我們的56倍;即便沙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人均也達到496美元,是我們的3倍多。
而如今,總量17.72萬億美元,排名第二,人均1.25萬美元(這可是14.42億人的平均水平),排名升至63位;欣喜的是人均超越世界1.2萬美元的平均水平。而曾經是我們人均56倍的日本,現在卻不足4倍。非洲國家就不必浪費筆墨了。
第二:糧食產量:78年是3.04億噸,人均佔有量317公斤(9.6億人計);
現在:總產6.8億噸,人均(按14.2億人計)474公斤;遠超國際公認的400公斤糧食安全標準線。
針對網上部分人不認可吃飽飯是改革之功的說法,這裡做個簡單了論述。
首先:是49年一52年,當時土地歸農民所有,完全實現自主經營,在沒有良種化肥、農藥、節水灌溉等先進農技措施的情況下,糧食平均增長率連續幾年都超過10%以上;特別是50年,達到了建國以來最高的14.6%。
其次:實行包產到戶僅僅兩三年,就破解了困擾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不得飽食的困境,不能不說是功惠千秋的偉大成就;有的地方甚至當年實現飽食;客觀講,當時各項先進農技措方始未興,就全國而言,應用範圍有限;主要是理順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關係,提高了生產力發展水平—-人的主觀能動性得以有效釋放;
再次之:在一定條件下,萬物皆有極限;人的主觀能動性亦然;在現有條件下,特別是科技水平和投入水平的限制,人的主觀能動性已發揮到極致,紅利基本釋放殆盡,因此後期出現了瓶頸;好在科技措施的不斷增加和完善,彌補這一缺陷;客觀講後期糧食增產,是人性激勵機制和科技廣泛應用疊加的結果。然而,科技之所以進步,也是得益於:在“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學論斷影響下的、尊重知識和重視人才的結果;歸根結底是改開紅利蓬勃釋放的結果。
第三,工業增加值:78年工業增加值為1622億,而2020年達到30多萬億,按不變價格計算,增加了56倍,年均增長10.7%;確實難能可貴。眾所周知,正常情況下,基數越大,增長幅度提升會越難,甚至無法保持原有增長速度;但同樣增長率,增量不盡相同;基數大,無疑增量多。
最後,全國居民人均收入:全國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從1978年的171元增加到2020年的32189元。剔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22倍。城鄉居民恩格爾係數分別從1978年的57.5%、67.7%下降到2020年的29.2%、32.7%,意味著,除去必要生活開支,增加了更多自由支配資金。
同時,既然當年沒有多少基礎也能創造卓越成就,那麼改開又何嘗不能呢?更為重要的是:事實證明了基礎並非不可或缺;而一系例改革措施卻是缺一不可,是改開取得巨大成功的、主要推動力和貢獻者。
同時,針對一些創作者客觀再現歷史苦難文章,總是無一例外地送上抹黑中傷的歷史虛無主義帽子;那麼那些一味謳歌,卻對曾經客觀存在的歷史不足,隻字不提的言論,是不是也是人為美飾的歷史虛無主義呢?甚至上升到情懷和道德層面加以邦架。無論真假對錯,只要是苦口的,便是不愛的。反之亦然。孰不知,如此作為,不僅有失公允,而且極不道德。
甚至在辨無可辨情形下,競然丟擲“怎麼也比舊社會強”的論調;事實上,強是正常,不如則是倒退,用一個長相不錯的與一個醜陋不堪的進行比較,意義很大嗎?這一論調尚不足以成為證據支撐。因為,社會不斷進步,是社會規律運動的自然過程,憑慣性前進的也不在少數。
同時,在這一群體中,極可能存在著部分在文革時期十分活躍的人;他們作為根正苗紅的執行層面主體,人為製造了太多的傷痕。客觀講:藉著大勢,他們既是傷痕發明創造者,也是踐行者;然而就是這樣一群創造傷痕,強加於人,施暴傷人同時,意得志滿的人,卻是站據道德高地,抗著正義大旗,阻礙重現歷史,無情打擊著受傷者。何其荒唐?或許正是因為他們害怕過住陋行、在歷史重現中會裸色呈現,才極力阻撓和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