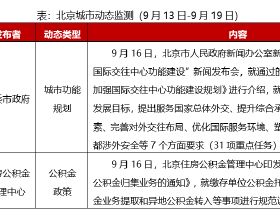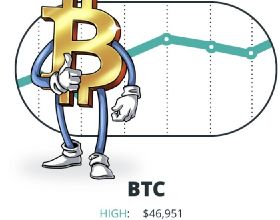史沫特萊經過長途跋涉,克服重重困難來到山西后,一方面繼續完成對朱德的採訪,一方面則作為隨軍記者忙於進行戰地報道。
史沫特萊
隨後的日子對於史沫特萊這樣一位外國女記者來說,過得是極其艱苦的。1937年8月間還呆在延安的時候,史沫特萊騎著馬在山野間馳騁,不小心從馬背上摔了下來,致使背部受了重傷。途經西安、太原時雖然都進行了治療,但由於沒有時間靜心修養,她的背傷一直到山西抗日前線時也未能痊癒,而且不時發作,非常痛苦。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史沫特萊“不但要揹著自己的公文包、照相膠捲,還得把打字機用繩子捆好背在身上”,每天跟著部隊長途行軍。當時,她從戰地給友人的信上就這樣寫道:
“我的背痛得很厲害,我得忍著疼痛工作。況且,我們從來也不在一個地方駐紮兩天以上,部隊總是在流動之中。一整天我不是走路就是騎馬,到了晚上,又得開始工作。如果部隊要是在一個地方只呆一天或一個晚上,那麼,我常常就要通宵達旦地寫東西,根本顧不上把稿子潤色一下。我疲勞不堪、疼痛難忍,實在無力把稿子用打字機重打一遍,有時候,甚至連錯處也顧不上改正。”
在這封信中,史沫特萊還向友人介紹了所在部隊和自己的困難處境:
“這一帶沒有鐵釘、沒有食油和豬油,沒有鹽巴,也沒有燒柴。我以後在隆冬臘月中寫稿子也不會有火取暖。甚至(這還用得著告訴你們嗎?)連吃的也都不夠。即使現在是秋天,我們吃的主食不是大米就是小米,外加一樣菜。今天,我們吃的是胡蘿蔔,昨天吃的也是胡蘿蔔。有時候,我們根本就沒有菜吃。這一帶來了很多隊伍,所以連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還缺少。糖,壓根兒沒有。”
可是,與朱德和八路軍戰士在一起,史沫特萊卻體驗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感受,獲得了巨大的快樂。還是在這封寫給友人的信上,她就說:
“我向你們談到的所有這一切情況,毫無抱怨訴苦之意。相反,這些日子都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有意義的日子。我寧願過這種每天淡飯一碗的艱苦生活,而不稀罕那個‘文明’所能給予我的一切。”
朱德在抗戰前線
由此,史沫特萊還決定要把自己的命運與朱德和八路軍戰士結合在一起,用手中的筆去描繪他們的偉大斗爭,反映他們甘願為之獻出生命的壯麗事業的全部含義和實質。為了做到這一點,她忍受著背傷發作所帶來的巨大痛苦,更深地融入了朱德率領的八路軍隊伍和當地的人民之中,成為中華民族偉大解放鬥爭的熱情參與者和忠實記錄者。
太原會戰要圖
1937年10月前後,正是日本侵略軍兵分幾路向山西省的首府太原進犯,戰事變得異常頻繁和特別激烈的時候,正如史沫特萊當時所記述的:“八路軍沒有真正的前方,它的戰士到哪兒,哪兒就是前方。因此,我們可以說八路軍的‘前方’北起察哈爾省,到大同,然後往西延伸到綏遠,往東延伸到平漢鐵路。它在成百個地方可以同時進行戰鬥。”隨著戰事的進行,史沫特萊跟著朱德的流動司令部和八路軍的戰鬥部隊從五臺縣出發,一路與日寇連續作戰,曾經去到過山西的五臺、壽陽、陽泉、平定、昔陽、榆社、武鄉、中陽、安澤、洪洞、臨汾等許多地方。到1938年1月5日與朱德和八路軍分別時,史沫特萊在烽火連天的山西共生活了兩個多月的時間。
史沫特萊有一本黑色封面的日記本。每當行軍途中休息的時候,她都會強忍著腰背部的疼痛,蹲在地上把每天發生的事詳細地記錄下來。這本日記的每一頁上都密密麻麻地寫滿了蠅頭小字,有的字是歪歪扭扭,難以辨認的,而且沾滿了汗水和泥垢。到了晚上,史沫特萊再坐在打字機前對白天記下的材料進行整理。就是透過這樣在艱苦的條件下的拼命工作,史沫特萊才取得了對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領導的全民抗戰的豐富觀感和深切體驗。
八路軍奔赴抗日前線
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史沫特萊當時觀察、採訪、記錄下的材料是相當豐富、全面的。
“我們昨天下午乘卡車離開太原,馳過太原北邊的平地,向前方進發,然後再穿進一個個四周群山環抱的峽谷。一路上,我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了日本轟炸機濫炸後的痕跡。公路被毀壞了,北邊的鐵路線也被毀了。”“我們聽說,近兩個星期以來,這兒有十多個老鄉和三十多頭耕畜被炸死了。”“在不少地方,日軍從每家抓走兩、三個人並加以殺害。也有的時候,他們乾脆把整個村莊裡的年輕人全部殺光。他們把這些人用繩子先捆起來,然後用刺刀劈開受害者的腦袋。按照他們的理論:那些活下來的中國人,特別是青年人‘非常危險’”。作為一名富於正義感的記者,史沫特萊所到之處都不忘把關注的目光投向日軍的暴行和中國人民正在承受的深重災難,也從中探尋著眼前這場戰爭的根源所在。
但是,史沫特萊用力最大的,還是採訪和記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是如何在艱難困苦的條件下,積極組織軍民進行抗敵禦侮的。
在她看來,八路軍首先非常重視抗日宣傳和發動:“在沿途的各個集鎮和廟宇的牆上,在那些早已湮沒在風沙之中的城鎮的古老的拱門上,寫有八路軍的口號和張貼著宣言。……‘不做亡國奴!決不當漢奸’、‘抵制日貨’、‘鄉親們,組織起來,武裝自己’。……我們希望全體同胞都能參加民族救亡工作。抗日戰爭一定勝利。”
八路軍在戰鬥
史沫特萊也注意到了八路軍的民眾組織工作的巨大成效:“我們到達五臺山裡一個有城牆的小鎮時已經是深夜了。日本轟炸機天天來光顧這個鎮子。一個名叫‘前線動員委員會’的組織為我們安排住宿。年輕而熱情的八路軍人員在這裡擔任負責工作。他們告訴我們,三個星期之前,他們可是組織這裡的青年農民,準備參加游擊戰;現在,這裡已經有差不多一千五百人參加了游擊隊。他們在接受兩個星期的游擊戰術訓練之後,前幾天已經被送到前方去了。新的自願參戰的人每天都接連不斷。他們全是種地的”,“組織人民,武裝人民的工作開展得非常迅速。八路軍在過去的六個星期之內已經把兩萬人組織成跟八路軍有聯絡的游擊隊”。
在隨軍採訪期間,尤其讓史沫特萊難以忘懷的,是八路軍與老百姓之間在共禦外侮的戰鬥中建立起來的魚水之情:“每過一個村莊,老鄉們都要出來看我們。……他們在路邊用泥土和石塊築起火灶,上面放著盛開水的大鐵壺。火灶前面,擺著小桌,上面是他們家中最象樣的陶瓷碗,涼著開水,每個人都盛著十多碗開水。我們隊伍路過時喝完一碗,他們就會馬上再斟上。老鄉們站在路邊,雙手給我們送上一碗碗的開水。這場面確實叫人感動。有好多次,我們剛拐了彎,還在離村口老遠的地方,就能看得到村裡飄揚著一團團的熱氣了。群眾就在前面等候我們。有些地方的群眾還為我們用大桶裝著煮熟的玉米棒子。他們把什麼都給我們送來,卻從不收一文錢。”
八路軍為維護抗戰統一戰線所做的一切,同樣也進入了史沫特萊的視線:“山西地方軍和中央軍在雁北戰略要地忻口失利之後,匆忙撤逃,在當地丟下幾千枝步槍和機關槍。事後,賀龍部隊把這批武器搶了回來。當時,我就對朱德說:‘這下你又可以武裝一萬多人了。’ 朱德看了看我,沒有作聲。後來,我聽別人說,八路軍把那批武器全數送還閻錫山將軍。閻錫山又把它們發還給吃了敗仗的川軍的幾個師。”
八路軍在戰鬥
至於八路軍對日寇發起的戰鬥和取得的戰果,更是史沫特萊所關心的內容。
——“在昨天的一次交火中,賀龍手下的一支游擊隊打死了六十名日軍士兵,……每天都有人到我們的院子裡來報告最新訊息。有時候,一天就要來好幾次。譬如說,一支游擊隊在一個地方打死二十名日軍,在另一個地方打死四十名,在另一個地方又打死六十名;游擊隊截獲了十五輛敵人的運輸車,又截獲了五十輛運輸車,又收復了一個城市等等。這樣的訊息源源不斷,我不可能把它們全部列舉。”
——“在山那邊的林彪部隊狠狠地打擊了日本軍隊:九千日軍從平定州分幾路向前推進;八路軍退到廣陽之後,就進山埋伏起來。八路軍切斷了日軍縱隊,用強大的炮火阻擊他們的先頭部隊,還殲滅了後面的大約一千名日軍。八路軍繳獲敵人五百匹軍馬、馱騾和大量的物資,另外還抓到一大批俘虜。”
——“八路軍不但成百地擊毀日軍運輸車輛;他們在十月十八日夜間還襲擊了日軍的陽明堡空軍基地。基地上共有二十四架轟炸機,其中二十一架被毀。十一月底,八路軍從敵人手中繳獲一千多匹馱騾和軍馬,幾百枝步槍、大量彈藥、近五十挺機關槍、幾門重炮、許多藥品和其它軍用品。他們殲滅日軍約一萬名,還把幾萬個農民組織、訓練、武裝起來,對敵人開展游擊戰爭。在山西的中國軍方人士說,日軍在西北的戰役中大約損失三萬人。”
除此而外,映入史沫特萊眼簾的,還有發生在山西抗戰之初的許許多多的事情,像共產黨和八路軍創辦軍事、政治訓練學校開展戰時教育,發表宣言、散發傳單做日本士兵的反戰工作,以人道主義精神對待和改造日軍俘虜,丁玲帶領西北戰地服務團進行抗戰宣傳演出,還有閻錫山軍隊和其他中央軍在對日作戰中的種種活動,等等。史沫特萊一邊隨軍採訪,一邊“通宵達旦地寫東西”,陸續透過友人把自己在山西抗日戰場的這些所見所聞報道給了世界。1938年,她又以自己隨軍採訪的行程為線索,採用日記體的形式,將兩個多月時間的採訪所得,作了進一步的編輯加工,形成《中國在反擊》一書,在紐約和倫敦得以正式出版、發行。
由此看來,《中國在反擊》一書的內容是極其豐富的。在這部著作中,史沫特萊以其深入紮實的採訪,對抗戰之初共產黨和八路軍帶領廣大民眾在山西戰場所開展的英勇鬥爭,作了全景式的觀照和反映。而且這種觀照和反映,是以“我”貫徹始終的,並建立在大量生動可感的細節之上,這就使得該書同其他有關山西抗戰的史籍等各類著作大異其趣,顯得真實而細膩,讓人捧讀在手,時時產生如臨其境之感。多少年後,它對於希望更多地探知那段火熱生活的人們來說,就變得彌足珍貴了。
不僅如此,由於史沫特萊處身山西抗日戰場的時候,還隨時注意捕捉來自全國各地的戰事資訊,關注著整個中國抗日形勢的變化,像談到“日本軍隊已經侵入廈門,並開始了佔領整個華中和華南地區的大規模行動”,“德國駐南京大使陶德曼博士正在極力引誘蔣介石跟世界強盜國家同流合汙,把中國變成另一個西班牙式的戰場”等等,並把它們同山西的戰事程序自然而然地融匯在了一起,這就使得她的視角產生了很強的輻射作用,從而也把這部著作的內容推入了一個非常寬廣的領域之中,直至讓人們庶幾看到了整個中國抗日戰爭起始之際的完整狀貌。由此看來,作為一代名記者的史沫特萊是長於記事的,充分顯示了其超凡的新聞素質。
實際上,史沫特萊在《中國在反擊》中並沒有止於僅僅作客觀報道,特殊的情勢和分明的個性促使她常常激情難抑,有感而發,就耳聞目睹的事件作了大量精到的評述。如當史沫特萊在行軍途中看到“腳下的路就常常從厚厚的煤層中穿過。在路邊有一些地方,石油就從地裡面往外滲出。……面前呈現著一座又一座的礦山”時,她寫道:“走在這樣的土地上,我們一下子就聯想到為什麼日本人要侵略中國的一個理由”,“多少年來,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為所欲為。他們深入到中國的各個角落,繪製地圖、拍攝照片、探明進犯的路線、尋找那些最適合的地區以實現他們征服亞洲計劃的第一步。山西省煤、鐵、石油蘊藏豐富,所以就成了日本侵略的主要目標之一”,“此種情景,不能不激起我們心中的怒火”。
當看到廣大民眾在共產黨和八路軍的組織下積極行動起來時,她又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我想這裡正在發生著一種無法形容的偉大事業;為了廣大工農群眾、為了受壓迫人民謀求解放這樣一個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運動,而進行鬥爭的這一部分中國人民的雙腳正從這裡踩了過去。這一場鬥爭還得繼續很長很長的時間。但是,這場鬥爭的開拓者、先鋒隊,儘管衣衫襤褸,裝備很差,可他們的形象卻無比高大,意義無比深遠,因為他們已經擺脫了牛馬的生活,他們已經站起來了。”
而當史沫特萊對共產黨和八路軍為民族解放所做的一切有了足夠的瞭解後,她則評論說:“那些具體體現在八路軍身上的原則將同樣會指導中國、拯救中國,並且能夠給亞洲一切被壓迫民族爭取解放以最大動力,同時也是能給人類社會帶來新生的原則”,“我覺得我也正在經歷著中國歷史上和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個時刻。有的場面看來令人很難相信,可它們就跟這塊石壁一樣真實無疑。鋼鐵般的中國人民大眾,是命定地將要決定整個亞洲,而且在很多方面,乃至整個人類的命運”。
山西武鄉八路軍太行紀念館雕塑
正是這些夾敘夾議的文字,賦予了《中國在反擊》這部著作以豐富的思想和鮮活的靈魂,讓它變得更加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給人留下了味之無窮的深刻印象。
《中國在反擊》雖然是一部新聞作品,而且是在戰爭的間隙中倉促成章的,但作者在寫作過程中,並沒有以平鋪直敘的簡單記事為滿足,而是對書中的文字極盡錘鍊加工之能事,使全書讀來流暢優美,引人入勝。關於這一點,我們從下面這個段落中,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證:
“今天凌晨,月亮還高高地掛在半空的時候,我就醒了。從窗外院子裡很舊的瓦房頂上面,我看到有一些亮光。我耳朵裡還聽到有隱隱約約的音樂聲。一會兒響幾下,一會兒又響幾下,彷彿有樂隊在大清早進行演奏似的。……我離開院子,走過站在門口的哨兵之後,就順著幽靜的小巷走進了前方的一處樹林裡。在這裡,我才找到了‘樂隊’的所在地。這是拂曉之樂,它在迎接新的一天的來臨。林中,各種飛鳥佇立枝頭,啁啾百囀,盡情歌唱。片片樹葉輕輕抖落,瑟瑟作響。兩隻山鷸,你啼我鳴,引來多少同伴的和應。遠處隱約夾雜著汪汪的狗吠聲和母牛清細的哞哞聲。這些就象是從樂器上演奏出來的旋律一般。萬物正在大地上甦醒過來。整個樹林和林間的生命正在活躍起來。我驚異地靜立在那裡,凝神聽著樂聲,這樣美妙、這樣無法形容的樂聲。接著,就在這微弱、既可分辨又難分辨的音樂中,出現了一個新的聲音。這第一聲軍號吹響了。軍號婉轉、悅耳,好象在輕輕地推著戰士們的肩膀,告訴他們說:‘該起來了,起來吧,請你們快起來吧!不要貪睡,你們瞧瞧,天都亮了。’”
像這樣的句子和段落在書中可謂俯拾皆是,枚不勝舉。它們的存在,為整個作品營造了一種浪漫的情調,並藉以表現出八路軍和廣大人民群眾不畏強敵的英雄主義精神,同時也使人們暫時忘卻戰爭的殘酷和生活的艱危,對民族解放戰爭的前景樹起堅定的信心,生出美好的憧憬。
1938年英文初版《中國在反擊》
對於《中國在反擊》,史沫特萊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我……感到自己不過是個作家,一個寫文章的旁觀者而已。……我明白了我將永遠也不能理解,也無法感受他們的生活。我只能是個講故事的人或是一個能夠描寫並沒有切身經歷過的那種生活的作家。中國真正的歷史只能由中國的工人、農民自己去寫。今天,還不能做到這一點。……至於我所能寫的東西,算不上是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本質。它們只是一個觀察員的記錄。”其實,《中國在反擊》卻是一部紀實性和文學性、思想性和藝術性並重的新聞佳作。正像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本書《序言》中所評價的那樣:“艾格尼絲·史沫特萊這本書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透過八路軍在晉北最早進行的幾次戰鬥中遇到的一些細節問題來介紹八路軍的。這頭幾仗給給中國帶來了新的希望,也給中國各條戰線提供了新戰術”,“本書堪稱一部偉大的著作”。史沫特萊以其戰地報道所顯露的勇氣和才華,贏得了國際的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