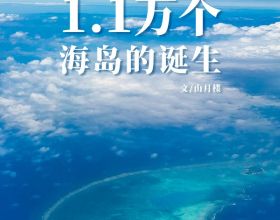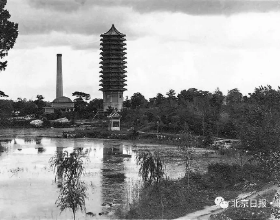陳翰笙(1897—2004),江蘇無錫人,原名陳樞,著名社會科學家和社會活動家。早年就讀於東林小學、明德中學、雅禮學校,1915年赴美勤工儉學,1916年入波莫納大學,以歷史學為專業。1920年入芝加哥大學,獲碩士學位。1922年入哈佛大學,後赴歐洲,1924年獲柏林大學博士學位。同年,受蔡元培邀請回到北大任教,經李大釗介紹為共產國際工作。1927年赴蘇聯國際農民運動研究所任研究員,與馬季亞爾就中國農村性質問題發生爭論。1928年回國,次年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社會組主任,組織大規模中國農村調查,撰寫多部農村問題研究著作。1933年正式成立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創辦《中國農村》雜誌。1934年,赴日本東洋文庫工作。1935年再赴蘇聯,任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特約研究員,加入中國共產黨。1936年赴美國太平洋學會工作,協助饒漱石辦《華僑日報》。1939年赴香港協助宋慶齡開展“工合”運動,創辦《遠東通訊》。1942年輾轉至桂林,1946年赴美國任華盛頓州立大學特聘教授。1950年應周恩來總理邀請回國,任外交部顧問、外交學會副會長等職,並出任第二、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一、第二、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協助宋慶齡籌辦《中國建設》。1955年被遴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62年擔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世界歷史研究室主任,後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名譽所長、北京大學和外交學院兼職教授等職。
陳翰笙是馬克思主義農村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是享譽中西的學術大家、以馬克思主義方法研究中國社會現實問題的最早踐行者,他的學術研究和社會活動均以解決中國現實問題、推動社會發展為中心。他力圖以廣泛的農村社會調查瞭解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進而解答中國社會性質問題,這項工作成就卓著、影響巨大,是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在農村調查領域的開創性和拓展性工作。陳翰笙也是一個身體力行的革命者,不僅以筆為武器,揭露帝國主義國家侵略中國的罪行,而且切實進行革命活動,以戰士的姿態昂揚奮鬥。
在中國問題研究中運用馬克思主義方法
陳翰笙早年在美國和德國求學,以歷史為主業,能熟練使用英語寫作,並利用德、俄、日、法等多種語言進行研究,1924年獲得柏林大學博士學位。同年,受蔡元培先生邀請,陳翰笙攜夫人顧淑型回國。陳翰笙赴北京大學任教,在此期間結識了李大釗,並透過其介紹,認識了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和一些蘇聯友人。這些交往使他能夠閱讀《資本論》並同友人討論,逐漸以唯物史觀作為主要研究方法。他在晚年回憶說:“我過去在歐美學的歷史卻沒有使我瞭解歷史,而只是些史料、史實的堆砌,讀了《資本論》,才使我瞭解了真正的歷史。”1926年,陳翰笙曾見到蔡和森,瞭解到海陸豐農民運動的情況。李大釗被捕後,陳翰笙和顧淑型經過日本到達蘇聯,在共產國際籌辦的國際農民運動研究所任研究員。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共產國際內部對於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爭論十分激烈,對這個問題的認識與中國革命的方針和政策等問題密切相關。陳翰笙在國際農民運動研究所邂逅了擔任該所東方部部長的匈牙利人馬季亞爾。馬氏是亞細亞生產方式論的代表人物,1926年曾到過中國,正在寫作《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二人就中國社會性質問題、中國農產品商品化等問題進行了爭論。馬季亞爾認為,中國的生產方式屬於亞細亞的生產方式,東方的永佃制形式是中國的特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解體的不是等級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權,而是農民所有權及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帝國主義向中國擴張帶來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其特徵是資本主義不能征服和排除商業高利貸資本,只能隸屬於財政資本之下。陳翰笙認為中國的現實情況更為複雜,要認識這種複雜性,就迫切地需要進行翔實的社會調查。
1928年,陳翰笙夫婦回到中國,應蔡元培先生邀請,陳翰笙於次年出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社會組主任,領導一批青年開啟中國農村調查。當時,已有多個國內外團體對中國社會進行了多樣的社會調查。陳翰笙為調查進行了充分理論準備,廣泛蒐集調查資料,分析調查方法優劣,揚長避短。除《資本論》外,他們還討論列寧、考茨基、馬季亞爾、廖謙珂等多位馬克思主義者的方法和觀點。他們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作為理論指導和主要方法,兼及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調查足跡遍及江蘇、河北、浙江、黑龍江、廣東、雲南、廣西、陝西等地。陳翰笙完成了《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之發軔》《畝的差異》《封建社會的農村生產關係》《難民的東北流亡》《黑龍江流域的農民與地主》等著作。他們透過廣泛調查和多種研究報告的出版,將中國不同區域農村間的廣泛差異、土地計量方法和單位的區域差異、土地分配不均、土地所有權複雜多樣、農民沉重的稅役負擔等狀況,呈現給了國內外的研究者和讀者。他們於1933年正式成立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創辦《中國農村》雜誌,在青年中間廣泛宣傳馬克思主義觀點,參加調查的薛暮橋、孫冶方、王寅生等眾多青年,或成長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或參加革命有所作為。
20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性質、中國社會史和中國農村社會性質三場論戰,直指如何以馬克思主義方法分析中國社會形態這一重要理論問題。在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中,以“中國農村派”的錢俊瑞、薛暮橋等為一方,以王宜昌、張志澄等為另一方,論戰雙方爭論的問題包括:中國社會性質、農村問題研究方法、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相互作用、劃分階級的方法、帝國主義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資本的作用、小農經濟的特點、地主是否以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等。這些論題既涉及農村問題研究方法,也包括對於中國社會形態的認識。陳翰笙及“中國農村派”成員充分利用《新中華》《中國農村》《益世報》等報刊表達觀點,並出版漢、英、日、俄語版本的《廣東農村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等著作,以農村調查為基礎,論證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出色地公開表達左翼學者的論點,批駁了認為中國社會已經是資本主義性質的錯誤觀點。陳翰笙及“中國農村派”成員用馬克思主義方法研究中國農村問題,是以生產關係為中心研究社會性質的學術實踐。陳翰笙將薛暮橋等人的文章編輯為《農村中國》英文論文集,在太平洋學會資助下在美國出版,並出版了日文版。這些文章對中國農村社會中地權複雜、土地分配不均、高利貸盛行、農民負擔沉重、手工業衰落等狀況進行了分析和揭露,論證了在中國進行土地革命的必要性。陳翰笙成為西方學術界公認的中國農村問題研究專家,時至今日,他的觀點仍然受到重視。
1940年10月,陳翰笙赴西雙版納調查,完成《中國西南邊疆土地制度》(《解放前西雙版納土地制度》是其節選本)。他指出,西雙版納封建主義的行政機構和農村公社是並存的,存在著前封建主義的農村公社,土地則屬於部落及其氏族成員所有,農村公社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制,血緣在農村公社裡始終起著控制作用。這項研究豐富了對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認識,也為“亞細亞生產方式”論爭提供了實證性材料。陳翰笙反對將中國社會歸入“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社會形態特殊論。他注意考察中國不同區域生產關係的差異,將20世紀上半期中國社會視為一個轉變中的社會,完全的封建還未過去、完全的資本主義還未到來的社會,在理解區域差異的基礎上,分析何種生產關係佔優勢。他將中國社會歸入前資本主義的、半封建的社會。
1944年,陳翰笙在《如何走上工業化的正軌》中指出,中國製定工業化的政策不能忽視歷史的繼續性和工業的社會性,以及輔助工廠工業的手工業。他在研究印度經濟區域問題時,進一步指出,當大多數人購買力極低時,真正的工業化幾乎是沒有任何基礎的,真正的工業化是工廠生產為國內市場服務的工業化。對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而言,擺脫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掠奪是實現真正的工業化的前提。在中國進行工業化建設,要利用國內市場積累資金,在建設上應當按照農業、重工業、輕工業的順序進行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1929—1930年陳翰笙領導的無錫、保定調查基礎上,於1958年、1987年、1998年又先後進行了三次無錫、保定調查,為中國農村問題研究積累了寶貴資料。
堅定不移走革命之路
陳翰笙對於革命道路的選擇,既受到時代精神的感染,又與其個人成長經歷相關。他在幼時受教於東林小學,飽經傳統士人觀念的浸染,少年時代又就學於黃興任教的明德中學,受到革命精神的薰陶。1910年,陳翰笙寫下《書懷鄒容》詩:“落落何人報大仇?沉沉往事淚長流。淒涼讀盡支那史,幾個男兒非馬牛。”這反映了其少年時代對革命者懷有的崇敬之情。李大釗是陳翰笙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他在1980年回憶李大釗時,稱其為“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戰士”。無論身處何種境遇,陳翰笙始終堅定不移地走革命之路,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1925年,他經過李大釗和於樹德介紹加入國民黨,併為共產國際做地下工作,為《國際新聞通訊》供稿。1926年,陳翰笙親歷“三一八”慘案,寫下《三月十八日慘案目擊記》。慘案的血腥和李大釗的被捕就義,更加堅定了陳翰笙繼續革命的決心。
1928年,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會議透過《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土地問題決議案》和《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農民問題決議案》等檔案,明確指出農民的土地革命是當時中國革命的主要內容,中國土地關係的根本問題是土地佔有制度的問題,農民的鬥爭是反對一切封建的束縛。從理論上廓清中國社會性質問題,以科學的方法研究中國農村土地問題,是最迫切的時代之問,陳翰笙以馬克思主義方法研究中國農村問題,回答中國社會性質問題,成為將治學與革命密切結合的踐行者。
陳翰笙從1932年開始參與宋慶齡、蔡元培等人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活動,多方營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和愛國人士。1933年,陳翰笙在《夢想的中國》一文中,希望“中國能完全獨立,印度、朝鮮也獨立,帝國主義因此壽終正寢”。他透過宋慶齡結識美國進步記者史沫特萊,進而結識裡哈爾德·佐爾格,成為其小組成員,秘密從事革命工作。1934年,陳翰笙夫婦赴日本東洋文庫工作,其實是配合佐爾格小組在東京的活動。1935年,因為有暴露的危險,陳翰笙夫婦再次輾轉赴蘇聯,後陳翰笙加入中國共產黨。1936年至1939年,陳翰笙夫婦在美國工作,陳翰笙以太平洋學會的工作為生,實際上是幫助饒漱石辦《華僑日報》,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並發動捐款購買醫藥及救護車等,贈送給中國八路軍。陳翰笙在美國廣泛結交同情中國革命的知識分子,並撰寫文章駁斥對於中國局勢的錯誤觀點。
陳翰笙密切關注中國局勢的變化,以文章、書評、信件、宣傳冊等方式介紹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他講求宣傳策略,以西方人能夠理解的語言風格進行寫作,力求為中國的進步力量爭取廣泛的支援。七七事變前後,陳翰笙積極撰寫文章分析日本帝國主義政策的實質,呼籲國際社會關注日本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他在此期間寫作《征服與人口》《七七回顧——一位中國官員揭示的戰前中國政策》《中日戰爭的經濟背景》《中國持續抗戰的前景》等文章,以階級方法分析中國和日本社會各個階級在戰爭中的作用,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政策的掠奪性,日本重工業集團和軍國主義者的政策是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最重要的原因。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遠遠沒有消除農村中的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而是維護甚至加劇這種關係,日本無法透過征服解決人口問題。這些文章刊登在《太平洋事務》《遠東觀察》《美亞》等雜誌上,並對關於日本侵華戰爭問題的論著進行討論,宣傳中國左翼知識分子對於抗日戰爭的觀點。1938年初,陳翰笙受到太平洋學會加拿大分會的邀請,到加拿大十幾個城市宣傳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決心和力量,贏得加拿大朋友的讚揚。
1939年5月,陳翰笙夫婦按照黨的指示赴香港,協助宋慶齡開展“工業合作運動”,並積極參加“保衛中國大同盟”各項工作,向同情中國抗日戰爭的國外人士和海外僑胞募捐,支援中國的抗日鬥爭。皖南事變發生後,陳翰笙編輯的英文刊物《遠東通訊》用航空版最先向世界報道了事件真相,控訴國民黨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罪行。香港淪陷後,陳翰笙於1942年赴廣西,受“工業合作運動國際委員會”委託,在桂林創辦工業合作研究所,在此期間積極營救被國民黨逮捕的革命同志。1944年春,受到國民黨通緝的陳翰笙流亡印度,他趁機對印度農村進行調查並完成相關論著。1946年6月,他受到華盛頓州立大學邀請赴美任教。1947年,陳翰笙撰寫了《經濟獨佔與中國內戰》,揭露國民黨政府發動內戰的原因,指出國民黨統治區內經濟的實質是一種依靠軍事獨裁控制的前資本主義買辦性的政府獨佔經濟。他在許多大學和學術團體進行公開演講,宣傳土地革命和與之直接相關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美國聽眾中產生了廣泛影響。
1950年,陳翰笙夫婦應周恩來總理邀請,回到祖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先後擔任外交部顧問、外交學會副會長、中國經濟學會副主任委員、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委員、中印友好協會副會長、對外文化關係協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亞洲團結委員會副秘書長、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等職務。他擔任英文雜誌《中國建設》的編輯,撰寫多篇文章宣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設成就。他創辦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南亞組,培養研究人員,推動南亞研究,並倡議由南亞研究擴充套件至中亞研究,對中國周邊國家進行系統研究,將研究領域逐步擴大至整個亞洲。
科學認識中國社會性質問題
陳翰笙著述達400餘種,多部作品有漢、英、德、日、俄語等多種版本,涉及諸多研究領域。雖然著述如此繁複,其治學旨趣卻有清晰脈絡可尋,他所關注的核心問題是中國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網路中的地位問題,既探討中國社會性質,又揭示中國同資本主義經濟網路的互動關係。圍繞這一主題,從農村生產關係到華工出國,從半封建社會農業發展到社會主義社會工業化程序,從中國到印度,從帝國主義國家經濟政策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經濟區域發展的不平衡,他對這一系列問題進行研究,利用生產關係、生產力、經濟區域、階級分析、小農經濟、工業化等概念對社會現實問題進行深入考察。他利用階級分析法,充分分析不同階級在農業生產中經濟活動的特點,對農業生產各要素,如田價、田租、利息、工資等實際狀況,進行詳盡分析。
陳翰笙在廣泛的農村調查基礎上回答中國社會性質問題,他選取江蘇、河北和廣東作為具有代表性的區域,以區域性調查為基礎,並針對移民、手工業發展、菸草種植等問題,對黑龍江、浙江、雲南、廣西、陝西、山東等地進行專題調查,從生產關係著手分析中國農村社會的基本情況,進而確定社會性質。1929年,陳翰笙在《黑龍江流域的農民與地主》中,以黑龍江流域農業生產為例,討論農業生產各要素之間的關係,例如地價與田租,在工業資本主義不發達的情況下,田租包含著農業紅利甚至是工資,田價增高就使田租同時增高,農民所得工資低落。田價愈漲,佃農僱農的經濟地位愈低,自耕農與一部分地主所能投入生產的資本亦愈少,無力改善農耕技術。
1930年,陳翰笙在《封建社會的農村生產關係》中考察了西歐、東歐及日本等地封建社會中的賦役制、強役制、工償制等制度的特點,為考察中國農村生產關係提供參照。1931年,陳翰笙在《中國的農村研究》中指出,中國農村普遍存在的土地面積標準的缺乏、農田的分散和農村地權的複雜性,都很明顯地指出一種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但是,農村生產關係的具體狀況需要進行調查。例如,以無錫為例,農戶中存在資本主義和前資本主義兩種經營形式,占主導地位的是前資本主義式的經營。陳翰笙認為,中國農村土地的分散、賦稅的繁重、谷價激落,使地主和富農不能趨向於資本主義化,土地所有與土地使用之間的矛盾是中國土地問題的核心。他在《廣東農村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中提出切實可行的農戶分類方法,基於富力而同時參照僱傭關係,具體分析不同區域農民擁有田地畝數與生活水平之間的關係,注意不同區域的差異性。他考察地主與農民之間土地分配的情況,考察農民負擔的田租稅捐和利息情況,揭示土地分配不均、農民稅負田租過高等現實問題,總結農村生產力低落的狀況及其原因。他指出,農民經濟地位越低,其承擔經濟風險的能力越低,其在生產中受到的壓力及付出的勞動越多,土地價格的高漲加劇了農民內部的分化,大批農民越趨向於貧困,成為高利貸盤剝的物件。
他以實證性研究剖析帝國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之間經濟關係的實質。陳翰笙認為,19世紀中葉以來,工業資本侵入中國農村,其最大影響是工業化和農產品的商業化。外國工業擴張所侵襲的是中國的市場關係,它幫助發展了中國舊有的商業組織,使商人資本在中國農業經濟中的地位得以加強。他在《帝國主義工業資本與中國農民》一書中,分析帝國主義經濟滲透與中國農民生產活動之間的經濟關係。他認為,在半殖民地的情況下,現代工業化沒有對中國農民的生活產生有益的作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工業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工業原料作物的發展,一般總是導致農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富農、中農和貧農在工業原料作物選種方面承受的經濟壓力不同,後兩者面臨更多經濟壓力卻獲得更少回報。只有一個獨立民主的中國,工業化才能帶來它所期望的社會福利。
陳翰笙比較中國和印度的農村生產關係,完成《印度和巴基斯坦經濟區域》一書,以此研究說明三個具有普遍性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帝國主義的統治會對殖民地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他給出的答案是:帝國主義統治會造成殖民地經濟結構的不均衡,這種不均衡會成為殖民地社會工業化的絆腳石。第二個問題是前工業化國家農村問題的出路在哪裡,陳翰笙的研究表明,僅僅是解除封建制,未必能夠解決農村問題,因為農民對於土地的權利沒有保障,解除封建化後必須以某種改革實現農民對於土地的權利。如果農村問題不解決,工業化就不是徹底的真正的工業化。第三個問題是如何協調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陳翰笙注意到,在印度最好的農業區也存在這樣的現象,即土地肥沃、物產豐富與農民貧困同時出現,自然環境的富饒不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條件,必須同時具備合理的制度,農民的貧困可能是制度性的貧困。
陳翰笙將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地理學等概念引入歷史學研究中,提出中國的世界歷史研究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形成自為一體的世界歷史研究體系。世界歷史研究應當說明世界歷史演變的過程,並揭示歷史發展的普遍性規律。他重視歷史資料的蒐集整理工作,認為必須在大量掌握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進行科學研究。他與其他學者共同主編“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叢書共10輯。他主持編纂的《華工出國史料彙編》為中國華工史研究奠定基礎。他同薛暮橋、馮和法共同主編《解放前的中國農村》史料集,彙集了中國共產黨關於農村問題的理論、方針、政策的重要文獻。他注意普及歷史知識,積極推動“外國曆史小叢書”出版。陳翰笙既是學者也是戰士,為推動社會發展貢獻了畢生精力,後人應當紀念他、景仰他。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專案“‘中國農村派’與農村經濟問題研究”(20BZS090)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牡丹江師範學院音樂與舞蹈學院;歷史與文化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劉旭升 何宛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