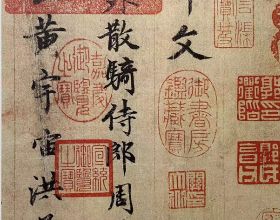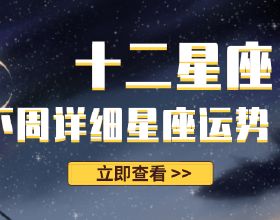作者:考拉是隻鹿,新零售商業評論特約評論員
“一招‘鮮’,能否吃遍天?”
“過年吃餃子咯。”
伴隨著虎年春節的來臨,全家人圍坐在一起,吃一頓閤家團圓的年夜飯成為了眾多遊子和父母最快樂的團聚時光。而新年的餐桌上,往往少不了餃子的身影。
俗話說,好吃不過餃子。餃子是最具中國特色的國民美食之一,它既是小吃,又是主食。一盤熱氣騰騰的餃子,雖說簡簡單單,卻足以撫慰人心。
對於北方人民來說,餃子既是日常最熟悉的一餐,也是任何節日裡都不可或缺的主角;對南方人民而言,隨著越來越多的餃子館開始進駐城區,南方味蕾們也在慢慢接受這一北方美食,特別是在一二線城市,南北方飲食的融合早已打破了地域的限制。
餃子,理應在餐飲賽道中佔據一席之地。
與此同時,隨著人們對生活質量的追求不斷提升,餐飲的升級改造也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中。而餃子館的升級版——鮮餃館正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中孕育而生。
堪稱鮮餃館鼻祖的袁記雲餃,從2016年開業至今,門店數量已達到1480家,在同類業態中規模排名第一。除袁記雲餃外,熊大爺、水餃匠、吳火獅等連鎖鮮餃館也紛紛上線,角逐賽道。
鮮餃館比起普通餃子館有何不同?鮮餃館的主攻領域和消費客群在哪裡?行業今後的發展又有哪些機遇和挑戰呢?
超越餃子館
2021年12月31日,作為速凍水餃大王的“思念”,在鄭州開張了旗下首家“鮮餃鮮吃”餃子館。
與在速凍界大張旗鼓的廣告宣傳不同,思念的首家餃子館顯得低調而樸素。店裡僅設四五張桌子,採用了鮮餃館慣用的“外帶+外賣+堂食”三重經營模式。
“鮮餃鮮吃”餃子館裡所有的食材,從切配到包制,都是新鮮售賣,包出來的餃子,如果超過2小時便會下架。
與普通餃子館前店後廚的佈局不同,鮮餃館都是將後廚前移至最顯眼的櫥窗位置。全透明玻璃的櫥窗設定不僅使得店內的食客可以欣賞到現包餃子的手藝,即便是匆匆路過的街邊市民也能駐足在店門口,近距離地觀看包制過程。
根據“鮮餃鮮吃”餃子館負責人的介紹,“鮮品外帶與外賣是兩種主要的銷售方式,未來再開的店,根據每家店的情況,不一定會設堂食。”
除了運營端的升級,鮮餃館在產品端的創新也是必不可少。
迄今為止,作為鮮餃館領軍企業的袁記雲餃已經開發了60種以上的產品品種,這樣全面的口味在普通餃子館裡是很難見到的。
同時,“雲餃”是雲吞+餃子的簡稱,可見袁記雲餃充分考慮到了南北飲食文化的差異,而且袁記雲餃還有4款手工面,可謂是餃子、餛飩、麵條,三者一手抓。
產品線的不斷豐富是品牌增加消費者黏性的重要手段,而如果能打造出一兩樣網紅爆款,那無疑將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北方水餃大佬喜家德在產品端的做法則更為大刀闊斧。2021年,喜家德將大連當地的餃子館升級成為了小酒館,真正實現了“餃子就酒,越喝越有”的風尚。
而喜家德旗下的高階水餃品牌“喜鼎”更是將海膽這一不尋常的食材融入了水餃這一平民美食中。
不僅僅是運營和產品上的升級,包括鮮餃館在內的連鎖餐飲還涉足了另一個風口——直播。
直播可以大大增加連鎖餐飲的輻射範圍,拓展客戶群,同時成本相對不高,非常值得餐飲品牌嘗試。
紮根北京40年的清真餐飲連鎖品牌紫光園,20平米的店面日營業額最高可達6萬元。2020年疫情期間,紫光園更是逆勢在京城新開100多家直營店。
紫光園的直播銷售業績相當喜人,直播產品包括線上預包裝產品和線下堂食單品菜品、套餐、代金券等。據紫光園創始人劉政介紹,直播帶來的額外消費達到20%以上。
作為升級版的餃子館,鮮餃館的升級打怪遠不止一點點。從運營到產品,從營銷到戰略,可以說,鮮餃館帶來了一種全方位的新型餃子館模式。
決戰社群餐飲
近年來,商場餐飲的競爭愈演愈烈。一二線城市的商圈經濟逐漸趨於飽和,餐飲大品牌們雖然坐擁名氣和口碑,但其中不少都是叫好不叫座,尤其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全面爆發以後,商場客流銳減,全國餐飲都按下了暫停鍵。
如今,雖然疫情已經得到較好控制,但人們的消費情緒尚未恢復到早年的水平。海底撈、茶顏悅色等品牌的大規模關店正是商場餐飲紅利遭遇“退潮”的一個縮影。
有趣的是,在商場餐飲如履薄冰的同時,社群餐飲卻“猛抬頭”,成為了餐飲業的最熱賽道。
相較於商場餐飲的高大上,社群餐飲更加接地氣。但這種接地氣絕不只是早年“解決溫飽”的蒼蠅館子這麼簡單了。乾淨、整潔、美味、實惠,這些才是消費升級後新型社群餐飲的代名詞。
商場為了流量,通常會選擇口碑優勢突出的品牌,對於新晉品牌往往並不友好;而社群餐飲品牌只要付得起租金,就能掌握更多的主動權,而且坐落於居民區中,無論是租金成本還是管理成本,相比商場都更低。
鮮餃館的興起,固然是萬千餐飲店中的一種,但更重要的是,它所瞄準的正是社群餐飲這塊“肥肉”。
餃子雖然煮起來容易,但真要自己買食材、擀麵皮、做餡料,也得費一番周章。如果一味依賴速凍水餃,口感又欠佳。鮮餃館的出現恰好同時解決了這兩大難題。而明檔的模式又使其兼具了平易近人感和乾淨衛生的形象。
不僅如此,相較於普通餃子館僅做堂食生意的套路,鮮餃館的檔口模式使得零售埠接單量更大,同時也大大增加了消費者購買的頻次。
既然下決心要進軍社群餐飲,就需要考慮社群餐飲的屬性,消費群體裡既有想一餐快速填飽肚子的年輕人,也有喜歡比價的老年群體,因此經濟實惠的餐飲連鎖更適宜紮根社群,餃子自然也就成了其中的一員。
為了做出價效比,也為了進一步提升坪效,小而精的經營模式通常成為了首選。
例如,熊大爺就採取了“生食外帶、熟食外賣”的小店經營模式。
熊大爺的店面大多在10~15平米之間,不設堂食,店內只需要五六個員工包餃子,1位收銀員稱重即可。也就是說,相比袁記雲餃這樣有堂食的鮮餃館,熊大爺再次壓縮了經營成本。
當然,社群餐飲的契機並不意味著競爭的減少。喜家德主打現包水餃的副牌“吉真”,計劃實現萬店目標。隨著鮮餃賽道的崛起,越來越多的大佬和新品牌殺入其中只是時間問題。
速凍 vs. 新鮮
鮮餃館PK的物件,主要就是高階速凍水餃。從售價來看,兩者也較為接近。
根據相關資料顯示,袁記雲餃年產值約為10億元,而2020年我國速凍水餃的年產值則達到了450多億元。從資料來看,鮮餃館還有巨大的增長空間。
想與速凍水餃分庭抗禮,現包水餃最大的優勢就在於新鮮。
不過,這一優勢同樣也是挑戰。鮮餃館的這個“鮮”字,無疑給商家帶來了更高的成本壓力和供應鏈考驗。
從成本端出發,鮮餃館目前尚屬於賽道初期,也是最容易得到資本青睞的階段。
比如去年8月,熊大爺就收穫了美團龍珠和番茄資本的聯合投資。在美團龍珠創始合夥人朱擁華看來,“水餃是大眾剛需、高頻的重要餐飲品類。未來,我們也將積極推進美團與熊大爺在業務層面的深度合作,並探索長期在線上生鮮零售方面的合作潛力。”
2021年,熊大爺全年新開門店達100家以上,佔門店總數的80%,高速擴張的態勢可見一斑。
圖源熊大爺餃子云吞官網
速凍水餃和鮮餃館在產業模式上其實截然不同。速凍水餃是食品生產型企業;而鮮餃館是餐飲型企業。換言之,鮮餃館是一個非常重資產的行業。
餐飲型企業的單一門店能否盈利,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選址是否成功。租金、人工費,客流,這些都需要經過精密測算。
從過往諸多連鎖餐飲的案例來看,一味的跑馬圈地或許能在一開始佔據較高的市場份額,但在後期卻會面臨毛利率下滑、盈利難以為繼的窘境。
例如水餃品類中,最早發展起來的品牌其實是大娘水餃。在資本介入的巔峰時期2013年,其最大規模發展到了全國450餘家門店,而如今僅剩下290餘家,早已是日薄西山。
在供應鏈方面,有了資本的加持,各家也著力於建成生產線的護城河。
以袁記雲餃為例,公司目前已經在佛山和蘇州分別建立了運營管理中心及現代化生產工廠,加盟店所有餡料必須由總部配送,每兩天配送一次餡料和麵皮,不得私採。
而吉真則可以依託喜家德在全國的30餘家中央工廠,保證原料在全國市場暢行無阻。
此外,速凍水餃可以透過機械化大規模生產,再以冷鏈的形式走向全國超市;而生鮮水餃主打的是現場手工包制,產能和輻射範圍相對於速凍水餃完全不在一個量級,想要在全國範圍內銷售只能依靠加盟。
隨著門店數量的激增,供應鏈能否同步升級迭代;加盟店包出來的餃子品相會否參差不齊;能否保證菜品的統一口感;食品安全問題如何長治久安……企業所面臨的問題都將呈幾何級的遞增。
不追求數量,先確保質量,才是可持續發展的生存之道。
一葉知秋,鮮餃賽道的發展預示著社群餐飲的未來,也演繹出傳統餐飲小吃的蛻變。
在餃子這條體量巨大的賽道上,充滿了未來擴容的想象力。
不過,正由於賽道的寬廣,想要一家獨大,未免顯得有些太貪心;想要一口氣吃成胖子,同樣有些不切合實際。
但在未來幾年中湧現出幾家第一梯隊的企業想必是板上釘釘的,誰能在這一口美味的餃子中,共享這一份消費升級下的紅利,值得期待。
快來說說,你覺得鮮餃館能拼過速凍餃子嗎?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