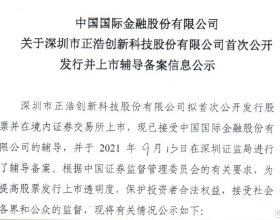上週六,我和朋友去博愛縣吉莊村看望我幼年時的老師孫耀威叔叔,晚上叔叔讓嬸孃給我們熬糊塗、烙油饃,炒他親手種的“夏皇后”大白菜吃。這大白菜甜絲絲的,入口的糊塗香噴噴的,這油饃更是綿軟可口。這一頓飯激活了我日漸寡淡的味蕾。
想想平素大魚大肉吃多了,山珍海味也不覺多稀罕。但油饃的香,一下子讓我想起小時候的幸福時光。
那時候的生活物資極為匱乏,鄉村的日子不好過。我一直認為天底下最好吃的麵食就是油饃。油饃雖好,但也不能天天吃。烙油饃費油、費面、更費時間。我父親常說填坑不要好土,他固執地認為,好東西自己吃了是填坑,讓別人吃了才是為人。無論蒸饃、窩頭還是土豆、紅薯,只要能把肚子撐圓就行,不講究食材好壞,亦不講究色香味美,吃飽後還要去地裡幹活養家餬口。只有家裡來了親戚、貴客,大人才捨得烙幾張油饃。過去家裡的掌櫃要出遠門、孩子赴京趕考、親戚走時,都不忘給他們烙幾張油饃。我們家有一鄰居是跑大車的,他們家閨女叫家瑤,和我一樣大,我常去她家玩,我發現她家經常吃油饃。她不僅吃油饃,而且還用小磨香油、蒜、醋調汁蘸著吃。那時,我的母親淋香油是用筷子頭蘸一點點,瓶口晃出一星半點還不忘用手抿嘴裡,而家瑤是嘩啦啦往碗裡倒香油,那種氣勢真讓人眼饞。
烙油饃時火不能太大,大了容易外焦裡生,需要文火。在我們武陟老家,白麻稈最好,其次是麥秸,這樣燒出來的火不急不躁、火勢穩,烙出來的油饃外焦裡嫩、色澤金黃,看來烙油饃也需要懂得中庸之道啊。
記得小時候,我娘娘烙油饃是在院裡支三塊半截磚頭,放上大鏊,然後開始和麵。她和麵是用冷水,也叫死麵,擀成圓形的麵餅,裡邊放少許鹽和油,然後再擀成一個薄薄的更大的圓餅。娘娘麻利地抓一把麥秸往鏊底塞,然後嚓的一聲點著火柴,這時她會趴在地上用嘴吹,噗的一聲火焰騰了起來。我特別記著娘娘趴在地上時額前的那一縷頭髮,她家裡孩子多,生活苦,哪有時間收拾頭髮,總是胡亂挽個髻子。娘娘一手拿擀麵杖翻,一手轉饃,三下兩下,一張油饃就落到了饃筐裡,一張挨一張摞起來,最後再在上邊蒙塊白籠布保溫,吃油饃時若能捲上一根小蔥,那可是最佳美味嘍!
我姑姑烙的油饃會更精緻一些,因為她家裡只有一個孩子,生活相對寬裕。她烙的油饃,一半燙麵、一半死麵。她也是用麥秸烘火,她每天蘸水梳頭,把頭髮梳得紋絲不亂,所以她吹火的時候,沒有亂髮拂下來。她擀的油饃裡除了放鹽,還放蔥花和雞蛋,烙好後,香甜鹹香,是我們味蕾上的想念。
而烙油饃最好的當屬我的父親。他烙的油饃,大小均勻,餅圓如滿月。餡兒更為豐富,那是放了油渣或肉末的,而且烙的油饃一層層起酥,色澤金黃,咬一口滿嘴餘香。當然吃油饃時他還會做一鍋地道的雞蛋湯給我們喝,那是相當享受。
如今給我烙油饃的父親已老邁體衰,而我常因工作忙碌而無暇烙油饃。想得狠了,便去菜市場買油饃吃,估計是油不好的緣故吧,熱吃尚可,涼了就很不好吃。今天嬸孃烙的油饃,是他們自己種的花生打的花生油,面是自己種的小麥磨的面。沒想到我還能吃到地道的油饃,我的味蕾和心情感到無比舒坦。
油饃好吃耐嚼、厚實頂飢,靠得住,就像人一樣。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我最喜歡的油饃、花捲、虛糕、糊塗、糊塗麵條、油茶等懷川大地上的眾多美食,構成了我人生最初和最終的美學,滋養著我的身體和心靈。我知道,所有的美好,往往從複試中生髮出來。我知道,土地和生靈構成了這個美好的大千世界。我知道,在人生的匆忙過程當中,總有無數的回憶刻骨銘心,比如我愛吃的油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