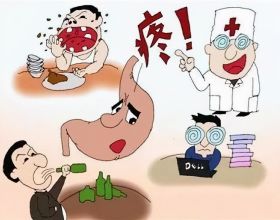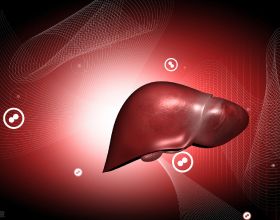我們的讀者現在要求越來越高了,經常有人留言說:能不能講一本關於博弈論的書?
我上大學的時候是讀過博弈論的書的,那時候覺得很難,因為它裡邊全是數學公式,講起來很費勁。後來終於被我找到了這本,叫作《博弈論與生活》。
這個小書你別看它很薄,來頭很大。作者蘭·費雪是非常著名的英國物理學家,他一輩子研究物理。但是他是一個科普愛好者,喜歡寫非常簡潔的文章給大家,在這本書裡邊他沒有用到任何數學公式,但是把博弈論講得特別妙趣橫生。
博弈論是解決什麼問題的呢?你看它封面上畫著三個手勢:石頭、剪刀、布,英文書名叫Game Theory in Everyday Life。就是我們怎麼跟他人互動,怎麼去玩遊戲,怎麼在博弈當中獲得勝利。
最簡單的例子:兄弟兩個人要吃蛋糕 ,怎麼分這個蛋糕比較合理?分得不小心,哥哥說我拿得少啦,弟弟說你拿得多啦,然後兩個人開始吵架。博弈論有一個非常簡單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就是:哥哥負責切,弟弟先選。那麼哥哥在切的時候,一定會盡量把它切得大小均勻,因為他後選。你看就引入“先切後選”這麼一個小小的方法,爭端就減少了很多。
這只是最簡單的一個舉例,你再往後聽你會發現,就切蛋糕這麼一件事都沒有這麼簡單。因為現實情況下,可能不是隻有兄弟兩個人,還有其他更多的人;可能要分的不只是蛋糕,還有很多看不見的東西。
博弈論是20世紀40年代被提出來的,然後開始火熱。火熱到什麼程度?有一個事實能夠證明這一點:有五位獲得諾獎的博弈論研究者被美國國防部聘請為顧問。國防部不會請所有的經濟學家做顧問,他請的一定是那個對他們有極大影響的研究方向的專家。他們認為博弈論對於國防部的研究影響很大。
這個作者有一天在他們學校裡邊喝茶——英國喜歡喝下午茶——就聽到一個教授在那邊喊:誰把茶勺給拿走了?就是公共茶勺被人拿回家了。然後作者就說:到處都是博弈論。這麼一個公共茶匙會被誰拿走的事情,是一個典型的公地悲劇,也是博弈論研究涵蓋的範圍。因為茶勺是公共的,學校出錢買,沒有人會為它負責,最後的結果就是它會被拿走。
博弈論的前提是你得承認人性是自私的,你不能夠簡單地透過“我們把大家都教好,大家都不要拿”就解決了。你需要設計一系列方案,一系列博弈手法,來讓自私的人性相互制衡,最後達成一個對大家都有效的解決方案,這是值得一學的。
首先最有名的博弈論的命題,叫作囚徒困境。囚徒困境的命名者是普林斯頓大學的阿爾伯特·塔克。
什麼叫囚徒困境?這兩個人犯罪了,被抓到警察局,如果誰都打死不承認,就是說我什麼都沒幹,那麼充其量兩個人各判兩年。因為你沒有更多的證據,就只能判兩年的輕刑。這是第一種狀況。
但是警察局長很聰明,他就跑來跟這個人講:你那個同夥很有可能就會交代,我告訴你,你最好也交代。為什麼呢?如果你交代了而他沒交代的話,那麼他要判十年徒刑,你無罪釋放,立刻就走。
同樣的話局長也說給了他的同夥,所以同夥也在考慮:我如果交代了,我可以立刻被放走;我如果不交代,而他交代了,我要判十年徒刑。
這是他們的兩個選項,那麼兩個人都不交代,兩個人都是兩年;要麼一邊判十年,一邊無罪釋放。最後兩個人會做什麼選擇?大部分情況下兩個人都會選擇交代,我檢舉他,他檢舉我,最後的結果是至少各判四年。
那你說為什麼兩個人都非得交代呢?假設你是其中一個囚徒,你想想看你交代不交代。如果對方不交代,你交代了,無罪釋放;如果對方交代了,你也交代了,也才判四年。但如果對方交代你打死不交代的話,你會判十年。因此導致的結果往往是:這兩個囚徒並沒有餘地去做那個對他們最有利的的選擇,往往都是兩個人爭先恐後地交代,然後各判四年。這個就叫作囚徒困境。
它為什麼是一個困境?因為並沒有達成它可以獲得的最好的狀態,雙方產生了博弈。囚徒困境在生活當中多嗎?太多了,比如說追女生。這個作者就講,他小時候跟他弟弟同時喜歡上社群裡一個新來的小女孩,然後兩個人都跑到小女孩面前去說對方的壞話,最後的結果是兩個人誰也追不到。這也是囚徒困境。
還有一個就是當年死海古卷的保護。考古學家發現貝都因人生活的地方有死海古卷,很珍貴的文物,就開始向那些牧羊人收購這些古卷,說如果你有這整張的紙,你賣給我。後來競爭變激烈了,說你有一個碎的小紙片也可以賣給我。結果你猜怎麼著?很多牧羊人找到死海古卷以後,撕碎。因為撕成一小塊一小塊賣的錢更多。他們這種爭先恐後收購、試圖保護古卷的行為,反而導致了大量的古卷受損。
還包括現在最火的碳排放的話題,誰先帶頭把這個碳排放降下來?好,我們降,我們降下來 隔壁國家不降怎麼辦呢?隔壁國家如果搭我們的便車,我這邊降低了,他那邊燒,那他財富增加得比我快得多,我這邊成本高了很多怎麼辦?這時候該怎麼樣帶領全世界的人走出囚徒困境,讓各個國家的總統總理們能夠理解囚徒困境對所有人都不利,這都是博弈論所要研究的方向。
這裡邊要提到一個人,大家看過一個電影叫《美麗心靈》吧?那裡邊的男主角叫納什,納什是諾貝爾獎得主。他1948年進普林斯頓讀書,申請碩士學位,推薦他的教授寫的推薦語只有一句話:這是個天才。他研究數學,研究邏輯學,他認為最讓他瘋狂的就是邏輯學這件事。他後來得諾貝爾獎也是因為研究邏輯學,提出了納什均衡的概念。
什麼叫納什均衡?就像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各判四年的狀況,那就是一個納什均衡。納什均衡的定義就是:在任何競爭或衝突中,如果各方不願或者無法溝通,就至少會有一個納什陷阱等著請君入甕。那兩個囚徒他沒法溝通,他們倆在不同的房間裡邊。所以你知道審犯人的時候,為什麼警察的第一招就是先分開、先拉到不同的房間去?因為這樣就阻斷了他們的溝通,就一定會有一個納什陷阱在等著:雙方均已選定一種策略,任意一方獨自改變策略將會使情形惡化。假如這兩個人是慣犯,在進去之前都已經商量好了,說如果抓住的話打死也不承認,這樣的話咱倆都是輕刑。但是如果有任何一方改變事先約定,都會使得情形變得更糟糕,這時候他們就進入到納什陷阱當中。
在各方都選擇了同一策略的情形下,沒有一方能夠透過獨自改變策略而獲益,此時的策略搭配和後續結果,就構成了納什均衡。就比如說有一方招了,然後你說我堅守,我不招。你不招,你判十年;而對方招了,對方獲益,零年。這時候就是陷入納什陷阱當中,同時達成了一個四四的納什均衡,沒有人有動力再去改變。
山路堵車也是一個典型的納什均衡。我去年去林芝,走那個國道,那是非常美的路段。但那個路段太容易堵車了,只要有一輛車想要佔道超車,完了,你就會發現那個車長串地堵在一起,甚至連讓的機會都沒有。就一定要找到一個第三方,這個第三方就是警察。要警察大老遠趕過來協調,才有可能疏通,否則就會長期地堵在那個地方。為什麼呢?假如有一個司機說我願意讓,你願意讓的結果就可能導致你永遠也走不了。然後那邊的車很多,源源不斷地過來。這時候如果沒有一個令雙方可信的第三方出來調解,大家就會陷入在這個納什陷阱當中,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在生活當中,經常會出現各式各樣的納什陷阱,還包括離婚。有生活經驗的人會知道,離婚這件事發展到最後往往就是爭財產。一開始大家都不這麼認為,開始離婚的時候大家都會說,錢我不在乎,都給你都行,我走了。
結果發現對方真的都拿走了,就開始生氣,說憑什麼你這樣對我,我不蒸饅頭爭口氣!然後就開始打官司,不斷地折騰。最後你會發現大量的錢用作了律師費,用作了消耗的社會成本。原因就是雙方各不退讓,不願意妥協。一開始的姿態都很好,但是由於一方做的讓對方不滿意,激起了對方的惡意,開始大量地爭執,最後陷入到一個納什均衡當中。這就是為什麼離婚會成為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
那這個書裡邊作者就講說,如果你希望在離婚當中不要有那麼大的傷害,各讓一步。就是如果雙方都能夠像山路上那個開車的人一樣,說我自覺地讓你先過、你自覺地讓我先過,這時候雙方妥協對對方的收益更大。但是往往大家不願意妥協,因為我生氣,我覺得我吃虧了。其實你吃這點虧,也比你連著打三年官司吃的虧要少得多。但是因為人們的這種情緒和不同價值觀的選擇,就會導致我們很容易陷入納什陷阱。
那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分兩步。第一步是找到方式達成協議,我們要在這個博弈當中能夠達成協議;第二步,找到方式讓對方不變卦。比如說,一開始大家約定好都不招,這就是一個協議;但後來有人變卦,你就受不了了。所以要用博弈論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讓對方不變卦有三個途徑:第一個途徑叫作改變態度。就是我們在博弈的時候不要有那種 “不蒸饅頭爭口氣”這樣的想法,如果你能夠稍微成熟一點,能夠把效用範圍變得更寬泛一點,可能更容易達成協議。
第二個叫作訴諸善意的權威人士。我記得我很小的時候,家裡邊有人吵架,大家族裡邊這一家跟那一家吵架了,就會請兩三個族中長老,圍坐在一個大屋子裡邊開始講理,跟今天的辯論會是一樣的。其實我覺得我們家的民主氛圍特別好,就是聽老人家最後擺平,告訴大家應該怎麼做。這個叫作訴諸善意的權威人士。
第三個方法是制定能夠自行運作的策略。就是設定一套能夠自行運作的機制,不需要整天由長老出面來解決問題,這個是博弈論的重點。因為前兩個其實都是教育工作,涉及的都是你的態度,你要信任。最後一個是不需要教育工作,你照著做就行了。
咱們的交通規則就是一套典型的自行運轉的機制。很多地方不需要警察,只要有攝像頭,交通就能順暢地執行。所以重點就在於我們怎麼樣去打造出能夠自行運作的策略來。
要解決囚徒困境,就要解決公平和正義的問題。這一章作者給它起個名字叫作“我切你選”,就是我們剛剛講切蛋糕那件事。
人們對於公平和正義的需求,是一個天然的感受,甚至黑猩猩都能這樣。動物學家研究黑猩猩,給它們分香蕉,他故意地給一些黑猩猩分得少,給這個兩三個,給那個就分一個。竟然有的黑猩猩把那個香蕉摔了不吃,它生氣了。我們以為說只有人才會在意公平,其實猩猩也在意。所以人們對於公平和公正的需求,是一個底層的動物性的需求。
而“我切你選”這樣一個基本的管理方法,英文叫作mini-max(大中取小)。這個策略在什麼情況下有效?著名數學家、計算機的始祖馮·諾依曼講過,只有在零和博弈中有效。零和博弈就是這事咱們不會再創造更多的溢位效應,就是這麼多,咱們怎麼分吧。就比如說家裡邊分財產這種事,我不可能透過分財產這件事創造出更多價值來,要麼我多,要麼你多。這叫零和博弈。
在國際社會上,如果你是零和博弈的思想,那就是秀肌肉,看誰強大,然後討論怎麼分。但假如你能夠有建設性,你說我們不一定非得把它靠分來解決,我們透過建設、透過獲取更大的收益來解決,這時候“我切你分”這個方法,就未必見得有效了。
這裡邊有三大難題。第一大難題是價值觀不同,就是我切的時候,我們的價值觀是不一樣的,你可能喜歡奶油,而我喜歡蛋糕;或者你喜歡奶油當中有花的那部分,你覺得能夠分到那朵花就夠了,但是我不認為那個花很重要。這是價值觀不同,不能夠簡單透過“一樣大”就解決,生活就是這麼複雜。
第二個是實際執行的問題。蛋糕你可以拿刀切,更多的東西怎麼切?比如榮譽感、署名、職稱這些東西,就很麻煩。
第三個難題是最後如何讓這些人都接受這個結果。這三個就是我們想要保持公平公正最難的問題。
作者有一個案例特別逗。有一次他去晚宴上吃飯,最後一道是甜點,輪到他這兒的時候只剩兩塊蛋糕了,一塊大一塊小。他後邊還有一位女士,然後他就展現紳士風度,把蛋糕交給那個女士,說您先選。他想觀察一下這個女士會選哪塊。結果她毫不猶豫地選了小的那一塊——哎你看,這個跟我們對人性自私面的理解不一樣。
他就覺得很奇怪,難道博弈論不存在了?他就問:您為什麼選小的這塊呢?女士說:“我覺得選大的有點不好意思。”各位請注意,這是什麼呢?這個東西叫作效用問題。
什麼是效用?你在一個十歲以下的小孩子面前,這個蛋糕所帶來的效用就是吃,那就是越大越好越開心。但是對於一個正在減肥當中的女士,或者一個要顯示紳士風度的男士來講,別人怎麼看你、別人怎麼評價、別人對你有什麼樣的印象,這些可能比吃到多大的蛋糕更重要。所以儘管她的選法跟其他的案例當中的假設都不一樣,但是博弈論依然存在。因為它的效用變了,這個美好的感受也成為了效用的一部分,因此那個女士依然是自私的。
各位能理解了嗎?經濟學最有趣的地方就在這兒,它怎麼都能解釋得通。為什麼很多科學家把經濟學叫作偽科學,就是因為你沒法反駁,你只要說它不對,它就說那是不同的效用。它一定能夠透過效用的方法來度量、來解釋這個事情。這個很有意思。
那如果遇到更復雜的情況,透過簡單的“分蛋糕”不能解決了,應該怎麼辦呢?這裡邊有一個方法,叫作有爭議的部分平分法。
什麼叫作有爭議的部分平分法?古老的智慧當中,猶太法典《塔木德》、中國過去的寓言中都有這樣的故事:大房和二房要分財產,大房堅持認為說我要分全部的財產,這全是我的;二房認為說我至少應該分到這財產的一半。那麼請問,根據我們古老的智慧,她倆應該各分多少?
答案是不用算,大房75%,二房25%。你說這是為什麼?過程很簡單,就是首先看哪些是有爭議的部分。有爭議的部分是一半,因為二房主張只要一半;另外一半是沒爭議的。沒爭議的先分給大房,剩下的一人一半,所以大房75%,二房25%。
大家不要覺得太簡單,人類歷史上大量分割問題的解決,都來自於這個公式。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講過一句話,特別有意思。他是個談判專家嘛,這一輩子就是在跟全世界談判。基辛格說:你在談判桌上能夠獲得多大的收益,取決於你一開始能夠提出多麼離譜的條件。就是你把那個爭議的範圍放大,最後你獲得的東西會多一點。假如你像我們前面講的那個二房,這麼老實,說我就要一半,那你就只能獲得這一半的一半了。
當然我不是想教大家變壞,不是讓大家都變成那個特別野心爆棚的人。在後邊你會聽到:如果一個人總是用惡的策略對待別人的話,其實對他的博弈結果非常不利。這本書我覺得最陽光的一點就是:它整個讀完了以後,你會發現做個好人是最好的,你在博弈當中反倒能夠獲得更多的好處。
更困難的是三個人怎麼分?就比如說三個孩子分蛋糕。現在好了,老大你負責切,切完了弟弟先選。麻煩了,老大很難切得三塊完全一樣,老二就佔便宜了,因為老二可以選一塊大的拿走。
這時候有辦法:讓第一個挑的那個人,或多或少你要切出一塊來。這種規則也是有過的,老二先挑,挑好之後,好,忍痛切一塊給你們拿走,然後剩下兩個人挑。兩個人中先挑的那個,再切一塊拿出來。這個方法導致的結果是分不完,很有可能永遠都有一小塊,都有一個極限點需要你去分。
還有一個方法叫作調整贏家法。調整贏家法的基本原理就在於:對於同一項資產,不同的人可能會定出不同的價值,假如雙方要劃分所有權,就可以動些手腳,讓雙方感覺自己都拿到超過一半的所有權,達到雙贏的局面。而且不管是什麼情境都能夠適用,這個叫調整贏家法,雙贏。
雙贏局面是怎麼產生的呢?是來自於大腦當中的幻覺。大家不要覺得這是騙人,這個在生活當中非常實用。
我有一次慘痛的經歷,我成了調整贏家的受害者,賣了北京的一套房子。我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心血來潮,三萬一平米就給賣了。我記得很清楚,我和那個買我房子的人交接完了以後——之前我們倆都沒什麼特別多的溝通,只是說趕緊辦手續——手續一辦完,我們倆從交易大廳走出來,相視一笑。那人說:這個價錢以後在這個地恐怕是買不到啦!然後我說:房價也未必會一直漲吧。
這就叫調整贏家。我們倆被誰調整贏家了呢?被那個中介。中介給我做工作,說:完了,我告訴你,北京這房價都三萬了,你放心吧,現在絕對是高點。被忽悠了,賣了。給買家調整的方法就是:這房子太便宜了,你趕緊買。所以我們倆最後抱著非常美好的心情達成協議交割了房子。現在那個房子大概十萬塊錢一平。
調整贏家這個策略在談判過程當中肯定會有效,博弈的時候你要能夠告訴大家說:這兩塊蛋糕雖然大小不一樣,但是你這塊上面有花呀,多開心,拿走。我們在對待小孩子的時候,經常會用這個調整贏家法,這是很有效的。
實在不行可以投票。就是大家說沒法分了,投票吧。這也是一個公共決策的方法。這些東西都是為了解決囚徒困境當中不好分、沒法達到公平的問題。
那生活當中,你說光一個囚徒困境就已經這麼複雜了,還有別的困境嗎?生活當中至少有七大困境,全是邏輯造成的。這是邏輯所帶來的必然要面對的問題。
除了囚徒困境之外,我們下面來說其他六個困境。
第一個叫作公地悲劇。公地悲劇是指多人的囚徒困境,所有人困在了那個最糟糕的狀況之下。比如說,有一段時間好多公園喜歡擺很多紅雨傘,特別好看,擺了兩個小時後消失了,進公園的人都把那個紅雨傘拿回家。後來還有很多報紙報道出來,說為什麼都拿回家?很簡單,公地悲劇呀,因為這東西它沒有主,不知道是誰的。
公地悲劇是多人博弈,這麼多人陷入到一個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雙方,公地悲劇是多個人進入,變成了公地,公有的地。公有的地沒人管,造成的結果就是所有人的效用都下降。
第二種叫搭便車,它其實是公地悲劇的變形。比如你每天上班,有個同事跟你住同一個小區,說你把我捎上吧。第一次無所謂,大家關係挺好,捎上了。結果第二天捎人成了你的義務了,哎你怎麼沒等我呢?把你完全當班車這麼對待。
對於他來講,他會覺得說:你不拉我難道你就不開了嗎?你把我拉上有什麼不好呢?這叫作搭便車。往小裡說,你覺得這事無所謂;往大里說,扔垃圾的時候,不交垃圾費的跟著一塊兒扔,反正有本事你也別交垃圾費,咱們這兒垃圾堆成山。你受不了你交了,那我就跟著搭便車,最後的結果是交的那些人吃虧。
搭便車的行為要想解決,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讓搭便車的風險和代價提高,就是想辦法去懲罰那些搭便車的行為。讓他意識到說,儘管你交不交這個錢都沒關係,但是你也得交。這裡邊的那個下限在哪兒呢?在有效合作下限。搭便車的行為之所以存在,是因為這個錢我不交也沒影響,沒有達到有效合作下限。在公司裡邊、小區裡邊、家庭裡邊、學校裡邊,經常會出現這種搭便車困境,所以我們需要提高它的代價,然後改變獎勵結構。
第三個困境叫懦夫博弈。這個特有意思,懦夫博弈就是不退讓的一方會獲益的博弈。兩個人狹路相逢,一個小衚衕裡邊兩個車頂在一塊兒了。誰讓?這邊開始按喇叭,那也開始按喇叭,都不願意退讓。這個叫作懦夫博弈。
懦夫博弈就是看誰先服軟,你往後退,行,你服軟了,那我就過來,過來以後走掉,這個懦夫博弈才能夠解決。能夠解決的前提是你得往後退。我們在國際社會當中,經常會遇到懦夫博弈的狀況,比如說古巴導彈危機。古巴導彈危機是人類距離核戰爭最近的一次,美蘇兩國都要表現說我是義無反顧的、我是一定要打你的,你只要敢動我就一定打。這是很危險的事,都不讓,怎麼辦?
作者說第一個方法特別有意思,叫作笑一笑。笑一笑就解決了。什麼意思呢?對方過來一輛車,你這兒過來一輛車,他不讓,你笑一下,你給他讓了就算了,擴大一點你的效用範圍。如果你的境界很低,你覺得只有優先透過這個衚衕才叫贏,那麼你就會發現誰也過不去;但是如果你有一點幽默感,你能夠笑一笑,你會意識到說遇到了一個懦夫博弈,讓開了,你會滿足於自己的修養提高。
你看看,你的效用值是不是擴大了?一旦你的效用範圍擴大,解決問題的途徑就變多了。這就是孔子講的那句話,叫作“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你想做一個好人,你現在做了一個好人,你有什麼好抱怨的。我們在生活當中,很多人不願意做好人是因為老覺得好人吃虧,憑什麼讓我做好人?你看,當你說出“憑什麼讓我做好人”這句話的時候,就證明你並不覺得做好人是個好事。你覺得沾光是一件好事,就會陷入懦夫博弈,那這誰也解決不了。所以這是我們說第一個方法啊,你要學會笑一笑。
第二個辦法,你也得經常調換自己的策略,叫作鷹鴿搭配效果好。我們經常說有鷹派、有鴿派。鷹派的特點是說打就肯定要打,老鷹要來抓你,就不可能放過你。如果你在國際上,或者你在單位裡邊博弈,你要顯示自己是個鷹派,你永遠是很剛硬的,好,這是你的一種策略。什麼是鴿派?鴿子經常虛張聲勢,“譁——”俯衝下來,看起來要抓你了,“嗚——”飛走了。因為他是個“鴿子”,他並不是個“老鷹”,他經常會嚇唬你一下又跑掉了,這種是鴿派。鴿派就是可以徵求一下訴求,一看不行,我就讓了。
如果你總是鷹派,你其實會傷害自己,因為對方知道跟你博弈沒有好下場,他跟你槓上就是危機邊緣;如果你總是鴿派,被大家琢磨透了,說這人總是騙人,虛架子,不管他,也沒用。所以最好的方法是鷹鴿搭配。
第三個辦法,在懦夫博弈當中,如果你對對方提出了威脅,有一個原則很重要,這個威脅要能夠生效。如果不能生效,那就不是個威脅。這個作者說特別逗,有一次他在超市裡邊看到一個媽媽大聲地吼女兒,有一個小女孩不聽話在那兒玩。那個媽媽說:你快點給我過來,不然我就“宰”了你!然後那小女孩很淡定地講:你最好這樣做。這說明媽媽的威脅不管用,因為你怎麼會因為在超市裡邊玩就把小孩子“宰”了呢?你不能夠做出這種沒道理的、虛張聲勢的威脅。
國際社會交往當中,我們說國際信用很重要。你如果沒有信用,你想做出鷹的姿態,或者威脅別人的姿態,沒人信。這都是我們在懦夫博弈當中要注意的東西。
古巴導彈危機最後怎麼解決的?是因為雙方都做出了更大的效用,肯尼迪和赫魯曉夫決定說我們可以選擇別的東西,然後你把導彈撤了,我把駐軍撤了,用相互妥協的方法解決了這個危機。
如果雙方真的是不理智,完全沒有其他效用引進的話,懦夫博弈經常會帶來很大的傷痛。你看電影裡邊經常會有那個俄羅斯轉盤賭,拿一把槍,啪一轉,來,你來一槍。啪、啪、嗵! 死了。這是懦夫博弈中典型的悲劇。
第四個叫作志願者困境。這個很有意思,簡單地講,就是第一個站出來的人肯定會犧牲,但是如果沒有人站出來,所有人都犧牲。最標準的例子,看過《動物世界》吧?非洲大草原上牛羚過河的時候,河裡邊有很多鱷魚,怎麼辦呢?那群牛羚都在河邊猶豫不敢下,就得有一個牛羚率先跳進去,所有鱷魚撲過來咬它的時候,其他牛羚趕緊過。那麼誰來做這第一個牛羚?
我們在生活當中,其實經常會遇到需要有一個人站出來做自我犧牲的情況。你比如說發救濟糧,你能看到在索馬利亞這些地方發救濟糧的時候,為什麼有時候會排隊、有時候會哄搶?這個跟第一個到達救濟站的人有很大關係。如果第一個人到了那兒以後說,排隊,我第一個要求大家排隊,這時候大家容易建立一種秩序。
住在阿根廷火地島的亞根印第安人,有一個詞可以用來形容志願者困境中大家的心態,真是再貼切不過了。這詞叫作mamihlapinatapai,意思是“雙方互望,希望對方去做一件彼此都希望能完成,但自己又不想做的事”。就是這麼複雜的一個意思,用這麼一個長的詞彙表達出來了。這個詞入選了1993年版的吉尼斯世界紀錄,因為它是所有語言當中最精煉的詞。
志願者困境應該怎麼樣解決?有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叫謝林,提出來一個概念叫謝林點。就是在所有這些志願者困境的博弈過程當中,第一個牛羚為什麼跳下去了?因為它覺得該它跳,它找到了那種該我跳的感覺。那些衝出來大吼一聲、制止歹徒的那個人,也是找到了那種需要站出來那種感覺,或者是心理暗示。托馬斯·謝林對謝林點的描述是什麼呢?他說:每個人在面對他人期待自己怎麼回應的期待時,心中所產生的那個期望。再念一遍,這話有點拗口:每個人在面對他人期待自己怎麼回應的期待時,心中所產生的那個期望。
就是你在猜測對方對你的想法,然後你根據對方對你的想法的猜測做出一個判斷,這時候你覺得該動一動了,這個點叫謝林點。說得這麼拗口,我的感覺就是叫心照不宣。謝林點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就是告訴你:我們有一些暗示、默契、心照不宣的地方。這個作者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你走在一個陌生的國家,迎面過來一個人,現在你希望靠右走或者靠左走,怎麼做呢?你得給對方一個動作,就是你得有一個身體的傾斜,有一個小小的暗示,雙方一側身,就過去了。這種讓對方一下子明白的這個點,就叫作謝林點。
然後這作者故意搗亂,他要挑戰不同國家的人對於這個謝林點的耐心到底有多少。他就故意地看對方朝右他也朝右,看對方朝左他也朝左,然後就跟人在街上這樣晃。你們見過嗎?在一個窄路上兩個人過不去的那種感覺。他說用時最短的一次是在英國,一個人過來,他跟別人剛晃了一下,那個英國人站住了,說:你先確定要走哪邊。最長、最有耐心去探索這個互相的邊界的是在日本,他在日本的街上跟一個人面對面連續晃了十七次,沒有人敢於打破這個窘境,雙方都在謹小慎微地晃。
這就是在探索不同文化之下的謝林點到底在哪兒。在這裡邊有一個原則,叫作:你要小心顫抖的手。什麼叫顫抖的手?就是比如說,你家房子著火了,整個小區都著火了。作者真的有一次碰到這個情況,山火燒上來了。這時候他有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是趕緊往自己家的房子上潑水,先救自己家房子;還有一個選擇是趕緊打電話報警,晚一點給自己的房子注水。當然最好的情況是別人打電話報警,他趕緊救自己的房子。但是這個時候你就要小心“顫抖的手”——萬一所有人都這麼想怎麼辦?萬一所有人都想著讓別人去報警吧,我趕緊救我的房子,那導致的結果就是沒有人報警,最後很有可能這個火真的燒上來。好在他說他們那些鄰居,大概有四五個人都選擇了先報警。
志願者困境裡出現的這種“顫抖的手”,在生活中其實比比皆是。各位知道有一個現象,你在大街上遇到了壞人想要求救,最有效的方法絕對不是向所有人求救,如果你在那兒喊“救命!幫忙!有人搶劫!”你喊這樣的話,其他人全站著盯著看,但不會行動。為什麼呢?大家覺得那個人離得更近哪,這個人個頭更高啊。你看,每個人都期待著別人去做,導致了“顫抖的手”現象發生。在大街上,如果你真的遇到了困難,遇到了危險,最有效的方法是抱住一個人求救,就突然撲過去抱住一個大哥的腿,“大哥救命!”這時候反倒能救你,因為這個責任歸他了,那個“顫抖的手”解決了。
紐約曾經發生過一起令紐約人引以為恥的案件,就是一個女孩在街道上被人搶劫,被殺害了。被害過程中發出了巨大的慘叫,但整條街上沒有一個人出來看,沒有一個人管。原因就是大家覺得:有別人管吧,肯定有人管。
所以我們在面臨這種志願者困境的時候,我們建議大家:你應該站出來。當然不是說像牛羚那樣跳進去就死了,但是至少你可以做一些小小的犧牲,這時候反而會使得大家容易團結起來。打破志願者困境的關鍵點,也是在於你的效用值跟別人不一樣。如果每個人考慮的都是安危,那效用值一樣,志願者困境一定發生;但如果有人考慮高尚,如果有人考慮說這是我應該做的、我的價值觀,那這時候,就比較容易打破志願者困境。
第五個困境是兩性戰爭。這特有意思,兩性戰爭的前提是什麼呢?就是兩個選擇都不錯,都行,都能接受。不像志願者困境或懦夫博弈那麼要命,但是還是有差別,我就是不樂意。最要命的是春節回家去哪兒:去你家呢?還是去我家?你家已經去過幾次了,為什麼不能去我家?為什麼咱們倆要一年去一個地方,咱們家就這麼僵化嗎?就算你想透過“今年你家,明年我家“來解決,也不行,吵架。這叫兩性戰爭。
兩性戰爭的解決方法給我逗死了。一個叫奧曼的經濟學家,因為解決了兩性戰爭問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奧曼提出的博弈論的方法就是拋硬幣。就是你們決定今年要去哪家過年,拿硬幣拋一下,正面去你家,反面到我家。就這麼點事,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是人家不是這麼白得的,人家是把各種解決方案全部用數學公式算了一遍,算來算去,最後的結果是拋硬幣最有效。
理由是:在解開僵局的過程當中,關鍵在於雙方要同意以某種方式隨機選擇策略。由不具利害關係的第三方選擇之後,私下告訴雙方怎麼做,但不要告訴他們這個策略對另一方有何影響。這個原則很簡單,但實際執行起來還是會有點難,但是這已經是解決兩性困境的最好方法了,因為引入了隨機性,大家拋一下,就解決了。
球場上誰先開球,這就是兩性困境。最後怎麼解決的,拋硬幣呀。裁判拿出個硬幣一拋,解決了。所以引入隨機性有時候真的能夠很有效地解決很多問題。就像我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有些問題解決不了,石頭剪刀布,大家卒瓦,一卒瓦就知道了。
七大困境的最後一個叫獵鹿問題。這個問題非常常見,比如說咱們仨一起出去打鹿,鹿可不好打呀,鹿跑得快,大型動物,所以咱仨都不能退,這才有機會能打到鹿。但是呢,也有可能咱們仨這一天什麼都沒打到,因為鹿很難打嘛。結果剛出門沒多久,那張三就發現有個兔子在旁邊,你說打不打那兔子?萬一張三跑去打那兔子呢,就會導致你們倆打鹿肯定失敗;但是張三肯定能得到一條兔子,他得到這麼一隻兔子回家,全家就有吃喝了。所以張三可能就會選擇跑去打兔子,然後把獵鹿的工作交給你們倆。這個叫作獵鹿問題。
獵鹿問題的核心就是你要小心低風險的誘惑。因為獵鹿是一個高風險高收益的事,收益高,但你很有可能得不到。低風險會帶來誘惑。你比如說我們在創業的時候,你跟你的員工描繪了一個偉大的願景,說咱們公司好好幹,努力上市,上市完了以後你們都跟著發了,你看那都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好多。但是這個員工呢,他老喜歡幹私活,為什麼?他覺得等到你上市那天,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了,我還是每個月稍微乾點別的吧。幹私活、偷懶,能夠帶來即刻的收益,就像抓兔子一樣,但是這會使得別人很有可能抓不到那條鹿。這個就是典型的獵鹿問題。
這個“兔子”和“鹿”,在我們的生活當中是經常會出現的,那我們就要做抉擇,就要去想:怎麼樣能夠讓大家更加相信這件事情。
我們把這七大困境全部講完了,都是人類亙古就有的,自古以來就一直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博弈。今後你就學會了,你去看電影電視劇,你一看就知道這說的是哪個困境,一定是從這七種困境當中演化出來的。博弈論的好處就在於,只要遇到矛盾,一定有一個困境等著你,你可以對照,看清楚自己是處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中。
講完這七大困境以後,我們接下來看看,如何讓一個策略能夠自行運作。這作者說,我們要解決這些困境,讓策略自行運作,最經典的做法就是石頭剪刀布。
這就是石頭剪刀布的圖案為什麼會被印在封面上的原因。石頭剪刀布在美國叫Ro-Sham-Bo,翻譯過來就是羅尚博。羅尚博是法國和英國打仗時的法國元帥。那為什麼用法國元帥的名字來命名石頭剪刀布呢?這個特好玩。英國跟法國在美國打完了仗以後,雙方要簽訂和平協議,雙方主帥要走進帳篷裡邊籤和平協議。但是誰先進?這是個問題。我尊敬你,你先進;我不尊敬你,我先進。但那個說我也不尊敬你。怎麼辦?雙方開始猜拳,用石頭剪刀布的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所以後來大家就討論說,很有可能提出這個建議的人,就是法國的主帥羅尚博,於是美國就把石頭剪刀布叫作羅尚博。
石頭剪刀布之所以有效啊,其實是自然界的規律。就你發現自然界就是靠石頭剪刀布的這套規則在維繫的,老虎吃雞、雞吃蟲、蟲啄棒子、棒子打老虎,形成了這麼一個迴圈。它有它的科學性存在,而且有隨機性。很多案例都是透過它來解決,猜拳是最簡單的方法。
就比如說,一個日本人要拍賣一幅畫,蘇富比和佳士得都想要。怎麼選呢?雙方提了好多提案,競爭的能力不相上下,這個老闆就很苦惱。他女兒在旁邊出主意,說讓他們卒瓦丁殼吧,卒瓦完了以後決定,就這麼簡單,解決了。所以不要小看卒瓦丁殼,它是能夠打破很多博弈困境的非常有效的方法。
大家看《非誠勿擾》裡邊葛優發明的那個東西,叫問題分歧終端解決機。兩個手塞在那個套裡邊,然後開啟。有它的理論意義,它使得卒瓦丁殼變得更加科學有效。這是一個很好玩的自行運轉的策略。
那如果遇到了更復雜的多方對決的狀況,該怎麼辦呢?這裡邊有一個案例,你們可以判斷一下。
這個案例很精彩,說三個邏輯學家討論一個問題的時候突然生氣了。生氣了以後怎麼辦呢?決定決鬥。邏輯學家決鬥就要有邏輯,所以他們就說,咱們拿槍出來決鬥。決鬥的方法是:槍法最差的人可以先開槍,這個人有1/3的命中機率;槍法第二差的人有1/2的命中機率,他第二個開槍;槍法最好的那個人,100%命中的,他最後一個開槍。這時候如果你是那個槍法最差的,有1/3命中機率的人,你該向誰開槍?你該先打那個槍法1/2準的,還是打那個最準的?
答案很簡單,你只要對空放一槍。效用最大。為什麼呢?你想想看,假如你砰打死了那個1/2準的,那你必死無疑了,因為剩下那個人一槍就給你打死了,你的死亡機率一下子變成了100%;假如你打死那個100%的,剩下那個人能打中50%,那你的死亡機率變成了50%。不論你打哪一個人,你最低的死亡機率都是50%。但是如果你對空鳴槍,把這個答案交給這個1/2的人來決定,1/2的人會打誰呢?1/2的人不管打誰,你的死亡機率都不會比50%更高,因為他既可能打那個100%的,也可能打你,就算他選擇打你也只有50%,何況還可能會選擇打他呢。
透過這個三方對決的模擬,你會發現,我們在多方博弈的過程當中,往往最有效的方法是讓他人先博弈。你要能夠學會退出來讓他人先博弈,你會成為那個受益者,“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就是這個道理。所以多方博弈的時候,你有很多不同的選擇,我們都免不了要跟別人丁殼。
各位想不想學一個卒瓦丁殼只贏不輸的策略,這招很靈啊。重點就在於:找出一個真正無法預測的隨機出拳策略,然後奉行無誤。
卒瓦丁殼的時候,最容易輸的狀況是你被別人看出了套路,別人一看你出,就知道你只出拳,完了;或者三次拳、一次布,不行不行,肯定完了。你的套路很有可能你都不知道,因為你會覺得自己是隨機出,但實際上你會有一個不自覺的套路,被對方觀察出來了,你就會輸。
而要保證你的輸的機率不超過五成,最有效的辦法就是你出拳是完全隨機的,那麼怎麼才能夠保證你出拳是完全隨機的呢?這個作者出了一個特別科學的招,他說你最好在腦子裡邊背過一個無限無規律的數字,就比如說π這樣的數字,3.1415926……背到一百位以後。
出拳的時候,要是你腦子數到的數字是1、2、3,就出石頭;如果是4、5、6,就出布;如果是7、8、9,就出剪刀;碰到0也出布。無非就是這幾種情況。你怎麼出石頭剪刀布,完全來自於你的密碼,這樣的話,對方完全不能夠猜測到你的規律,拿計算機來算都算不出來。因為它是一個無限不迴圈小數,記π也可以,記自然對數e也可以。哇我覺得好費勁哪,但是這個是科學有效的。
為什麼?你看這個統計就知道了,如果沒有這樣的損招,正常人出石頭的比例是35%,出布的比例是33%,出剪刀的比例是32%。大部分的人還是更願意出強硬的東西,石頭。那如果你想贏,你應該學會多出一點布和剪刀,少出一點石頭,你贏的機率可能會大一點。這個是用計算機算的,它肯定是對的,但是在生活當中你要不要真的這樣去做,那是另外一回事,因為它確實是一個需要很多的量的累積,才能夠出現效果的東西。
接下來我們說,除了石頭剪刀布這種自行運轉的策略之外,我們應該做的,就是透過溝通協商來建立聯盟,這才是解決博弈問題的最本質的東西。就是你發現如果我們真的相互信任,獵鹿問題也能解決,懦夫問題也能解決,志願者困境也能解決。前提是真的信任,真的形成了聯盟。
在動物界都有很多溝通的方法,這個作者說最有意思的是鯡魚,這種魚類溝通的方式是放屁。它在水裡邊放屁是有節奏的,透過這個節奏,它們之間達成一致,知道往哪兒遊,知道什麼地方有食物,哪兒有危險過來了。他說連一個鯡魚都知道要放屁來解決溝通問題。然後蜜蜂呢,大家知道跳8字舞,蜜蜂跳舞的路線代表著它的發現,這是蜜蜂的語言。
人類最樸素的溝通方法,或者說給我們帶來了很多傷害的溝通方法,就是威脅和獎勵。這個作者說有一次他在印度買東西,特別有意思,他說印度人把威脅和獎勵用到了極致。比如說他買一個衣服,八十塊錢。他們就很老實,給人一百,給了以後就發現不找錢。他也不跟你吵架,他說你再挑二十的。他們倆覺得太窩火了,然後這兩個英國人就學會了,假如對方說這衣服八十,那就給五十。對方說還差三十呢,不給了,你如果不願意賣,把五十還給我,我就走。最後他們發現這招經常會管用,這就是用威脅和獎勵來解決問題。你威脅我,等我有實力了我威脅你;你獎勵我,等我有實力了我獎勵你。
最有效的方法是建立聯盟。如果你能夠和對方建立一個聯盟,這些問題都能夠得到解決。“有一個叫作羅傑·A.麥凱恩的人說,‘成功的可能就在於,原則上只要各方能夠達成一個合作方案,任何非定和的博弈都能轉換成雙贏博弈。’要是辦得到的話,我還真想讓這句話從書上跳起來,並且加上音效,跑來跑去去大聲廣播,因為這正是我當初讀到這句話時,所感受到的震撼,我要找的就是如何讓社會困境能有雙贏的結局,而博弈論告訴我的確有法可循,只要建立起真正穩固的聯盟即可。”
要建立起聯盟,關鍵就在於信任。如果你能夠產生信任,問題就得到了解決。這裡邊有個很生動的案例,作者小時候過聖誕節,祖父母給他和他弟弟送禮物,結果開啟箱子發現送反了,就是他拿到了他弟弟的禮物,他弟弟拿到了他的禮物。然後說那你們倆換一下不就行了嗎?但是他們之間沒有信任呀,所以導致雙方都不撒手,哥哥也不撒手,弟弟也不撒手。我給了你,你萬一不給我怎麼辦?所以雙方陷入僵局,拿著對方的禮物又不想要,又不願意給對方。怎麼解決呢?這時候爸爸站出來做了一個可信的人,爸爸說你倆如果都不撒手,這兩個禮物誰都不給。他倆一聽,相信爸爸,撒手就交換。
一旦有了信任,你就會發現這個聯盟很容易建立。假如他們兩個人不合作,兩個人都要有巨大的損失。這就是在博弈當中引入第三方的好處,一旦第三方引入,聯盟的關係發生了改變,問題就解決了,這個叫作透過協商來建立聯盟的過程。
如果能夠形成這樣一個聯盟,最終會達成的解決方案就叫作帕累托最優。帕累托最優就是最省力也最有效率的一種狀態,處於帕累特最優當中的這幾個博弈方,沒有人有動力去改變目前的博弈結果,這就形成了一個短暫的帕累特最優。大家就都能夠沿著這個方式,沿著一套規矩去做。當然如果外部的條件在發生改變、在引入新的博弈方,格局就會發生改變。
關於這件事情的批評是什麼呢?大家對博弈論最大的批評,是覺得博弈論能夠解釋一切,所有有效的、無效的,結果好的、結果不好的,道德的、不道德的,博弈論專家說都是博弈論,它完全符合博弈論的作用。
我原來對博弈論有一個意見就在於,我覺得博弈論假設人性是理性的 ,它是經濟學嘛 ,經濟學假定人性是理性的。但是我們在生活當中,看到特別多非理性的行為,我為兄弟兩肋插刀!你看,都兩肋插刀了,它有什麼經濟性可言呢?生活當中的決策,很多是《思考,快與慢》的方式,丹尼爾·卡尼曼所研究的那個東西,心理學起到的作用比人的理性要多得多。
但這本書的作者說,這個狀況也是博弈論控制之內的。之所以有各種各樣截然不同的情況出現,就是因為效用完全不一樣。你在高階的博弈論當中一定要考慮到情緒的作用,而不僅僅是用囚徒困境那個簡單的模型。
就比如說有一個電視節目專門考驗這個。兩個人來參加遊戲,給A發一百塊錢,說你可以決定給B發多少錢,B如果要,你倆就各自拿著錢走;B如果不要,你們倆都一分錢也拿不到。這時候你想想看啊,A會怎麼想這個問題。一百塊錢,我給B一塊錢,你說你該不該要?你如果從理性的角度講,你肯定應該要,因為要也有一塊呀,你不要你連一塊錢都沒有,就這麼簡單。所以就有很多A就開始嘗試,給你一塊,或者給你十塊,給你三十,我留七十,等等。後來發現B的選擇往往是不要,就別說一塊、十塊,給30%有的人都翻臉。說我不要,憑什麼,咱倆一塊兒參加遊戲,憑什麼你拿七十我拿三十?走了。這就是情緒的作用。
在博弈的時候,經常會有這種不蒸饅頭爭口氣的狀況發生,它不是一個簡單的理性決策,所以博弈論會變得越來越複雜。
既然建立聯盟很重要,我們就要接著研究,建立聯盟的最大的困難在哪兒呢?就是信任。就是你怎麼能夠信任對方,這是很難的一件事。
這個作者特別調皮。他看歷史上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橋段,就有一次,伊麗莎白女王要下馬車,結果馬車旁邊有一灘泥水,不乾淨,女王穿那麼好看,怎麼能站在泥水裡邊呢?旁邊站著羅利爵士,立刻把自己外套脫下來鋪在那個泥灘上,讓女王踩上去。這成了歷史上的一段佳話,說你看,紳士風度就這樣。所以這個作者他要試一試,他就走在大街上,看到一個女士走過來,前面有個水坑,他就突然跑過去把衣服一脫,鋪在那個水坑上,然後看有多少女士能夠從他鋪的那個西裝上走過去。
他用這個東西測試什麼呢?他想測試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對於信任的感受。最早被報警抓是在美國,在美國一鋪,馬上就叫警察,說這個人騷擾我。人和人之間的信任就是這麼脆弱,你想學紳士風度就被人報警抓。
所以信任怎麼產生?從生理學上講,信任的產生是來自於催產素,就是如果我們體內能夠分泌很多催產素,我們更容易相信別人。我們專門講過一本書叫《感受愛》,如果你不知道催產素是怎麼回事,你去聽一下《感受愛》那本書。你就瞭解說被別人愛的感覺會讓你分泌催產素,而催產素會帶來信任。甚至有人做過實驗,在一種香薰裡邊加入催產素,噴在屋子當中;另外一個屋子裡邊沒有。然後給他們做同樣的實驗,就發現噴了催產素這一組的屋子,更多人選擇相信;而另外一組更多人選擇懷疑。所以這種激素對人的作用是很大的。
不信任是風險導向策略,信任是報酬導向策略,不信任更接近於我們原始的本性。你在原始社會當中生活的時候,風險太大了,到處都是風險,所以你一天到晚都要保護自己。睡覺的時候都要枕戈待旦,都要拿著武器,就在於你是周圍全被風險籠罩的。但是如果一個人完全跟別人不合作,你也沒法生存下去。信任是原始人類後天發展出來的東西,因為你要跟別人一塊兒打老虎、一塊兒打大象,必須得團隊合作,所以後來出現了報酬導向機制。就是我信任了你,咱們團結,我們會獲得收益。
但是這個風險導向的策略,也就是不信任,是我們體內最本質的東西。所以要想獲得信任別人的能力,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我們經常講信任別人是一個能力,我也講過一段話,有人覺得這話說得不對,但是我至今都覺得這話有它一定的道理,就是好多人都整天很緊張,怕被騙,但其實在我們的生活當中,被騙的成本和信任的成本比起來,哪個更高?其實被騙的成本是有限的,因為你被騙了,以後你就知道了,下次離開這個人,不願意跟他再合作了。你就吃一次虧,認清了一個人,很划算。但如果你什麼都不信任,這個人我也不信任、那個人我也不信任,這個團隊我也不信任、老闆我也不信任,你付出的成本可能是終身的。
信任是需要我們在後天慢慢培養起來的能力,如果你不把被騙當作是輸贏來看待的話,其實它也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書裡邊總結了一些典型的騙局。比如說場外贏家策略。你有一天路過一個賭場,裡邊衝過來一個人,給你一大厚摞籌碼,然後告訴你說:我現在被賭場趕出來了,我特厲害,贏了很多籌碼,但我去兌這個沒法兌。你是個生面孔,你進去兌就能兌出錢來,給你。你說哎這挺好,兌出錢來大家分。但是你得給我押點錢,要不然你拿走我這麼多籌碼不分我錢怎麼辦。一驗,籌碼是真的,行。他不是有同夥嘛,告訴你是真的。再加上他搞得神秘兮兮的,很緊張,你也不敢一個一個地驗。後來你把錢包押給他,拿著籌碼進去,發現全是假的。
這種騙局屢見不鮮。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就是你撿錢包,走著走著,前面那個人掉下來一摞錢,搞得你好緊張,心臟狂跳,你覺得發財的機會到了。突然出現一個人把你拉到一邊商量,說錢給你,你給我二百我就走。但其實地上那些錢是假的,你給的錢卻是真的。又被騙二百。這種騙局叫作賭場外的贏家。
還有典型的網路騙局:我讓你知道我藏了一筆錢在一個地方,但是我拿不出來,現在你得幫我。甚至有人冒充是歷史上的人,我都覺得這事不可思議。稍微有點常識的人都會知道,那個人死了兩百年了,但是他會告訴你說:我就是那人,我藏了一筆錢。竟然還有人上當受騙,原因很簡單,他用那個很誇張的前提在篩選被騙的物件,我跟你說我是歷史上的人你都願意相信,那你就是我的菜,然後想辦法騙你。
第三種叫浪漫陷阱。有人會覺得自己找到了愛人,但這個愛人其實是個酒託,帶你去吃飯、喝酒、花很多錢,騙你的錢。甚至嚴重的說我要創業,然後從你手裡邊掏錢。這都是典型的騙局。
我們需要增加的不是防範別人的心理,防範別人的心理我們已經足夠多了;我們需要學習的是這些案例。如果我們能夠學會從這些案例當中找到經驗,我們知道騙人就這麼幾種套路,你搞清楚了,然後你才能夠比較明智地、開放地對待其他更多的人。
我們要變得更明智,不要放棄相信別人。有的人被人騙了一次以後的反應就是:我以後誰都不信,誰都不信的結果是你把自己封閉起來了,你沒有了任何機會。而這個社會上其實好人是大多數,但你因為被騙了一次,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放棄了對所有人的信任。完了,被騙一次成了終身的遺憾,他不但騙了你的錢,還毀了你的人生。這才是最要命的。
所以信任別人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能力,前提是你要學習。
怎麼才能夠讓博弈雙方產生可信的承諾呢?兩招。第一招叫作反悔的代價極高。比如說,我們大家在一起二十年的朋友了,我們都是校友,都從一個學校裡邊出來的,我們共同認識的人至少有兩百多個,這時候你騙我,成本高不高?你騙了我以後,雖然沒有抵押,但是我只要把這個事說出來,你所有人脈關係全都沒有了。這就是為什麼在生活當中容易相信熟人的原因,他的成本代價更大。
但是你也還是要小心,我也見過一個人把自己幾十個億的財產託付給一個人打理,最後那個人卷錢跑了。就是他衡量了一下,我損失了所有的聲譽,但是我也夠了,幾十億呀。所以你要想,這兩個要均衡。
還包括中國古代,你比如說秦始皇為什麼被放到那邊做質子呢?質子就是代價呀,如果你要背叛我,你的代價就是你的孩子命都沒有了。這就是最原始的博弈的方法,就是讓反悔的代價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