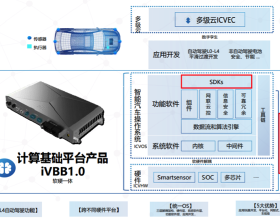在中國, 要不要回小城辦一場婚禮?怎麼辦?接受辦一場“爹味”婚禮嗎?這也是現在很多年輕人的普遍困境。在北上廣工作、生活的他們,即便是已經在這裡辦過一場草坪婚禮,或是簡單宴請了同事,也免不了回到老家再辦一場,這似乎是父母們約定俗成、心照不宣的“默契”——年輕人們,必須要辦一場爸媽需要的婚禮。
文 | 丁文捷
編輯 | 金匝
運營 | 田寶
“我不打算回老家辦婚禮”
“我不打算回老家辦婚禮。”穆言在電話裡向父母發起反抗時,她感覺到氣氛已經掉到了冰點。
29歲的穆言來自山西的一個小縣城,她和男朋友都在上海工作,兩人達成結婚意願後的第一個月裡,她需要每天在下班回家之後,花費三四個小時和自己遠在縣城的父母電話溝通,試圖說服他們接受自己不在老家辦婚禮的決定。一通操作下來,掛掉電話時,通常已經是過了午夜12點。
穆言之所以對小城婚禮極為抗拒,是因為在那個地方,她親身經歷過太多的怪誕現場。
縣城的小路總是很窄,婚車會停在大馬路邊,新娘抬腳離開家走向婚車時,她的父母會潑上一盆水,意味著“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等新娘走後,母親又必須大哭一場,因為“從此女兒就是別人家的人”。
▲ 圖 / 《魔都風雲》劇照
每次看到這樣的場景,穆言總會有一種從頭傳導到腳的不適感。她並不知道這些儀式的由來、具體名稱,但那些場面深深刺激了她。後來,她讀大學,在上海找到一份工作,有了更多的女性意識,開始能準確地瞭解到自己不適的原因:不管是婚禮上的潑水還是哭泣,都充滿了一種女性被圍觀、被凝視的感覺。
穆言將這些類似的婚禮瞬間,命名為小城婚禮上的“爹味”時刻。
她總結過,一個小城婚禮,彷彿就是昭告天下,女性已經離開自己的原生家庭,從此歸屬於另一個,所有人都在慶賀,但沒有人在意女性自己的感受。更多的時候,她們被精心打扮,在這樣喜結良緣的儀式上,走馬燈一樣地配合別人。
正是這種婚禮上的“爹味”時刻,讓穆言下定決心逃離,不再配合別人的表演。
在中國, 要不要回小城辦一場婚禮?怎麼辦?接受辦一場“爹味”婚禮嗎?這也是現在很多年輕人的普遍困境。在北上廣工作、生活的他們,即便是已經在這裡辦過一場草坪婚禮,或是簡單宴請了同事,也免不了回到老家再辦一場,這似乎是父母們約定俗成、心照不宣的“默契”——年輕人們,必須要辦一場爸媽需要的婚禮。
穆言生活在老家山西的母親,就格外看重小城婚禮。她的母親是當地老年舞蹈隊隊長,能歌善舞,經常出現在各種的婚禮現場,圍繞著新人們跳舞,將他們簇擁在中間,沿途的街坊領居也會聞聲擠到小路上來湊熱鬧,這種喜慶而和諧的氛圍讓母親覺得“這場婚姻在當地擁有了合法性”,她需要女兒婚禮的儀式感,來給周圍的親戚朋友一個交代。
“因為她生活在那個環境當中,可能會面對很多人情的壓力,所以她自然需要來自周圍人的認可。”穆言理解母親的想法,但又很難去遵守她的意志。
不尊重,不管是女性還是男性
小城“爹味”婚禮,能一路從接親延宕到婚禮現場,甚至綿延到婚房。
對剛滿26歲的瑾夏來說,婚禮是一項還離得很遠的日程。去年6月,她才研究生畢業,計劃是這兩年想先把工作弄好,在濟南穩定下來,等29歲之後再考慮辦婚禮這件事。但最近一次的經歷,讓她覺得自己有了婚禮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
那一次是瑾夏去參加別人的婚禮,婚車行駛到一半時,整個迎親車隊毫無徵兆地停了下來。
瑾夏開啟車窗探頭張望,只見新郎上半身穿著紅色內衣,下半身套著紅色絲襪,在大馬路上狂奔,後面緊跟著一群伴郎,手裡拿著麵粉、醬油和醋,試圖往新郎身上澆。雙方大約拉扯了三四百米,新郎被紅色絲襪絆倒在路邊,伴郎們彷彿看見獵物的野獸,猛地蜂擁而上,幾分鐘之後,麵粉與醬油的混合物糊在了新郎身上,連一根頭髮絲都沒能倖免。
“我當時都有點嚇傻了,這到底算習俗還是陋習?”這是成年後的瑾夏第一次參加婚禮,身為一個北方人,她原本對南方的婚禮習俗懷有天然的好奇,但那天,在四川成都周邊的一個縣城裡,同學侄子的這場婚禮讓她大開眼界,“原來討一個好彩頭,能鬧成這樣?”
穆言也有類似的經歷,在山西小城,新郎、新娘走向婚車的那段小路,他們的父母會頭戴紅冠,臉上塗著紅白油彩,看起來像是小丑的模樣,更誇張的,還會有人在脖子上掛上粉氣球和青辣椒。而周圍的鄰里朋友,則會紛紛往他們身上抹一些類似鞋油的東西來湊熱鬧,抹得越多,意味著越喜慶。
雖然婚鬧並沒有直接波及到瑾夏,但紅色絲襪、紅色內衣,這種極富女性色彩的物件,還是透過視覺刺激到了她的神經,“還是覺得不尊重人,不管是女性還是男性”。
▲ 包貝爾婚禮上的婚鬧。圖 / 微博
瑾夏不知道的是,兩千多公里外的吉林省伊通滿族自治縣,一個北方小城,相似的情節也在上演。
19歲的皮桃看見表姐坐在婚床中間,周圍散落的是棗子、花生、桂圓和蓮子,寓意很明顯,早生貴子。一輪又一輪無厘頭的捉弄遊戲後,她以為接親環節終於告一段落,這時,一位女性長輩突然端出了一盆透明的液體,一股辛辣而刺鼻的氣味頓時湧入皮桃的鼻腔,嗅覺告訴她,這是“大蔥水”。
“大蔥水洗手,生孩子聰明。”這位長輩一邊說,一邊示意新人該怎麼做,那股小心翼翼的勁兒,讓皮桃覺得“長輩們是真的相信這些”。她有些震驚,上一次眼前出現這樣的場面還是在父母婚禮的照片上,頓時她產生了一種時空穿越的感覺,“怎麼過去了近二十年,這種儀式還保留著?”
對著攝影師架起的鏡頭,表姐笑得很燦爛,可鏡頭一轉,皮桃還是發現了她表情中的疲憊。在這段感情之前,皮桃28歲的表姐剛因為異地而結束了一段長達十年的戀情。在皮桃看來,長輩們的“花式催婚”,是推動表姐和她的先生快速進入人生新階段的“主導因素”。
活躍的司儀,隱身的媽媽
在小城,一場“爹味”婚禮的承接者,往往是當地婚慶公司裡的“金牌”司儀。
司儀的受歡迎程度,決定了他們的檔期和價格。“金牌”司儀能說會道,又深諳各種婚俗,在操辦婚宴這件事上,深受長輩們信任。皮桃表姐的這場婚禮,就是由小城最好的婚慶公司全程負責,總共花費了5萬元,包括場地、策劃等,其中司儀的價格近4千元,佔了8%。
“司儀也是分檔位的,有高、中、低三個檔次。”據皮桃瞭解,當地司儀的價格在1000元到6000元不等,一般高檔的價格為3000元到5000元左右,如果有錢人家想要辦得更風光一些,就會邀請本地小有名氣的主持,一場下來單司儀的費用就會過萬。
作為婚禮上實實在在的局外人,司儀卻總在不斷怒刷存在感。“新郎家的飯好不好吃?” “新郎家的床軟不軟?”看著司儀在臺上打趣新娘、活躍氣氛,站在一側的阿湯“尷尬到可以用腳摳出三室一廳”,她是00後,接受的教育從來是尊重和平等,她不明白這樣的司儀存在的意義是什麼,“難道就是讓新娘難堪嗎?”
除了尷尬,皮桃也感受到了這些儀式裡過時的氣息。“感謝新娘父母多年來的辛苦培養,把自己至親的女兒親手託付給他。”“新娘遇到了她一生中的唯一。”“恭喜新娘在今天成為了X太太。”婚宴上,諸如此類的話,司儀說了一遍又一遍,他試圖營造溫馨氛圍,卻實實在在地刺激了皮桃的神經。“這些話的底層意思,讓人覺得新娘彷彿一個物品似的,還能這麼來回給,自己沒什麼能動性。”
而對於新娘本人的實際感受,司儀好像並不在意,他頻繁地詢問著男方結婚的心情、當下的體驗,似乎在他的經驗中,新娘在這一刻能感受到的除了幸福,還是幸福。
連父母也會配合這樣的“爹味”時刻,佟麗婭的父親就在《快樂大本營》上有過這樣一段發言:“我今天就把我的女兒,交給老陳家了,希望到了老陳家以後,多幹些活......”那是2014年年末,節目組為佟麗婭和陳思成補辦了一場中式婚禮,佟麗婭父親的這番話,也同樣引起過阿湯的不適。
▲ 圖 / 《快樂大本營》
在這樣的儀式中,隱身的除了新娘,還有新娘的母親。從小到大,阿湯頻繁出入各類婚禮現場,面對大人們習以為常的事情,她總會懷有好奇:“為什麼新娘一直是由爸爸牽著入場,交到新郎手中,那個時候媽媽在幹什麼?”
原本,阿湯以為新娘的母親在為更重要的事情忙碌,直到有一次,她託著表姐的婚紗,跟在後面走上T型舞臺,在一堆舉起鏡頭的親戚朋友中,她注意到,姑媽看著女兒挽著父親的背影,自己躲到一旁,悄悄抹了眼淚。
後來,她聽說有一些新娘因為父親去世得早,無法牽著自己入場,而會請家中其他的男性長輩代為承擔父親的角色。她更加疑惑,“為什麼牽著新娘的手入場的人,不能是媽媽呢?她明明也是很重要的人啊!”而除了這個環節,在婚禮上作為家長代表發言的,也幾乎都是父親。成年以後,阿湯從花童晉級為伴娘,可對於“母親的隱身”卻始終沒人能解釋得清楚,她發現“大家都只是學著前人的樣子,繼續延續下去罷了”。
一場體面的婚禮,在許多長輩眼中是子女一生的大事,也是自己應盡的責任。
穆言記得,將近十年之前哥哥結婚,除了高規格的婚宴之外,還有嫂子的彩禮、婚房的裝修,是一筆鉅額花銷。“這筆錢其實是超出了父母的承受能力,所以當時他們還去貸款、借錢,還了好多年才終於還上。”結婚之後,哥哥搬去了自己的新家,只剩穆言還和父母同處一個屋簷下,在生活的瑣碎中,她感受到了這件事情給父母帶來的壓力。
“為了這種面子工程,自己還要在家吃糠咽菜,我覺得這是一件完全不划算的事情。”明明是一家人,哥哥作為兒子,似乎很享受婚禮上的高光時刻,而作為女兒的穆言看到了父母更多的不易。可母親仍將“讓女兒風光出嫁”這件事情,當成她的為人母的“任務”她老年生活的重要支點。
得知穆言和男朋友有結婚的打算之後,母親常會念叨“一想到你要出嫁,我就要掉眼淚了”。好像從此她將不再屬於這個家,每次聽到這句話,穆言都會聯想起婚禮上司儀刻意編織的“煽情陷阱”。女方家長泣不成聲,男方家長紅光滿面,耳邊傳來司儀事先準備好的尷尬臺詞,這樣的場景如果換上自己的母親會怎樣?她無法想象,只想極力逃避。
誰會勝利?
2022年一開年,穆言和戀愛多年的男友在上海領了結婚證,母親暫時沒有再進一步逼迫她辦婚禮了,但這並不意味著她的反抗有了結果,她將這個方法總結為:“用魔法打敗魔法。”因為領證的日子,還是母親來定的。
母親是一個特別傳統的人,在她的觀念裡,結婚一定要挑個好日子。“當時她找人,根據我和男友的屬相,算了合適的結婚日期,但發現虎年一整年都不合適。最終快速促成我倆在過年之前領證。”
可穆言發現,就算是已經領了證,母親內心對於她不辦婚禮的芥蒂絲毫沒有消減。因為少了提親、雙方父母見面商議等流程,在母親看來,她們這小夫妻的婚姻過於草率了。“沒有一個女性是不想辦婚禮的,結婚這一天是女人最幸福、最美的一天。”這是一直以來存在於母親腦中的刻板印象,這個儀式於她而言,除了能給親戚朋友一個交代,履行為人父母的責任之外,還代表著一種承諾和保證,是安全感的來源。
但在穆言這裡,只剩下壓力。母親至今仍在刺探,她不敢相信這個決定是穆言發自內心做出的。“她總是各種旁敲側擊,問我是不是受什麼委屈了,是不是男方家不重視我,不願意大操大辦,我不敢跟她說,才找藉口說自己不想辦。”
事實上,穆言對婚禮的抗拒,很大程度上來自對母親命運的惋惜。她是一個要強又聰明的人,幾乎一個人主外又主內地支撐起一個家,父親至今連衣服都不會買。他們被包辦婚姻繫結在一起,母親因此承受很多不幸,無數次想過離婚、離開家到外面做生意,有幾次都已經走出去了,又被親戚以兩個孩子沒人管、女人不能不顧家為由勸了回來。
穆言常常會想,以母親的能力,如果有機會讀書、外出闖蕩,一定會過著完全不同的一生。因此她更反感婚禮上那些包裝成祝福和習俗的、對女人就要生兒育女、相夫教子的規訓
然而當她把這些想法告訴母親,鼓勵母親不要再為女兒的嫁妝和買房錢發愁,也不用時刻準備著帶外孫,可以過跳跳舞、做做飯的輕鬆日子,坦然地享受生活,母親的反應卻是:“我知道我給你攢的那幾萬塊錢你已經看不上了”“你是不是嫌我沒文化、沒見識,怕我在婚禮上給你丟人了才不想辦”。
“我想解放她,但她卻認為我要革她的命。”穆言這樣總結她和母親之間由婚禮引發的分歧。
自從得知穆言計劃結婚的訊息,母親的第一反應就是開始縫紅棉被,並裝在大紅行李箱裡給穆言寄到了上海。上海的冬天,空氣陰冷潮溼,7斤的棉花被子極易吸水,變得又重又溼,難以使用。雖然不合適,但穆言也不忍心拒絕母親一針一線縫製的心意。為此,她還需要特地整理出一半的衣櫃,來放置這些紅棉被和母親寄來的大紅色行李箱以及床上用品,本就狹小的空間一下變得更擁擠了。
每次看到父母的這些心意,穆言的腦中也閃現過一個折中方案,請親戚們吃一頓飯,把婚禮的流程儘量簡化,也算給他們一個交代。但剛開了這個口,母親就開始想盡辦法說服她:“這個環節不能省,那個環節也要留下,什麼都不能捨棄,最後又變成了那種傳統規格的婚宴。”這和穆言的想象完全不一樣,她立刻改口,回到了自己最初的想法。
最激烈的一次,電話那頭母親開始帶著哭腔大喊大叫:“我的女兒工作也很好,學歷也很高,也沒有比別人缺胳膊少腿,為什麼別人的女兒都能風風光光出嫁,我的女兒卻要偷偷摸摸地嫁人?”自此之後,穆言更加深刻地認識到,這是一件很難調和的事情,因為“兩代人對於婚姻這件事的底層認知就不同”。
如今,疫情成了雙方的緩衝劑,母女兩人圍繞婚禮的對峙仍在持續,但穆言知道,短時間內達成相互理解,不太可能。“最後只能是透過一個暴力革命的方式,要不就是他們鎮壓了我,要不就是我鎮壓了他們。”
▲ 圖 / 《不要戀愛要結婚》
(文中涉及採訪物件均為化名)
文章為每日人物原創,侵權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