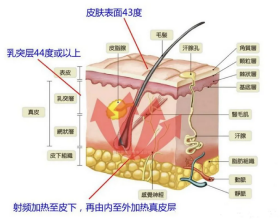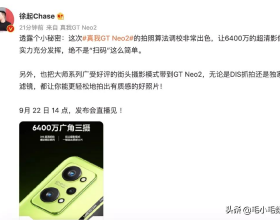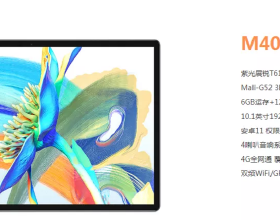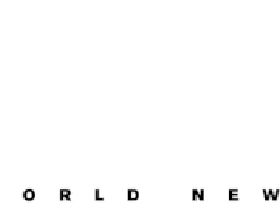彭總從被動中奪取了戰爭的主動權,迫使麥克阿瑟由主動轉為被動
在戰爭中誰掌握了主動權,誰就能夠取得戰爭的勝利。毛澤東說:“無論處於怎樣複雜、嚴重、慘酷的環境,軍事指導者首先需要的是獨立自主地組織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敵逼迫到被動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是要迅速地恢復主動地位。(引自毛澤東著(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在古今中外戰爭史上,以少勝多、以弱勝強、以劣勝優的諸多戰例中,除客觀因素外,指揮戰爭的統帥的主觀指導能力往往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在某種意義上說,戰爭是敵我雙方統帥的智慧,經驗、韜略和戰爭指揮藝術的競賽和較量。指揮戰爭的統帥要善於知己知彼、趨利避害;善於發揮自己的長處,利用和擴大敵人的弱點的短處;善於掌握戰爭中瞬息萬變的情況,迅速果斷地定下符合客觀情況的決心和處置。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之初,麥克阿瑟完全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我軍處於極為被動的局面,彭總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迅速從麥克阿瑟手中奪取了戰爭的主動權,使麥克阿瑟由主動進攻被迫迅速轉為退卻,並且從鴨綠江邊一直退到“三八線’’以南。
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以前,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確定我軍的作戰方針是:進到朝鮮平壤至元山以北的蜂腰部,佔領有利地形,組織防禦,構築二到三道防禦陣地,制止敵人的進攻,掩護朝鮮人民軍後撤整頓;並佔領北部山區,作為根據地,為爾後進攻創造條件。
可是,我軍進入朝鮮時,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且是急劇的變化,1950年10月19日晚,我軍跨過鴨綠江,敵人已於同一天白晝進佔了平壤,並迅速向北冒進, 已先於志願軍進佔了我預定的防禦地區,敵人的先頭部隊已進犯到鴨綠江邊,迫使我軍已不可能搶佔預定地區組織防禦了。過去我軍所運用的初戰必勝的條件,都變成對我不利,也不可能“寧可退讓,持重以待”(引自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了,因為在朝鮮境內已無地可退讓了。在這種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彭總於10月21日(我軍入朝後的第二天)即迅速果斷地放棄原定計劃,決心以運動戰方式殲滅冒進之敵。並即建議毛澤東主席令66軍、50軍迅速入朝參戰,使我入朝兵力由4個軍(38、39、40、42軍)增加至6個軍。同時建議中央軍委、毛澤東主席令第9兵團3個軍(20、26、27軍)迅速入朝,從輯安(今集安)過江,進至朝鮮東部,抗擊從咸興登陸進犯的美軍第10軍。
彭總並迅速調整部署,在區域性在區集中優勢兵力,抓住麥克阿瑟判斷的錯誤、分兵冒進的弱點,充分發揮我軍善於夜戰、近戰和包圍迂迴作戰的特長,力爭迅速地從被動中奪取主動。 彭德懷司令員將10月21日改變決心電報報告毛澤東主席。同一天(10月21日),毛澤東也電令彭德懷放棄原定作戰計劃,改為從運動中殲敵的方針,全軍最高統帥和戰區統帥的決心不謀而合,真是英雄所見略同!
從10月25日我軍第40軍在溫井、兩水洞地區與敵人遭迂打響後,在短短的12個晝夜裡,彭總根據瞬息萬變的情況,適時果斷地改變殲敵決心,調整部署,完成戰役展開。首殲溫井、熙川地區之南朝鮮軍,繼殲雲山之美軍,並運用戰役戰術上的迂迴包圍,把美第8集團軍打得暈頭轉向,迫使敵人由瘋狂地向北進攻,迅速地轉變為向清川江以南敗退。當11月3日敵人退過清川江以南後,彭總審時度勢,乘我軍意圖和兵力尚未完全暴露,為保持下一步作戰的主動權,於11月5日下令停止進攻追擊敵人,結束第1次戰役。我軍取得了初戰的偉大勝利。在新的情況下,彭總創造性地發展了初戰的軍事理論,豐富了毛澤東軍事思想寶庫。
我軍將敵人打退到清川江以南後,為了奪回戰爭的主動權,“麥克阿瑟這時在戰術上犯了他軍事生涯中最嚴重的錯誤。他一方面大大過低地估計了北朝鮮的中國人,另一方面又大大過高估計了飛機進行阻止的能力”。(引自美國小克萊·布萊爾著(麥克阿瑟)一書)。麥克阿瑟於11月6日命令遠東空軍1000餘架飛機全部出動,企圖以其絕對優勢的空軍發動空中攻勢, “消滅中國的干涉軍”。經過半個月對朝鮮北部和鴨綠江沿岸的狂轟濫炸,麥克阿瑟錯誤地“相信全面的空中進攻已達到了其目的”。認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是一種政治訛詐”、“不堪一擊”(以上均引自<麥克阿瑟)一書)。他傲氣十足地於11月24日由東京飛到朝鮮清川江以南新安州第8集團軍司令部,命令第8集團軍和第10軍向鴨綠江、圖們江進攻,揚言:“戰爭在兩個星期之內就會結束”,(引自李奇微著(朝鮮戰爭)),他計程車兵可以回國過聖誕節。
彭總抓住了麥克阿瑟想急於奪回戰爭主動權和急於求得勝利的心理,“採取了故意示弱、縱敵、驕敵和誘敵深入”(引自《彭德懷自述》)的方針,造成麥克阿瑟更大的錯覺。彭總則迅速、隱蔽地調整我軍的戰役部署,引誘敵人進至我預定作戰地區。在敵人發起攻勢的第2天,即11月25日黃昏,指揮西線我軍向敵軍突然實施戰役反擊,東線我第9兵團於11月27日向敵軍突然發起戰役反擊。
由於我軍出敵不意地反擊,又把麥克阿瑟打得不知所措,作為一個戰區統帥他已完全失去自我控制了,11月28日麥克阿瑟不顧前線最緊張的時刻,指揮官是不能離位的原則,緊急召第8集團軍司令沃克和第10軍軍長阿爾蒙德到東京開會,決定第8集團軍迅速向後撤退,要求“沃克撤往可以最有效保護他的部隊的任何地方(仁川或者釜山等等)”第10軍“阿爾蒙德撤至咸興、興南一線”,然後從海上撤退。麥克阿瑟的“聖誕攻勢”很快就被我軍粉碎,麥克阿瑟不僅沒有奪回戰爭的主動權,不僅沒有取得速勝,結束朝鮮戰爭,而且丟失了戰爭的主動權,完全處於被動了。被我軍打得大敗,退逃了。
敵人退到“三八線”以南地區,構築縱深防禦陣地,企圖阻止我軍的進攻。美國政府則企圖利用“三八線”為分界線,提出停戰談判的要求,企圖使部隊爭取喘息和整頓的時間,然後發動進攻,奪回戰爭的主動權。當時我軍因連續作戰部隊都很疲勞,戰鬥減員未得到補充,糧食、彈藥和物資也沒有完全補足,很需要休整補充。原來彭總的意圖是爭取2個月的時間,在“三八線’’以北稍作休整、補充,再繼續作戰。
毛澤東主席根據政治軍事上的需要,電令志願軍不要讓敵人停止在‘‘三八線’’上,要求我軍發揚不怕苦、不怕累的連續作戰的優良傳統作風,繼續組織進攻戰役,突破“三八線”,將戰線推進到“三八線’’以南去。彭總遵照毛澤東的電令,根據政治上的需要,決心克服一切困難,以西線中國人民志願軍6個軍和朝鮮人民軍3個軍團,實施突破“三八線”的第3次戰役。彭總充分考慮到我軍後方供應線太長,又遭受敵人的飛機的狂轟濫炸,如果再向前推進過遠,困難就會更大,為確保戰爭的主動權,彭總經過深思熟慮,確定這次戰役是“穩進”的方針,即突破“三八線’’敵人防禦陣地後,殲滅敵人,適可而止。1951年元旦,敵人全線敗退,新上任的美第8集團軍司令李奇微中將,為了避免他的前任所遭受的打擊重演,決心放棄漢城並向漢江以南撤退。我軍於1月4日收復漢城。彭總為了不使敵人據守漢江南岸,即令各軍越過漢江,向仁川、水原和橫城追擊。到1月8日,我軍將退逃之敵驅逐至北緯37度線以南。
在勝利的追擊中,彭總的頭腦非常清醒,認為雖然取得了突破“三八線”的重大勝利,但並沒有大量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
敵人退過漢江後,李奇微即迅速收攏和整頓部隊,麥克阿瑟則企圖誘我窮追,再來一次“仁川登陸”。彭總洞察了敵人的陰謀,果斷地停止追擊,結束第3次戰役。令韓先楚副司令員率志司“前指”,指揮第38軍、第50軍和人民軍第1軍團,在漢江南岸組織野戰防禦,監視敵人,防止敵人反撲。主力在漢江北岸休整,補充糧彈。
彭總這一著是很有戰略預見的,但遭到蘇聯駐朝鮮大使拉佐瓦耶夫和有的同志的反對。彭總堅決頂住了,並得到毛澤東、斯大林的支援。事實很快證明彭總的決斷完全正確。
美第8集團軍司令李奇微將退逃之美軍和南朝鮮軍稍事整頓,即於1951年1月15日,以所謂“磁性戰術”,向我軍發動了試探性進攻。25日開始,全線向我發動了較大規模的進攻,企圖奪回戰爭的主動權。這時,我軍已爭取休整了近20天,體力有了恢復,糧彈得到了部分補充。
為了掌握戰爭的主動權,彭總於1951年1月27日下令停止休整,調整部署,在西線,漢江南岸繼續進行防禦,遲滯敵人進攻;在東線,由鄧華副司令員率前指,指揮中國人民志願軍4個軍,在朝鮮人民軍2個軍團的協同配合下,選擇敵人的薄弱部和突出部,實施了第4次戰役,向敵人發動橫城反擊戰,殲滅了敵人。敵人迅速向我軍進行反撲,我軍遂結束第4次戰役,轉入機動防禦,遲滯敵人的進攻,盡最大可能爭取更多的時間,使新入朝參戰的第3,第19兵團向前開進,在東線的第9兵團完成休整後,南下參戰。然後向敵人發動了第5次戰役,戰役進行2個階段。至1951年6月,美國及其盟國政府都認識到不可能在朝鮮戰勝中國人民志願軍,因此,被迫提出停戰談判。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毛澤東主席和彭德懷司令員都認識到在當時我國綜合國力和我軍的情況,也不可能將敵人全部殲滅或趕出朝鮮。因此,同意與美軍進行停戰談判。但要求中國人民志願軍則不要寄希望於談判。而應實行積極的戰略防禦,持久作戰。並明確指出,戰爭的勝利只能是從戰場上打出來,不可能從談判桌上談出來。
在敵我雙方都轉入戰略防禦作戰中,敵人與我軍正面相持對壘兩年多,雙方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戰鬥、戰役的較量,我軍愈戰愈強愈主動,敵人則愈戰愈被動。在我軍戰略防禦作戰中,戰爭的主動權最後又被我軍奪取,從而使敵人完全處於被動,敵人不得不急於在1953年7月27日,在軍事停戰協定上簽字。
彭總趨利避害, 以己之長,擊敵之短,使麥克阿瑟的優勢對我軍無可奈何
在古今中外的戰爭史上,能以少勝多,以弱勝強,以劣勝優的統帥,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能夠高瞻遠矚,冷靜客觀地分析敵我情況,巧妙地採取計謀,趨利避害,以己之長,擊敵之短。就連麥克阿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太平洋對日軍的作戰中,也有過這樣的戰例,在其侵朝戰爭初期,他力排眾議,親自選擇和指揮美第10軍在不宜於登陸的仁川港實施登陸,一舉成功,使他成為“英雄”。可當他面對著中國人民志願軍的統帥彭德懷時,就顯得很笨拙了。
麥克阿瑟統率的“聯合國軍”,是高度現代化、機械化的陸軍,和佔絕對優勢的空、海軍。而彭德懷統率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當時只有步兵和少量炮兵,行動靠兩條腿,既沒有空、海軍支援和掩護,又沒有足夠的對空防禦武器,完全暴露在佔絕對優勢的敵人空軍的空襲下。在這樣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又加上在朝鮮這樣狹長的半島上,迴旋餘地太小,又不能就地得到補給,按照一般的軍事原理和戰爭理論,我軍的“小米加步槍”怎麼能和高度現代化的進行立體戰爭的對手進行較量呢?更不要說能戰勝敵人了,但是,在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領導下、在聰睿、膽略超群的彭德懷統率下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充分發揮了指戰員勇敢、機智和具有豐富的戰爭經驗的優勢,硬是使麥克阿瑟的優勢發揮不出來,達不到他所期望的目的。而我軍的優勢卻得到了充分的發揚,迫使麥克阿瑟統率的高度現代化的陸海空軍的“聯合國軍”,接二連三地敗下陣來。
麥克阿瑟遭到我軍第1次戰役的打擊後,仍驕傲自大,輕視我軍,認為以絕對優勢的空軍,就可以打敗我軍,遂命令遠東空軍,於11月8日開始,向我實施了空中戰役,每日出動上千架次的飛機,飛向我鴨綠江邊炸斷中、朝共有的鴨綠江橋,並不顧國際公約,悍然轟炸我國鴨綠江邊的安東市(即丹東市),企圖阻止我軍後續部隊和後方支援物資輸送入朝,並企圖對我國進行武力恫嚇。同時對朝鮮清川江以北所有的交通運輸線、城市和村莊、工廠和一般設施進行全面摧毀。即所謂地毯式的轟炸。
毛澤東和彭德懷從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是戰鬥力諸因素的首要因素,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出發,採取另一種方式來對抗麥克阿瑟的空中攻勢。毛澤東主席和彭總命令部隊完全轉入夜間活動,行軍在夜間,運輸在夜間,拂晚前部隊即進入松樹林子裡隱蔽。開始沒有將汽車、馬車、炮車車軲輪的撤跡去掉,被敵人飛機發現,遭到轟炸掃射,我各級指揮機關和指戰員,就迅速研究在車輛後拖樹枝,將撤跡掃去;白天做飯、燒開水冒煙易被動敵機發現挨轟炸,就規定每天三頓飯和開水都在夜間做好,白天不準冒煙。
我軍採取了各種各樣的防空措施,較大地減少了損失,並隱蔽地進行了戰役、戰鬥的部署調整。
我軍採取這些巧妙地隱蔽行動,迷惑了敵人,把麥克阿瑟搞糊塗了,使他產生了錯誤的判斷。認為持續了兩個星期的空中轟炸襲擊,使“中國人似乎在全線撤退”,相信已經達到了摧毀我軍的目的。麥克阿瑟便決定11月24日,即美國人的感恩節的第二天為進攻日。可是實際情況正如<麥克阿瑟》一書的作者(美國小克萊·布萊爾),對麥克阿瑟空中攻勢的描述:“空中攻勢幾乎沒有恫嚇住他們。這些經驗豐富計程車兵輕裝前進,利用夜暗行軍,白天則小心地隱蔽起來。對北朝鮮的狂轟濫炸,殺死了無數平民,但對中國軍隊沒有造成值得一談的損失。”
美軍地面部隊炮火很強,坦克也多,習慣於白天作戰,以便於諸兵種協同。他們先是航空兵轟炸、掃射,各種口徑的炮火轟擊,然後以坦克為先導,步兵跟隨其後,實施進攻。處於劣勢裝備的我軍,既無空中支援,也無強大的炮火與坦克支援。彭總就採取一切辦法避開敵人的優勢與長處,充分發揮我軍的優勢與特長。在戰役和戰鬥方式上,採取了夜戰、近戰、白刃戰;採取圍點打援,從運動中殲滅敵人;從敵人的側後攻擊敵人。這樣就避開我軍的短處,充分發揮了我軍的長處。夜間進攻,衝入敵人陣地內與敵人絞在一起,敵人空軍和炮兵都無法支援;和敵人拚刺刀,敵人更怕,拚刺刀不只是賃美國兵個兒大,主要的是靠勇敢與無畏,靠機動靈活制勝;敵人也很害怕我軍從側後進攻,敵人的火力主要在正面,翼側是敵人的薄弱部,我軍抄他的後路,不僅完全打亂了敵人的部署,並且也瓦解了敵人士氣。
當時美國新聞輿論說什麼: “中國軍隊打仗不正規,美國軍隊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不按戰鬥條令作戰的軍隊。”麥克阿瑟完全忘記了他所崇拜的西方軍事家“拿破崙打仗全然不按規則辦事”的作戰原則(引自蘇聯葉·維·塔爾列著(拿破崙傳))。因此麥克阿瑟不知道也不可能理解中國人民志願軍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我軍就是採取這些機動靈活的方法,將敵人打敗,取得了戰役戰鬥的勝利,創造了現代戰爭條件下,以弱勝強,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的戰爭奇蹟。
彭總抓住麥克阿瑟在戰役指揮上的錯誤,給予他以致命一擊
在戰爭中,善於發現敵人作戰指導上的錯誤,並加以利用和擴大,以奪取戰爭的勝利,這是最高的指揮藝術。彭總就是這樣的指揮戰爭的藝術大師。 麥克阿瑟在1950年9月15日,仁川登陸成功後,非常驕橫不可一世,連他們的老輩軍事家拿破崙“有一個一直遵循的規則,就是在沒有實際較量以前,決不認為敵人比自己愚蠢;預計敵人採取的措施決不比自己同樣的條件下采取的措施相形見拙。”(引自原蘇聯葉·維·塔爾列著<拿破崙傳)),麥克阿瑟還對他們的著名軍事家,普魯士(德國)的克勞塞維茨的名著<戰爭論)中,關於“集中兵力”的基本原理,都統統忘得一千二淨了。因而在戰役部署與指揮上,也不顧起碼的軍事常識而隨心所欲了。
一、美第10軍在仁川登陸後,按照正常的做法,應該交給美第8集團司令沃克指揮,當時沃克只指揮第1、第9兩個軍,可是,麥克阿瑟卻將第10軍歸他自己直接指揮;二、在向北進犯中,如果由第8集團軍指揮第10軍,從陸路向元山、咸興前進,既方便又迅速,而且南朝鮮軍第1軍團已於10月10日進佔元山,17日進佔咸興,中路南朝鮮軍第2軍團於10月19日已進佔陽德、成川,已經為向朝鮮東部前進創造了條件。可是,麥克阿瑟卻令第10軍於10月20日從仁川登船,繞道海上從元山登陸,向咸興、長津、江界及惠山方向進攻。這樣不僅使第8集團軍與第10軍之間的間隙達80—100公里,而且分散了兵力。特別是經過我軍第1次戰役, “第8集團軍和第10軍遭到沉重打擊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曾建議麥克阿瑟將兩軍會合,以便封閉兩軍之間的間隙,並建立一道綿亙的防線。但是,麥克阿瑟堅決反對”(引自<麥克阿瑟)一書)。
由於麥克阿瑟非常輕視我軍,因此也就非常奇特地認為,第8集團軍與第10軍之間的縱貫山脈是保障兩軍結合部的天然屏障,會阻止中國軍隊突入,中國軍隊將無法越過這些崎嶇的地形。這樣,第8集團軍與第10軍愈向北進攻,兵力也就愈分散,使兩軍互相不能聯絡,不能支援,他們之間的間隙愈來愈大,翼側也愈暴露無遺。<麥克阿瑟)一書的作者認為:這是麥克阿瑟“犯了他軍事生涯中嚴重的錯誤”。美國約瑟夫·格登在<朝鮮戰爭一未透露的內情)一書中,也認為:“麥克阿瑟在北朝鮮軍隊撤退時,決定把他的一半部隊撤出戰鬥,(注:是指將美第10軍從朝鮮正面調出,乘船到東海岸咸興登陸)不論怎麼說,這在美國的軍事史上都可以算得上是最引人注目的大錯之一。這一錯誤足以使他(注:指麥克阿瑟)的指揮功績黯然失色。”
彭總迅速發現了麥克阿瑟在部署和指揮上的錯誤,並利用和擴大了敵人的錯誤。他建議毛澤東主席迅速調第9兵團(第20、26、27軍)入朝參戰。令該兵團迅速向東線長津湖方向開進,擔任阻擊和攻殲美第10軍的任務。將原在該方向阻擊敵人的我第42軍主力西調,以集中6個軍的兵力,攻殲美第8集團軍一部。決心抓住美第8集團軍與第10集團軍之間留下的巨大間隙,給予麥克阿瑟以有力的一擊。
為此,彭總“採取了故意示弱、縱敵、驕敵和誘敵深入的戰術”,誘敵北進,同時隱蔽地調整部署,克服一切困難,將第38軍、第42軍調至德川、寧遠以北地區(原定將第40軍也調過去,因中部山區狹窄,集中與展開不了3個軍,故第40軍只進至球場東北地區),集中指向美第8集團軍右翼的薄弱而又暴露的部位,待我軍引誘敵軍進至我預定殲敵地區,於美軍11月24日,開始實施聖誕節前結束朝鮮戰爭的總攻勢的第二天,即11月25日的黃昏,我軍在彭總的一聲令下,從德川、寧遠地段向敵側翼突然發動了戰役反擊,迅速包圍殲滅南朝鮮軍第7、第8師,將南朝鮮第2軍團擊潰,隨即令第38軍迅速向順川、軍隅裡攻擊前進,該軍第113師一晝夜急行軍73公里,於11月28日晨7時搶佔了三所裡,29日晨又搶佔了龍源裡,將第8集團軍2條主要後路截斷。
這側後突然一擊,完全出乎麥克阿瑟意料之外,把麥克阿瑟打得驚慌失措,這時才認識到我軍的厲害。麥克阿瑟慌忙對華盛頓報告說:“投入北朝鮮作戰的中國軍隊是大量的,而且數量在繼續增加。打著志願軍或其他旗號進行小規模支援的任何藉口再也站不住腳了。我們面對的是一場完全新型的戰爭。”因此,他的部隊“必須由進攻轉入防禦”。(以上引自(麥克阿瑟)一書。
麥克阿瑟於11月28日,命令所有的部隊全部後撤。在這個命令下,敵人逃跑式地撤向“三八線”。我西線各軍先頭部隊尾隨敵人前進,主力於12月23日逼近“三八線”,朝鮮人民軍1軍團越過“三八線”收復延安半島和甕津半島。
彭總這強有力的側後一擊,迅速地發展成為致麥克阿瑟徹底大敗的一擊。麥克阿瑟這位被美國及其盟國軍界稱為“天才的、傑出的軍事家”,被我彭大將軍連續的幾擊,迅速地、全面地敗下陳來。徹底地較量輸了。
我在這裡引用約瑟夫·格登在他所著的(朝鮮戰爭一未透露的內情)書中一段很有趣的描述。1951年春天麥克阿瑟到“三八線”以北的南朝鮮軍第9師視察時, “麥克阿瑟頹然倒在吉普車的前座上,彷彿已經完全精疲力盡。他並未表現出他一貫的信心和盛氣,就連他那頂著名的油漬斑斑的軍帽,這一天也不顯得怎麼精神,他是一個鬥敗的人。”
麥克阿瑟被我彭大將軍打得大敗後,極大地震動了美國朝野和美國人民,也極大地震動了美國的各盟國,使他們大為沮喪和惱怒。他們感受到被麥克阿瑟遇弄和欺騙了,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1951年4月9日(東京時間4月10日)杜魯門總統正式決定撤銷麥克阿瑟的一切職務。撤職命令中寫道:“撤銷你盟軍總司令、聯合國軍總司令、遠東總司令、和遠東美陸軍總司令的職務”(引自<麥克阿瑟》一書)。而這個撤職命令是4月11日中午,首先由新聞廣播傳到東京的,當時麥克阿瑟正在舉行午宴,午後才收到正式命令。命令中還規定撤職令立即生效。
杜魯門總統給了麥克阿瑟一個突然襲擊,這種撤職方式在美國曆史上是沒有先例的。杜魯門對麥克可瑟是很惱恨的,作為總統是美軍最高統帥,調不動麥克阿瑟,1950年10月,杜魯門要麥克阿瑟回國向他彙報,麥克阿瑟不僅不去,而且選擇了離美國遠,距日本近的威克島要杜魯門來見他,而且對杜魯門很傲謾。
在戰爭的過程中,麥克阿瑟不僅根本不聽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和總統指揮,而且連意見、建議也不聽。杜魯門總統及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對麥克阿瑟這樣極端傲謾,對參謀長聯席會議、對總統的極不尊重和“抗上行為”積怨是很深的。
杜魯門的突然襲擊,這就使麥阿瑟無法舉行美軍慣常的指揮官交接儀式,也無法使他向部隊發表慣常的告別演講。也使他離開日本時,受到不凱旋式的歡送,只有他和家屬及少數隨從,冷冷清清地登上了回國的飛機。而且有意安排他的專機在夜間降落舊金山,不讓麥克阿瑟的支持者(共和黨人),在他踏上美國國土時受到歡迎。這也是他必然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