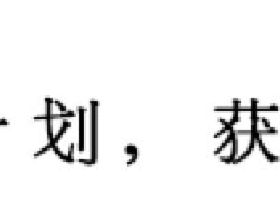1920年2月23日,曲阜衍聖公府,軍警林立,省長與將軍同時坐鎮,顏、曾、孟三氏奉祀官無一人敢缺席。如此陣勢只為等一個嬰兒的降世。此時,嬰兒的父親30代衍聖公孔令貽已去世3個多月。嬰兒註定是一個遺腹子。嬰兒的母親臨產之時雖出現難產,但有驚無險,最終,嬰兒平安降臨。然而,就在嬰兒出生十七天後,母親王氏突然離世。時代、孔府、女人、命運也由此被一條線串在了一起。
1.
聖人香火的延續,不僅在當時的曲阜,就是在全國都是一件備受矚目的大事。然而,天不遂人願。第30代衍聖公孔令貽雖然先後娶孫氏、豐氏,但都未生一子,決定續娶陶氏。孔令貽與陶氏原本生有一子,卻在三歲時不幸夭亡。隨後,陶氏不育。此時,孔令貽已過中年,眼看膝下無一子一女,甚為焦慮。為了能延續聖人香火,不得不繼續娶妻納妾。這次,他選中了陶氏身邊的貼身丫環王寶翠。
王寶翠的肚子相當爭氣。第一胎為孔府添了一位千金。三年後,又一位千金降臨孔府。這讓孔令貽對王寶翠寵愛有加。此時,正夫人陶氏羨慕嫉妒恨的本性暴露。她雖然知道王寶翠再怎麼受到丈夫的寵幸,也不會超越她的地位。而女人的嫉妒是毫無理由的,並且嫉妒很容易變成恨。女人對女人的恨是恨到骨子裡的。為了釋放心中的恨,女人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從陶氏對王寶翠的折磨可見一斑。
王寶翠,一個河北遵化貧苦農民家的女兒,從小被賣給陶家做丫頭,甚至“寶翠”的名字都是陶家給取的。寶翠雖為丫頭,但溫順、知禮、端莊。當她長到十六七歲時,全身散發出少女的氣息與活力,徹底迷倒了陶家的兩位公子。一夫可娶二女,但一女難嫁二夫,況且還是親兄弟。為了得到王寶翠,陶氏兩兄弟雖未走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但也將家裡鬧得雞犬不寧。最為痛心的莫過於陶母。
當時,陶家五小姐(陶氏)已嫁到曲阜孔家。有一次,陶氏從曲阜回到北京孃家,恰巧遇到兩兄弟又為王寶翠起了爭執。為了解決兩個兒子之間的糾紛,陶母決定讓女兒陶氏將王寶翠帶到孔府。就這樣,王寶翠一直作為貼身丫鬟陪在陶氏身邊。作為丫鬟,她認命,不敢有非分之想。但命運是最難預料到。二十歲時,王寶翠的命運發生了變化。
二十歲的王寶翠被四十三歲的孔令貽填房做了姨太太。王寶翠的使命只有一個,那就是為孔家延續香火。五年之中,王寶翠為孔令貽生下兩個女兒。但這也招致了曾經的主子陶氏的嫉恨。每當寒冬臘月,孔令貽都會離開曲阜前往北京。這段時間對於王寶翠最為煎熬。沒有丈夫的庇護,陶氏對她變本加厲地虐待。陶氏常常令王寶翠全身脫光,跪在地上,並用皮鞭抽。為此,陶氏還專門製作了一種皮鞭,一根半尺長的木柄,頭上並排釘著幾條皮鞭。這樣用木柄抽一下,身上就會出現好幾條鞭痕。
陶氏有時還會親自上手,直到自己精疲力竭。即使王寶翠在懷孕期間,也經常受到陶氏的折磨。有一次,陶氏要去濟南,將一切準備好之後,似乎心裡還有什麼事情沒做。就在這時,她突然想到“還得打一頓寶翠”。就這樣,陶氏毒打了王寶翠一頓之後,才悠然地上了火車。陶氏的陰險兇暴在孔氏家族中盡人皆知。曲阜老百姓甚至送給她一個“母老虎”的綽號。
2.
1919年,王寶翠再次懷孕。丈夫孔令貽並沒能時刻陪在身邊。因北京有事,孔令貽在王寶翠懷孕期間離開曲阜前往北京。這一走卻成了兩人的訣別。五個月後的11月8日,孔令貽在北京的官邸太僕寺街聖公府病逝。臨死之前,孔令貽念念不忘王寶翠肚子裡的孩子,並給大總統遺呈“令貽年近五旬,尚無子嗣,幸今年側室王氏懷孕,現已五月有餘。倘可生男,自當嗣為衍聖公,以符定例。如或生女,再當由族眾共同酌議相當承繼之人,以重宗祀”。
1920年2月23日,王氏臨產之時,產房四周裡三層外三層被北洋軍警重重包圍。一是,防止企圖之人用“狸貓換太子”的方法偷換嬰兒,二是,防止其他意外事情發生。
此時,丈夫孔令貽已死。作為衍聖公夫人,陶氏成了孔府的當家人。她也希望王氏能為孔府生育一名男嗣。因為,一旦王氏生了女孩,衍聖公的爵位將由南五府的孔德囧繼承。陶氏也將結束自己“衍聖公太太”的地位,從而搬出孔府。如果,王氏生育男嗣,陶氏將過繼到自己膝下,那樣,她依然是孔府的當家人。
一切正如陶氏與孔府上下期待的一樣,王氏生下了一名男嬰。當男嬰降世的那一刻,就被陶氏抱走了,而王氏連看一眼親生兒子的機會也沒有。就在王寶翠生下兒子十七天後,陶氏命她的心腹孔心泉買來中藥。當中藥熬好後,陶氏親自端來給王寶翠。王寶翠知道陶氏的為人,心生警覺。陶氏卻強說王寶翠睡覺打哆嗦,要喝下藥才能治癒。膽戰心驚的王寶翠跪在床上哀求陶氏說她沒病。陶氏置之不理,終逼著王寶翠喝下湯藥。
一位照顧王寶翠的唐媽媽此時雖守在床邊,但不敢吱一聲。當陶氏離開後,王寶翠含淚對唐媽媽說道:“我活著也沒好日子過,我倒不怕喝這藥,我就是想孩子,想看看孩子。”最終,王寶翠在臨死前也沒有實現自己的願望。此時,大女兒德齊才五歲,二女兒德懋二歲,小兒子德成只十七天。姐弟三人從此失去了親生母親。
王寶翠雖為孔家生育三個孩子,最終只落得孔林角落裡的一堆黃土,連墓碑也沒有。
後來,王寶翠的二女兒孔德懋回憶:“我常常想起我的母親,她做孩子的時候離開了母親,而做了母親的時候又離開了孩子。逃荒、被賣、捱打、毒死,這就是她一生的道路!一個善良、美麗、聰明的農家女兒的道路。”
偌大的孔府幾百號人,真正的主人只有四人:陶氏與孔家三姐弟。隨著三姐弟年齡越來越大,每當三人去母親墳頭祭拜時,都會長時間默默地待在那裡。三人會根據母親遺留的照片,腦補母親生前的形象。他們雖與陶氏生活在一起,但絲毫談不上母子與母女之間的感情。在他們心裡,感受最深的是,姐弟之間感情極其深厚。這世界上也只有他們三個是親人。
三姐妹生活在孔府的內宅之中,對外人來說,這是個與外界隔絕的神秘之地,猶如北京皇宮中的後宮。孔府上下數百名僕人中,也只有十幾人可以進入。內門之上曾貼有這樣一條諭告:“聖府內事關重要,無論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內,如有違犯輕者司察處,重者定予嚴懲不貸。”
三姐妹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漸漸長大的。吃飯、睡覺、讀書、遊戲,三姐弟朝夕相處,形影不離。三人雖有珍珠、翡翠、瑪瑙、金子之類的珍寶可玩,但童年時代唯一的一件玩具還是僕人用木頭給釘的一輛兩隻羊拉的小平板車。沒有布娃娃玩,就用後花園的野草和秫秸紮成小人玩。孔府的天與地就是他們心中的天與地。對於外面的世界,三姐妹幾乎一無所知。
3.
隨著大姐漸漸到了婚嫁的年齡,三姐弟在一起的時光慢慢減少。北京的馮家被選定為大姐的婆家。丈夫就是清朝著名書法家馮恕的小兒子。十七歲時,德齊離開妹妹與弟弟遠嫁北京。一場看似門當戶對的婚姻,卻成為德齊悲慘命運的開始。
在大姐出嫁的數百抬嫁妝中,頭一抬就是孔府的無價珍寶。一個像寫字檯一樣大的楷木如意,上面精工雕刻著文王百子圖:一百個小孩,相貌姿態各異,形象生動逼真,在中間的是周文王,一百個小孩是他的一百個兒子。如意本是吉祥如意的象徵,幸福的象徵,但大姐的婚姻卻恰恰相反,沒有絲毫的幸福感,甚至悽慘無比。
大姐出嫁時,孔府跟去兩個人,一個是男僕吳建文,還有一個女僕,後來女僕被馮家打發回來了。之後,大姐每次從北京回孔府,只有吳建文跟著伺候。三十年代,在北京,暖水瓶與暖水袋在大戶人家已經很普遍。但當大姐從北京將這些看似普通的物品帶回孔府後,卻成了稀罕物。孔府裡的人竟然從未見過暖水瓶,甚至為好奇,不用火還能保溫。這個暖水瓶也成為孔府中的第一個暖水瓶。
之後,大姐每次回家都是神色憂鬱、沉默寡言,沒有一點當年三姐妹在一起時那種無憂無慮的風采。每當弟弟與妹妹問她在北京的生活如何,她什麼也不說。那是一個“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年代,嫁出去的姑娘得認命。大姐認命,而她的命運自然與丈夫息息相關。
大姐的丈夫是個紈絝的富家子弟,雖已結婚,但整天在外面花天酒地,尋花問柳。當身上的錢花光之後,就會向大姐索要嫁妝錢。當時北京富家子弟經常開汽車炫耀,丈夫也不甘落後,於是向大姐要錢。當他買了汽車之後,居然經常載著一車女人兜風。由於開車技術太差,撞在了電線杆上,把滿嘴的牙都撞掉了,不得不換了一口牙。即使這樣,以男人為天的大姐還是縱容丈夫的窮奢極欲。當自己的嫁妝被丈夫揮霍得所剩無幾時,為了滿足丈夫金錢上的需要,每次回到孔府,總要帶些金子回去。她又怕別人知道了笑話,都交給僕人吳建文帶在身上。
弟弟德成與妹妹德懋都已懂事,從吳建文那裡知道大姐與丈夫的關係後,怕大姐難過,都不敢再提起她的丈夫,也不敢當面送她金子,怕她不好意思。因此,當大姐自己去取金子的時候,別人都假裝不知道。大姐的傷痛,她不願提,無人敢問,也只能深深埋在心裡。
之後,二妹德懋也遠嫁北京。兩姐妹恰巧都在北京西城,大姐在羊肉衚衕,二妹住在太僕寺街,兩地相距不遠。二妹的丈夫是歷史學家,清史館館長,溥儀的老師柯劭忞的小兒子柯昌汾。柯劭忞家有三子,老大柯昌泗,老二柯昌濟,都是著名的甲骨文字學家。小兒子柯昌汾最受家人寵愛,但也最不成器。太僕寺街的柯家與羊肉衚衕的馮家背景與家世都相當不俗。
柯劭忞在溥儀登基時曾任毓慶宮行走,與大總統徐世昌是換帖兄弟。徐世昌還將自己的孫女嫁給柯劭忞的孫子,兩家結為姻親。柯家的女人也非平凡女子。柯劭忞的夫人吳之芳是清代著名散文家吳汝綸的女兒,極擅詩詞。她的姐姐吳芝英也是博學多才,並與秋瑾女俠是好友。當年,秋瑾被殺害後,就是閨蜜吳芝英冒險前往收的屍體。
孔家與柯家聯姻可以算得上門當戶對。孔德懋曾回憶自己離開孔府的情形“上車的時候,我穿著一件粉紅色旗袍,旗袍下襬繡著一隻大鳳凰,告別了親人和家鄉,告別了我的朝夕相處的骨肉兄弟,揮淚遠去北京。”當時,小弟德成含淚對二姐說道:“你和大姐都走了,府裡就剩我一人了。”姐弟相處十幾年,一朝別離,心中頓生無限傷感。此後,孔德成為自己起了個字“孑餘”,意為孤獨一人,無限寂寞。
二妹德懋嫁到北京後,與大姐德齊相距不遠。兩姐妹相聚,自然欣喜無比,但想到夫妻的關係,又不大願說丈夫的壞話,有時兩姐妹只能默默對坐。當年,二妹德懋不甚明白大姐德齊的憂鬱與傷感,直到自己的出嫁後,才深有體會。自己與丈夫柯昌汾婚後生活並不美滿。丈夫經常貪婪地向她索取錢財,有時甚至會粗暴地對她。作為孔府的二小姐,德懋從小隻知以禮待人,任由丈夫欺辱,而默不作聲。此時,德懋的乳母王媽媽實在看不下去,毫無懼色地為德懋據理力爭。後果可想而知,最終,王媽媽只能被迫離開柯家,但心裡一直惦念著二小姐。
後來,德懋隨丈夫柯昌汾前往天津。但不久,她接到北京發來的緊急電報,大姐病危。當德懋動身回到北京,大姐已經昏迷不醒。北京四大名醫孔伯華診斷後,開了些藥離開了。德懋端著熬好的藥湯,紅腫著眼睛,要給大姐喂藥,但大姐已經難以下嚥。最終,大姐掙扎著醒來,用盡全力,氣息依然微弱地說了四個字“不用餵了”。隨後,大姐嘴角微動,想繼續開口說,卻已無力出聲,只能用哀傷的眼睛看著床前的二妹,眼角邊掛著一滴淚珠,匆匆走完了二十五年的人生路。每當德懋回憶起大姐離世之時,總會顫抖地說道“那情景歷歷在目,使人心碎,令人腸斷。”
大姐停止呼吸後,嘴唇和手指甲皆呈黑色,與服毒徵兆相似。生活的不如意讓大姐的心,痛到極點,選擇以這種方式結束自己,自認為唯有如此方能解脫。婚後,二妹德懋雖與大姐的遭遇極其相似,但她把委屈當作生活,並不斷從中尋找光明,使自己繼續活下去。如今,二妹孔德懋已越過一百零四歲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