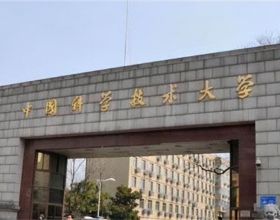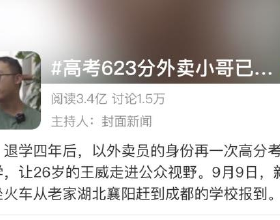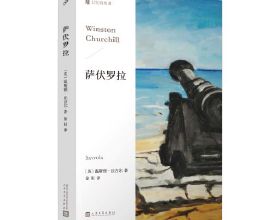近期,在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即將到來之際,中國歷史研究院舉辦了一場珍稀文獻展。展覽上,陳獨秀之子陳喬年的個人履歷,首次面向社會公開。
寥寥兩張泛黃的紙頁上,關於陳喬年一生的記錄是那般簡單直白,卻又讓人異常心酸。
1928年6月6日,年僅26歲的陳喬年,被國民黨殺害於上海龍華。
那一天,他手上腳上是乒乓作響的鐐銬,渾身佈滿傷痕和斑駁的血汙,光腳走在血水和泥濘之中。敵人舉起屠刀、猙獰地站在他面前,可他卻毫不畏懼,微笑著從容赴死。
“去時少年身,歸來烈士魂,陳家,滿門忠烈”。想必看過《覺醒年代》的朋友,都會不由自主的發出這樣一句感嘆。
亂世之中,陳獨秀先生率先扛起革命大旗,為民族解放貢獻終身。他的兩個兒子延年、喬年,相繼為國犧牲,離世時都未滿30歲。就連陳喬年的遺腹女陳鴻,都在不知道自己身世背景的情況下,接受冥冥之中的指引,走上了參軍報國之路。
1919年底-1920年初,陳家發生了兩件看似平平無奇、卻影響深遠的大事。一件改變了陳延年、陳喬年兩兄弟的人生軌跡,一件則扭轉了中國的命運。
1919年12月底,陳延年和陳喬年在上海碼頭,正式登上前往法國勤工儉學的輪渡。
2個月後,為了躲避敵人的追捕迫害,陳獨秀在李大釗的護送之下,經由天津秘密轉移至上海。期間,看著沿途窮困不安的百姓和動盪時局,兩人深受觸動。悲憤之下,他們約定:陳獨秀在上海,李大釗在北京,一南一北、同步推進建立中國共產黨的事宜。這也就是傳聞中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使得中國革命擁有了堅實有力的領導核心,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而關於陳延年、陳喬年的故事,以及赴法留學的意義,還要從他們的成長經歷講起。
陳喬年出生於1902年,自小在安徽安慶長大。他出生前,陳獨秀因宣傳反清思想遭到清政府通緝,被迫逃亡日本。儘管1903年,陳獨秀就已經回國,但出於種種原因,他只在家中停留了片刻便趕赴上海,之後又多次往返於中國和日本,為革命四處奔走。
所以說,在喬年的童年時期,父親這個角色是嚴重缺失的。對於陳延年而言,同樣如此。
延年比喬年大4歲,是家中長子。延年出生那年正值康有為、梁啟超推進維新變法運動,維新派人士高舉“資產階級改良”的大旗,倡導學習西方、改革軍政、創辦報刊、傳播新思想。儘管維新變法僅持續了103天就以失敗告終,但陳獨秀卻深受影響。本是晚清秀才的他迅速站到了思想解放浪潮的最前方,一邊從事反清鬥爭,一邊接觸學習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忙得根本不著家。
中國傳統文化中向來有“長兄如父”的理念,當陳獨秀在外為革命打拼時,延年自然而然地扛起了教養弟妹的重擔。從小到大,延年一直把喬年護在身後,像大樹和燈塔一樣,為他遮風擋雨、指明方向。所以,相比起早熟堅毅的延年,喬年仍帶著些許普通孩子的稚嫩和天真。
源於這種亦兄亦弟、亦父亦子的關係,喬年對延年非常的依賴和崇拜。他就像一個小跟屁蟲一樣,時時刻刻站在延年身邊。也正因如此,在1927年陳延年壯烈犧牲後,喬年才會一夜之間徹底長大。獨自擔負起兩個人信仰的重量,變得尖銳而執著,不要命一般投身革命。
看過《覺醒年代》的朋友想必都知道,陳家三父子之間的關係不同於一般的父子情。除了相處時間過少所造成的生疏客氣外,延年一度還十分憎惡、排斥父親,連帶著喬年也與父親十分疏遠。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父母感情上的問題,但最主要的還是與一場災禍有關。
那是發生在1913年的一件事。自1912年3月上臺,成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野心勃勃的袁世凱就企圖實施獨裁統治。他擅自向英法等國借款2500萬英鎊,瘋狂擴充軍備,企圖消滅南方革命力量,坐穩江山。
得知袁世凱的圖謀後,遠在日本的孫中山先生悲憤交加。他立即回國,召集各方力量,發動了一場針對袁世凱的武裝革命,史稱“討袁之役”。然而從之後袁世凱登基稱帝一事就能看出,這場討伐行動失敗了。
當時,陳獨秀正擔任著安徽都督府秘書長一職,已經參加革命10多年的他,早已成為了安徽地區鼎鼎大名的民主革命領軍者。陳獨秀毫無疑問的參與了“討袁之役”,也毫無意外的成為了袁世凱政府的眼中釘。
討袁革命失敗後,陳獨秀遭到追捕,還曾被捕入獄。幸得“辛亥革命四傑之一”的柏文蔚出手相助,陳獨秀才獲得釋放,隨後遠赴日本避風頭。
只可惜,陳獨秀低估了袁世凱政府的殘暴程度。在得知陳獨秀已經離開中國後,袁世凱竟然將魔爪伸向了他的家人。這年6月,袁世凱的親信倪嗣沖率兵攻佔了安慶,敵人拿著刀槍抄了陳家,還四處捉拿延年、喬年等人,叫囂著要斬草除根。
儘管在鄰居的幫助下,陳家上下避過了這一劫,可這件事卻猶如一根刺般,深深紮在延年心底。都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當時的延年只是一個涉世未深的少年。他不清楚父親做了些什麼,不知道父親曾鋃鐺入獄,險些被敵人迫害。他只知道,那一切都是拜父親所賜,可當敵人來襲時,父親非但沒有站出來承擔責任,反而出國避難,將他們一家置於險境。
對於此事,陳獨秀曾有無數個機會可以解釋,但他卻從未為自己辯解過半個字。或許他也為此感到自責,或許他寧願被孩子們埋怨,也不希望他們為此自責。
很長時間裡,陳獨秀和延年、喬年的關係都可以用水火不相容來形容。就算到了上海與父親團聚,他們也不願和陳獨秀獨處一室,不願拿陳獨秀一分一釐。前往法國留學前,兩兄弟天天在外風吹日曬幹苦力,餓了啃乾麵包,渴了喝自來水,一邊賺錢一邊學習。
然而,無論延年和喬年如何排斥,也無法抹去他們是陳獨秀之子的事實。同樣也無法否定,陳獨秀對他們的人生起到了非常強的引導作用。
作為我黨的主要創始人兼第一代核心領導,陳獨秀對中國革命的貢獻舉足輕重。他創辦的《新青年》喚醒了無數青年學子的革命理想;他引領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率先推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的大門;他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領導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為中國民族解放鬥爭打下堅實基礎。
所謂“虎父無犬子”,雖然延年、喬年和父親相處的時間並不多,可潛移默化之中,他們卻深受陳獨秀的影響和帶動。他們憤怒於敵人的殘暴和社會的黑暗,立志要參加革命,將身處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拽出深淵。只可惜由於身處老家,沒能第一時間接觸新思想,兩人滿腔的熱血和鬥志在心中左衝右撞,遲遲找不到宣洩的出口。直到1915年,他們來到陳獨秀身邊。
延年、喬年來到上海這年,陳獨秀和他的《新青年》猶如一記驚雷,炸響了整個中國。陳獨秀指出,中國革命的關鍵在於青年,在於思想變革。陳獨秀一針見血的主張,給延年和喬年帶來了極大震動。他們終於找到了為之奮鬥的方向,那就是尋找那劑可以喚醒麻木的中國人的心靈良藥。
最初,延年和喬年信仰著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這種主義倡導一種極端的大同、平等與自由,也就是社會之中無需政府、法律、強權的控制,全由各個團體之前自由契約、維繫關係。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中國的無政府主義主張,似乎是在清政府強權強壓之下,所形成的一種嚴重反彈,其明視訊記憶體在不小的缺陷。畢竟就算是一個小團體,如果沒有主持大局的人,也容易陷入混亂,更不用說是一個國家了。
而這些問題,延年和喬年在不斷試錯中,逐漸都意識到了。不過他們真正將信仰從無政府主義轉變為共產主義,是在法國留學期間。這也是開頭說赴法留學改變他們人生軌跡的原因。
關於延年、喬年在法國的經歷,我們無從得知。只是知道,1921年時,到法國勤工儉學的學生們曾開展過3次鬥爭行動。隨著鬥爭的結束,他們對無政府主義理念徹底失望。1922年,陳延年和陳喬年就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次年,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喬年趕赴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學成歸國後,他來到北京,在李大釗先生的領導下正式參加革命。
早年,因為陳獨秀的關係,喬年和延年一起參與了很多關於《新青年》雜誌的工作,對於印刷、發行、售賣有著豐富經驗。所以回國後沒多久,喬年就擔負起了在北京籌辦、領導秘密印刷廠的任務,主要負責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的翻印工作。之後,他又回到李大釗身邊,一邊協助李大釗開展組織政治活動;一邊積極準備講稿,講授宣傳馬克思主義等知識理念。
1927年7月4日是陳喬年人生的第二個轉折點。這一天,在上海一處刑場,陳延年被敵人亂刀殘忍殺害,年僅29歲。
哥哥的犧牲給喬年造成了嚴重的打擊,他為此心如刀割,恨不得把敵人挫骨揚灰。悲憤之下,喬年暈倒在地,大病了一場。
當他終於清醒過來時,就彷彿變了一個人一樣,變得更像延年了。喬年義無反顧的跟隨著哥哥的步伐,放下相對安穩的宣傳工作,奔赴革命第一線。
延年犧牲之時,他是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延年犧牲後,喬年擔負起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部長一職,揹負雙重使命往返江蘇、上海兩地,一邊與敵人周旋,一邊想方設法恢復被敵人破壞的黨組織。
只可惜,由於叛徒的告密,喬年在1928年2月16日的一場秘密會議中被捕。在監獄中,喬年受盡了各種酷刑,遍體鱗傷,渾身上下就沒有一塊完好的皮肉。
可令人沒想到的是,在那樣的慘況之下,喬年反而露出了些許少年時的模樣。敵人越殘暴,喬年就越堅強、越樂觀,他笑著安慰同伴說:“讓我們的子孫後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的幸福吧!”
這句斬釘截鐵的話,彷彿是一句勝利的宣言,在昭告天下:共產黨一定會勝利,中國一定會迎來光明。1928年6月6日,26歲的喬年再度跟隨哥哥的腳步,無所畏懼、英勇就義。
據悉,在安徽合肥,有一條延喬路,那是為了紀念陳延年、陳喬年兩兄弟而建。延喬路旁還有一條集賢路,而陳獨秀就葬在安徽集賢關。延喬路和集賢路沒有交匯,卻並行著直直通往繁華大道。這個用心的設計,是對他們沉痛的悼念,更是一種永恆的讚頌。
值得一提的是,喬年犧牲時,他的夫人史靜儀還懷著一個女兒陳鴻。陰差陽錯之下,陳鴻自出生起就被寄養在別處,後來下落不明,一直到1994年才被找到。
可彷彿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改名苗玉、從不清楚自己身世背景的陳鴻,長大後竟也選擇參軍入伍、報效祖國。可見“陳家滿門忠烈”這句話,有多麼名副其實。
回顧往日崢嶸歲月,像陳獨秀、陳延年、陳喬年、陳鴻一樣,為民族解放、保家衛國而奮鬥終生的英雄戰士,還有很多很多。謹以此文向他們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