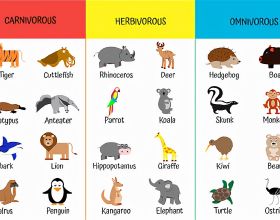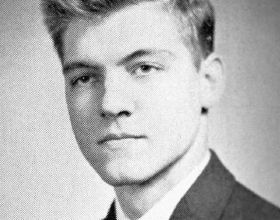第21章、多格灘戰鬥
溫斯頓·斯潘塞·丘吉爾 [英國]
01.
1月中旬,在政府上層的秘密圈子裡表現出對海上形勢的不安。約翰·傑利科爵士在他的書中描述,在這關鍵時刻,他認為大艦隊的情況特別虛弱。在他寫給第一海軍大臣的信中充滿了令人不安的計算出來數字,這些數字表示發生大戰時英、德兩國海軍的相對力量。他說英國的幾艘無畏級戰艦正在進行常規整修;另外兩艘,“君主號”和“征服者號”,由於碰撞而暫時癱瘓了。他又搬出了去年11月形成的那套理論:德國人秘密地採用火力十分強大的大炮裝備其最新的戰列艦。去年11月他提到有4艘軍艦裝備了14英寸的大炮,而此時增加到6艘軍艦裝備了15英寸大炮。說德國有此種變化當然是不可能的。我們的情報保證能正確得知,這些軍艦在什麼日期離開船塢開始活動,因此,敵人完成如此巨大的建設是不可信的。所以我不得不批駁這些論點以及其他性質同樣令人吃驚的言論,為此特別建立了一個由第三海軍大臣領導的委員會,以平息因相信德國出現這種大規模重新武裝而產生的憂慮。
總司令的另一個要求也讓我十分為難。他對駐紮在福斯灣的戰列巡洋艦表示極度擔憂,希望能將她們撤往克羅默蒂,以便更靠近主力艦隊。如果同意這個建議,我們將失去有效手段對付德國人襲擊我們沿海。12月16日敵人曾襲擊了哈特爾浦和斯卡伯勒,倘若他們故伎重演,我們將無能為力。克羅默蒂距離黑爾戈蘭灣與斯卡帕距離黑爾戈蘭灣同樣遠,貝蒂上將和戰列巡洋艦撤退到這麼遙遠的一個泊地,看來我們將毫無必要地陷入無助的境地。說實話,我寧願整個戰列艦隊全都南下進駐福斯灣。但是,即便做不到這一點,我也要強烈反對將戰列巡洋艦撤離這一在戰略上可遇上敵人快速艦的要地。因此,1月20日我給第一海軍大臣送去一份備忘錄:
戰列巡洋艦應該聚集在一起,如此我們便可時常保持一支強大力量,足以擊敗德國的所有快速軍艦。如果將戰列巡洋艦調往克羅默蒂,她們將鞭長莫及、無法保衛英國的海岸。克羅默蒂到黑爾戈蘭灣的距離與斯卡帕到黑爾戈蘭灣的距離相同。因而我以為不能分散她們或將她們調離福斯灣,除非貝蒂上將報告說他發現該處航行條件有危險。
第二天早上,關於這個問題和其他一些涉及大艦隊實力的事情,我和費希爾勳爵作全面的討論,他同意我所持的觀點。於是,我在21日下午給參謀長送去一份備忘錄:
戰列巡洋艦應該和目前一樣集合在福斯灣,除非貝蒂上將報告說,該處航行條件有危險。……依此行事。
這種憂慮的反映在戰時會議表現出來。1月21日首相寫信通知我,他要在28日召集戰時會議開會,他希望邀請約翰·傑利科爵士出席會議。我意識到海軍部四周再一次掀起逆流。我認為,當我們的力量正處於吃緊之時,當各種跡象表明敵人活動很可能出現之際,讓約翰·傑利科爵士離開艦隊來倫敦出席戰時會議是不對的。因此我拒絕召約翰·傑利科爵士來倫敦。
02.
年初德國海軍參謀部與德國皇帝舉行了一次商談,結果是對德國艦隊施加嚴格限制。德皇的這些決定的後果是,馮·因格諾爾上將把最強大的第三戰列艦中隊派往波羅的海訓練,這支艦隊由“愷撒斯號”和“柯尼希斯號”組成。然而,他打算讓駐紮在北海的艦隊先開展一次有限的軍事活動。由於天氣惡劣,這項活動一拖再拖。到了1月中旬,他和德國海軍參謀部得出結論,英國海軍即將展開一次大規模進攻。他們已經聽說在貝爾法斯特建造假軍艦,於是便將此事與另一個計劃聯絡了起來,即我們打算將阻塞船駛入黑爾戈蘭灣幾條河的河口。他們興奮激動了好幾天,並處於高度準備狀態。19日上午,一架德國水上飛機在黑爾戈蘭灣60英里外發現了“眾多向東行駛的英國軍艦,其中有數艘戰列巡洋艦,四周還有近百艘小船”。他們當時認為這是一次巨大的封鎖行動。實際上這只是一次由哈里奇港驅逐艦與潛艇小艦隊在戰列巡洋艦支援下的例行偵察。結果什麼也沒有發生,德國人得到的情報表明,英國艦隊的大批軍艦靠近了他們的海岸線,但隨後又退走了;由此馮·因格諾爾得出結論,阻塞行動已被放棄或者無論如何被推延了。20日他立即解除了特別警戒,並於21日命第三中隊穿越基爾運河,駛往波羅的海演習。這些相互矛盾、互不連貫的決策被彆扭地寫入了德國的官方歷史 [ 原注:第六章。 ] 。
戒備狀態普遍解除之後,按照德軍總司令在他的報告和戰時日記中規定的指導方針,在北海採取進攻行動變得比以前更為消極是十分自然的事。但是就在此時天氣開始轉好,參謀長埃克曼中將想要利用這個機會彌補惡劣天氣時的無所作為。於是,在1月22日他向總司令以書面提出下列建議:
“如果明天的天氣依舊像今天下午和晚上一樣,派一艘巡洋艦和一艘驅逐艦前往多格灘是很可取的。不需要特別準備,明天早上給高階軍官和偵察艦艇發一道命令就夠了。
“夜間出發,午前到達,晚間返回。”
一位德國曆史學家說,“馮·因格諾爾上將立即意識到這個建議與剛剛規定的指導方針相矛盾,他在報告頁邊寫道:
‘只有當艦隊一起行動時我才贊成軍艦出海。可惜目前做不到這一點。’”
然而他卻批准了。……
第二天上午10點25分下述命令透過無線電報發給馮·希珀少將 [ 譯者注:原文第348頁稱其為上將。 ]:
“由高階軍官偵察隊選派的第一、第二偵察組,即驅逐艦和兩支小艦隊的高階軍官前往多格灘偵察。他們今晚天黑後離港,明晚天黑後返回。”
03.
23日,費希爾勳爵得感冒臥床休息,儘管有種種觀點分歧,他在傑利科事件上一直很堅定,支援我。於是我到與海軍部大樓毗連的拱門樓看望他。我們就各類問題愉快地談了很長時間。當我回到海軍部我的房間時,已經接近中午。我還沒坐穩,房門被突然開啟,阿瑟·威爾遜爵士未加通報就闖了進來。他盯著我看,眼神透出一道光芒。他身後是奧利弗,手中拿著海圖和羅盤。
“海軍大臣,這些傢伙又出來了。”
“什麼時候?”
“今天晚上。我們讓貝蒂去那兒還來得及。”
我們一封接一封發出了下列電報:
海軍部致海軍艦隊(T)准將 [ 原注:指揮小艦隊的軍官蒂裡特准將在海軍中稱為魚雷准將,或簡稱“准將(T)”。同樣潛艇艇長稱作“艇長(S)”。 ] 哈里奇。取消Z方案。今夜需要你掌管的所有驅逐艦與輕型巡洋艦。派驅逐艦去希爾內斯護航一事取消。
海軍部致“雄腳號”中將羅賽斯。所有戰列巡洋艦、輕巡洋艦與遠洋驅逐艦立即做好出航準備。等待進一步命令。
海軍部致大艦隊總司令。第一、第二和第四戰列艦中隊、巡洋艦與輕型巡洋艦準備今晚天黑後出航。
發完電報,阿瑟爵士簡單解釋了他根據被截獲的德國電報(我們的密碼員已將電文破譯)和一些其他情報(他是搞情報的老手)得出的結論。所有德國快速軍艦將在天黑時出海,英國海岸顯然要遭到襲擊。我的同僚們接著開始致力於為英國軍艦確定會合地。海圖和羅盤經緯度圈立刻表明,只有貝蒂從福斯灣出動、蒂裡特從哈里奇出動才能在德艦襲擊和逃逸前攔截她們。大艦隊在第二天下午之前不可能到達現場,駐紮在克羅默蒂的任何艦隻也到不了該地。然而,對於貝蒂和蒂裡特來說,他們的軍艦有時間白天在多格灘附近會合。威爾遜和奧利弗在海圖上已經標出敵人的可能行動路線,事後證明他們標出的路線幾乎完全精確。他們根據猜測的德艦航速用羅盤一小時一小時地測定敵人航線,直到他們到達我們海岸。然後他們又畫出貝蒂和蒂裡特從福斯灣和哈里奇出發攔截敵人的路線。我們的意圖是,英國軍艦拂曉時在敵人後面約10英里某處相遇和會合,或者在敵人向西過去半小時之後隨即在敵人和其老巢之間相遇和會合。我們還討論了是否應冒更大的風險,即讓我們的軍艦在更靠東的會合點集結。這樣做可以更加確保處在敵人與其老巢之間,但是如果大氣變得多霧就更有可能找不到敵人;回想起12月16日發生的事情,後一種可能性就會變得非常嚴重。因此,集結時間與地點被確定為第二天,即24日清晨七點,在北緯55°13、東經3°12’,此處離黑爾戈蘭灣180英里,幾乎在黑爾戈蘭灣和福斯灣形成的一條直線上 [ 原注:請讀者注意本章末所附的地圖和計劃。 ] 。下面這份電報分別發給斯卡帕的大艦隊總司令、第三戰列艦中隊佈雷德福上將、羅賽斯的戰列巡洋艦司令貝蒂上將以及哈里奇的輕巡洋艦和驅逐艦司令蒂裡特准將: [ 原注:這份電報已發表在菲爾森·揚先生對此次軍事行動的敘述中,見《與戰列巡洋艦在一起》(With the Battle Cruisers)第174頁。 ]
4艘德國戰列巡洋艦、6艘輕巡洋艦和22艘驅逐艦將於今晚出航前往多格灘偵察,可能將於明晚返回。羅賽斯的所有可使用的戰列巡洋艦、輕巡洋艦與驅逐艦應駛往北緯55°13’、東經3°12’的會合點,明晨7時到達。(T)准將率領哈里奇的所有驅逐艦和輕巡洋艦於清晨7時在上述會合點與“雄獅號”上中將會合。如果(T)准將在穿越敵人行進路線時發現敵人,應對其發起進攻。除非萬不得已,不許使用無線電電報機。本電文發給國內艦隊總司令、“雄獅”中將、第三戰列艦中隊中將及(T)准將。
計算與討論花去了將近一個小時,而第一海軍大臣對所發生的一切卻還一無所知。於是我讓阿瑟·威爾遜爵士和參謀長將海圖和電報稿送往拱門樓,如果沒有不同意見就將電報立刻發出。費希爾勳爵對提出的決策表示滿意,隨之就採取了行動。
讀者可以想象那個漫長的下午和晚上時間充滿了何等緊張的情緒。我們無法與任何人分擔這個秘密。那天晚上我出席法國大使招待米勒蘭先生的宴會,他當時任法國陸軍部長,為一項重要使命來倫敦。我們感覺到有一層絕密的與內心沉重的、全神貫注之事的薄膜,把我們與聚集在這裡的高貴客人隔開。在12月份,我們幾乎沒有可信的情報來源。一切都捉摸不定。看上去甚至什麼事都不會發生。現在心裡壓著這麼一件大事,只有一個念頭主宰著頭腦——黎明的戰鬥!這是歷史上兩支強大超級無畏級戰艦的第一次戰鬥。同時還有一種令人震顫的感覺,彷彿眼見被獵捕的動物正一小時一小時地朝陷阱悄悄靠近。
04.
第二天凌晨天還沒亮我們便已起床忙碌起來,等到門外天色明亮時,費希爾、威爾遜、奧利弗和我都已經來到作戰室。各個部門平時值夜班的工作人員都還沒有下班。突然,像命定一樣必然,像閱兵一樣準時,從艦隊截到的電報送到了我們面前。這是第一輕巡洋艦中隊發給“雄獅號”(貝蒂)和“鐵公爵號”(傑利科)的電報:
(上午7:30發出,上午8:01收到)
急電。發現敵人。北緯54°54’,東經3°30’。向東行駛。包括戰列巡洋艦和巡洋艦數目不詳。
兩分鐘之後:
急電。北緯55°24’,東經4°15’。發現敵人,包括巡洋艦、驅逐艦、戰列巡洋艦和輕巡洋艦,朝東南與正南之間方向行欲。
於是,敵情再一次得到證實!
在海軍部的安靜的屋子裡分分秒秒地跟蹤著一次海上大戰的具體細節,人的精神經歷中不可能注入比這更多的冷酷刺激。在遠處藍色的大海上,在格鬥的軍艦上,在大炮震耳欲聾的爆炸巨響中,歷史事件的片斷正一幕幕地展現在肉眼前。那裡有最強烈的戰鬥感覺;那裡有戰鬥的憤怒;那裡充滿緊張、默默經受肉體與精神苦楚。但是在白廳只有鍾在滴答走動,一些沉默不語的人匆匆走進來,將鉛筆寫的紙片擱在別的同樣沉默不語的人面前,他們或在畫線條或在潦草計算,不時地用手指指點或者壓低嗓音簡短地評說幾句。電報一份接著一份,間隔只有幾分鐘,有人在收到並譯出時順序經常顛倒、意思也常常含混不清;在這些之外在頭腦中一直有一幅影象時常在閃爍變化,環繞這幅影象在每個階段想象力會冒出希望或悲劇的閃光。
第一輕巡洋艦中隊致總司令
(上午8:00發出,上午8:20收到)
敵人軍艦改變航線轉向東北。
“雄獅號”致總司令
(上午8:30發出,上午8:37收到)
發現敵人4艘戰列巡洋艦,4艘輕巡洋艦,驅逐艦數目不詳,方位南61、東11英里。我的位置北緯54°50’、東經3°37’。航向南40東,速度26節。
總司令致第三戰列艦中隊
(上午9:00發出,上午9:18收到)
朝黑爾戈蘭灣方向行駛。
蒂裡特准將致總司令
(上午9:05發出,上午9:27收到)
第一與第三小艦隊在戰列巡洋艦後。2英里。
總司令致第三戰列艦中隊
(上午9:20發出,上午9:28收到)
支援第一戰列巡洋艦中隊作戰。
“雄獅號”致總司令
(上午9:30發出,上午9:48收到)
正與敵戰列巡洋艦交火。距離1.6萬碼。
第一輕巡洋艦中隊致“雄獅號”
(上午10:08發出,上午10:18收到)
敵人派最後面的一艘戰列巡洋艦離開艦隊。我被趕走。
第一輕巡洋艦中隊致“雄獅號”
(上午10:21發出,上午10:27收到)
我正與敵人保持接觸。
第一輕巡洋艦中隊致總司令及“雄獅號”
(上午10:15發出,上午10:59收到)
敵人飛艇,方位東南南。
將近一個半小時我們沒有聽到“雄獅號”發電報,這段時間裡也許她與第一戰列巡洋艦中隊正在激戰中。約翰,傑利科爵士顯然也感覺到這種壓迫性沉寂的重量。
總司令致“雄獅號”
(上午11發出,上午11:09海軍部收到)
你在戰鬥嗎?
隨後又是20分鐘的沉寂,感覺似乎要長得多。然後,到了11點37分,終於傳來了電報,這個電報不是從“雄獅號”或第一戰列巡洋艦中隊發來的,而是指揮第二戰列巡洋艦中隊的高階軍官發給總司令的:
與敵人戰列巡洋艦猛烈交火。北緯54°19’、東經5°05’。
有人說,穆爾正在報告:“雄獅號”顯然遭重創。
這時我的心裡浮現出一幅純粹無關的畫面。我回想起曾多次去威斯敏斯特教堂參加追悼會:人群、軍服、覆蓋著英國國旗的靈柩、還有哀樂,貝蒂!這個場景至少不是真的;但是,天呀,的確太真實了!“雄獅號遭重創。”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