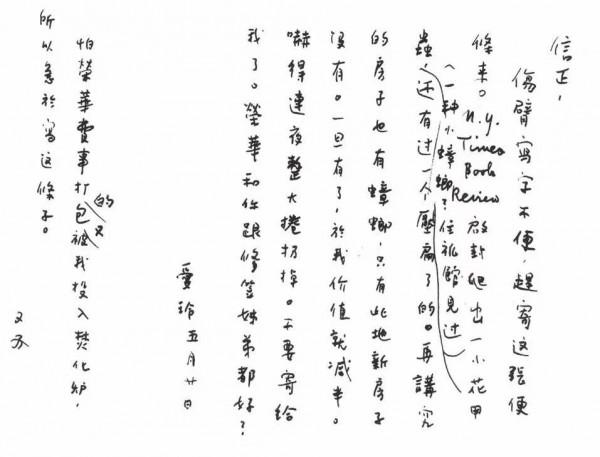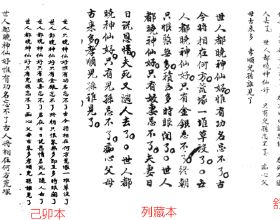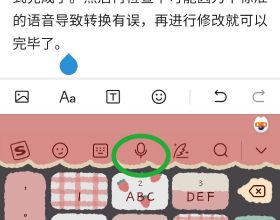都說張愛玲的文字遍佈蒼涼,確實如此,在淺顯和初始的閱讀上,她的作品確實如此,但在深且遠的地方,卻深藏暖意。當閱讀觸到了暖意,方如初春寒意未散,但江上一隻鴨感到了水暖,因知冷,所以知暖。
張愛玲願意看見平凡生活和平凡人。這平凡包含低微、平淡、現實等若干狀況。
她的小說中,經常會描述市井街巷一個邊沿角落,或在微雨中,一隻小煤爐,正在生火,冒著白煙,或煮著一隻奶鍋子,溢位來的奶燒糊了,煙煤味、奶的焦糊味,假使煮著的只是稀粥,或者南瓜,那熱氣正有“暖老溫貧”之意。
珍饈美食或可悅人齒呷,但稀粥或南瓜上的熱氣卻是貧寒現實中真實切近的慰藉。她願意在一團團白煙、焦糊味中穿過,切膚貼近,感受,然後在作品中時不時描述這場景。實則是將這種感受和慰藉傳達給讀者。
這只是沙海中一粒,她的細微在整個的行文的全部中,描述,卻又姿態迥異。她也非常容易看到人的孤獨寂寞,然後轉述在文中。比如經常寫到鸚鵡。這也是個象徵。鸚鵡通常是富貴人家有錢有閒但孤獨寂寞的人用來解悶的,這指的是誰?一夫多妻的現實中,妻與妾可能都有看起來熱鬧實則難言的境地。鸚鵡既是個伴兒,也是寂寞的表彰,人去樓空時,歡宴歸來時,一下子落入虛空,此時鸚鵡一聲“可曾安好?”卻不是人聲!好的作品就是這樣,寫什麼不會明指,那時刻心情如何,只輕輕提到看見一隻鸚鵡立在架上,或者一聲話不知哪裡來,循聲去,卻是一隻鸚鵡。
林黛玉孤女一個,與姐妹們嘻笑後,更顯得孤獨,她從賈母房中回來,進到瀟湘館,入房前,聽得一句“姑娘來了,打簾子”,卻也是鸚鵡。
這難說不是《紅樓夢》對張愛玲的感染,可也見得她是一個容易在此處受到感染的人。
《封鎖》第一句就是“電車司機開著電車”,如此平淡無奇。就如魯迅的“左邊一棵棗樹,右邊還是一棵棗樹”。似乎這些話是無意思的。
但這無意思的話,一定是確定的有意為之,並傳達語言中一種意境——無意中的深意。且來看“電車司機開著電車…前面的兩條車軌像曲蟮一樣無盡地來了,又來了,沒有止境…但是他不發瘋。”
將人引入一種意境,生活、歲月和人的心情,都像似水流年一樣,進行著進行著,讓人煩悶苦惱害怕,但仍然就這樣進行著。
除了語句,小說的架構也能在極小的細微處發人深思。架構這事兒,像人生閱歷一樣,不親歷不能體會其中滋味,年少不懂小說架構,以情節取勝,彷彿一時的瑰麗情節、一時的意氣可以代表一生。流年給人的領悟就是將未來變成過去,把因果變成可見。五十歲寫《小團圓》,寫九莉與邵之雍相戀,門頭一直有一隻木雕鳥看著,突然又寫到十幾年後在紐約打胎的恐懼一幕,已成形的四個月的胎兒也像一隻木雕鳥立在馬桶壁上…彷彿在那隻鳥的注視下,流年默默將一輩子的恩怨都衝逝過去,妖邪可怖,是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的意味。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