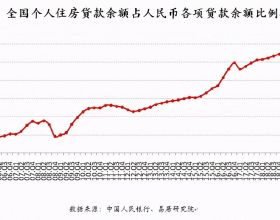湘軍鎮壓太平軍、捻軍、回民起義後,軍功紳士急劇膨脹,給近代湖南社會帶來了許多新的影響。
首先,軍功紳士的膨脹,帶來了湖南紳士隊伍結構的新變化、軍功紳士佔了紳士階層的主流地位,而一向佔主流的功名紳士則退居其次,從而導致紳士隊伍整體素質的嚴重下降,領導鄉村社會的精英群體的社會功能出現嚴重弱化的趨勢,無法擔負起整合鄉村社會秩序和經濟建設的歷史重任。有的甚至憑軍功之勢強橫一方,成為地方惡霸,有的因參軍擄掠,一朝致富,錢財得之甚易,因而往往揮金如土,奢侈無度,帶來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
其次,軍功人員大量湧入紳士隊伍後,用搜刮而來的錢財強買土地,進行地租剝削,反對有損於自身利益的任何改革,成為社會上一股最為保守的社會勢力。湘鄉除曾氏兄弟購買了大量的田產以外,許多湘鄉將領也紛紛回鄉置田建莊。
湘鄉縣黃田章合才(官至提督)在白田一帶置田6000餘畝,同治三年(1864)至光緒三年(1877)建成108間和94間的莊園各一棟。
湘鄉縣橫洲鄉陳湜,於同治三年(1864)六月,獨領一軍攻入南京,搶劫金銀財物,船運至家,置田數千畝,人稱“陳百萬”。
此外靠謀財害命發家的錦屏楊氏,至光緒二十年(1894)已佔有田土1萬畝,莊園12棟、房屋5000多間。
湘潭的郭松林,國功被封一等輕車都尉,“出軍中獲資,置田宅值十餘萬”。
臨湖人劉滶,入湘軍後,官至臺灣道,後革職抄家時,抄出田契431張,值銀6290兩,房產68間,值銀4588兩。
這些廣置田產的軍功紳士,由於自身文化素質不高,往往眼光短淺,不願意做風險性的投資,也反對別人投資近代企業,損害自身的傳統利益,因而他們往往成了篤信傳統的最頑固的保守勢力。這就是湖南雖集資數百萬、數千萬的軍功紳士很多,而投資近代的企業人數最少,成為反對引進現代生產方式最激烈地區的主要原因所在。
再次,軍功紳士揮霍無度的奢侈之風,敗壞了社會風氣,使有用之財虛擲於無用的奢靡淫樂之中。“荊俗敦樸,自古志之耕農之餘,遊閒甚少,金玉纂組,雕文刻鏤,里老相傳數十年”,但是,自軍功紳士成批湧現之後,長沙府縣之人則“衣必軍綺羅,出必奧馬,宴客必珍味,居處必雕幾,故近市鎮而擁素多無封者間亦有之。”“風土記雲,湖湘間賓客宴集,供魚清羹則眾皆退用五復者,皆數十年前事。士大夫宴客珍錯交羅,競為豐,有一食至費數金者,而婚葬為尤甚。”
湘潭“及寇平,諸將擁資還,博戲倡優,相高以侈靡。嘗一度輸銀至鉅萬,明日舉典商部帖嘗之,傳以為票。未十年,潛無餘矣。”不事經學,一味追求個人享受、這在軍功紳士幾乎是極為普通的現象,使得昔日儉樸持家、力耕以食的社會風氣蕩然無存。既虛擲了大量有限的社會資財,又不能促進當地社會經濟的繁榮,不能為社會創造財富,增加就業門路,反而敗壞了社會風氣,滋長了好逸惡勞、奢侈享受的不良之風。
第四,軍功紳士勢力的膨脹,直接影響著官紳矛盾的加劇,造成了紳權對湖南地方政權的干涉。湖南的官紳矛盾在駱秉章主政湖南時已出現。駱秉章重用以左宗棠等湖南紳士組成的幕僚群體,就引起了湖南各級官吏和衙門胥吏的強烈不滿,他們四處大造謠言,或戲稱左宗棠為“左都御史”,隱射左宗棠權勢尚在官銜為右副都御史的湖南巡撫駱秉章之上。或造謠說什麼“幕友當權,捐班用命”,藉以挑撥駱秉章與左宗棠的關係,打擊、排擠參政的紳士。只是因為時局混亂,駱秉章需要紳士的支援來控制局勢,穩定人心,因而沒能達到目的。但是太平天國被鎮壓後,湖南地方官就急欲擺脫紳士對省政的制約,因而“官湖南者皆以屈抑紳士為先務”。但是,由於軍功紳士的大量返鄉,特別是一些曾手握重兵的湘軍將領退職鄉居,像曾國荃、郭嵩燾、王闓運等人退職後都曾定居於長沙,他們憑藉自己昔日的影響和與在朝為官的湘軍將領的關係,往往對地方行政產生較大的影響,使得官府對紳士的屈抑,不僅達不到預期的效果,甚至適得其反。
例如,曾任湖南布政使的蜀人李榕想讓豪紳按田畝捐稅,就是因為田畝大戶曾國荃的反對,而遭彈劾革職;湘撫毛鴻賓因“惡紳與官事,謀盡去之”,反遭到湘紳聯合反擊,毛鴻賓“乃大窘”,遂不得不“詣諸紳謝,任以事,又加禮焉”。
王文韶出任湖南巡撫後,雖心存“屈抑士紳”之意,且“日有孜孜”,但終究不敢採取強硬對策,在湘紳面前,王文韶“遇有強狠負固者則憚之,人眾則憚之,挾端求逞則憚之”
可見,近代湖南紳士的勢力已經膨脹到了挾制地方官府的強大之勢,這在全國可稱得上是一種獨特的現象。
(原載《曾國藩研究》第2輯,湘潭大學出版社2007年11月版,作者許順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