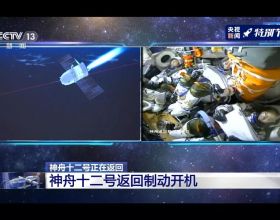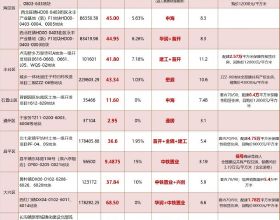汪漋(1669-1742),安徽休寧人,康熙三十三年進士,在康熙朝做了兩任浙江學政。雍正即位,汪漋的仕途迎來了爆發期,連續幾次提拔之後,雍正三年十月,被授廣西巡撫職務。如此人生際遇,是所有寒門士子夢寐以求的。
然而,汪漋的廣西巡撫只幹了6個月,江西巡撫僅僅做了8個月,封疆大吏旅途就此止步。是貪墨?瀆職?黨爭?都不是。原因非常弔詭。
雍正四年二月,第一次使用奏摺言事的汪漋,就被雍正皇帝罵了“居心不純”。三個月之後,被調往了江西。不管怎麼說,這次調動都是不正常的。怎麼回事呢?
赴任廣西之前,皇帝當面交辦了一個任務,就是訪查“左江鎮總兵梁永禧居官如何,據實具奏”。汪漋是這麼上奏的:
臣到任後,因左江鎮總兵駐紮南寧府,與省城相距甚遠。臣密加訪查,梁永禧辦理營務尚去得,在地方亦不多事。伏惟皇上至聖至明,無遠不燭,凡臣下賢否之分,難逃日月之照。臣履任日淺,耳目未周,不勝惶懼之至。
汪漋說了三個意思:一是梁永禧辦理營務說得過去,在地方上也不多事;二是皇上最為聖明,地方再遠,臣子好壞難逃天子慧眼;三是南寧府與省城桂林之間挺遠,自己到任不久,耳聞目睹不一定周全,內心感到非常恐懼。
看起來四平八穩的奏摺,一下子惹惱了御下嚴苛的雍正皇帝。雍正怎麼罵汪漋的,罵得有沒有道理,我們看一看雍正的硃批。
既雲履任日淺,耳目未周,則“辦理營伍去得,在地方不多事”之奏,亦屬荒唐。
既然履職時間短,聽到的東西不全,那麼,關於梁永禧的評價肯定是荒唐的。雍正皇帝先是從文字上找了汪漋的毛病。
桂林不過數日之程,即以為相距甚遠,京城去粵西數千裡之遙,而謂朕之“聖明無遠不燭,其賢否之分,難逃日月之照”云云,何不體情理,一至於此耶?爾初次奏摺,即如此依違瞻顧,居心不純,已見一斑,殊大失朕之所望。
桂林距離南寧區區幾天路程,你以為“相距甚遠”,京城離南寧幾千裡地,臣子是否賢良,卻難逃皇上“日月之照”,不通情理啊!雍正皇帝接著又從邏輯上跟汪漋較了真。
如果硃批到此為止,那不是雍正的做派,也不是雍正的水平。接下來的一番話,才是他的真實用心。
封疆大吏既受國家知遇之恩,當思竭力致身之義。切忌柔佞巧詐,獨善己身,而不乃心國計。朕披閱所奏,甚憂汝不克勝此任也。勉力為之!書生章句虛文,非此任所需之物。苟不以實心行實政,秉公甄別賢否,據實入告,動輒瞻前顧後,持首鼠兩端之見,以圖自便,則大負朕用人之意矣。勉之慎之!
封疆大吏既然受到天子知遇之恩,應當盡心竭力報效國家,切忌玩弄小聰明,想方設法保全個人。像書生一樣玩弄虛頭八腦的文字遊戲,不是巡撫這個職位需要的作風。如果不能實心實意做事,秉持公心辨別官員好壞,實事求是向上級報告,相反,首鼠兩端、瞻前顧後,預先給自己留退路而不講真話,那就辜負本皇帝為國擇人的心意了。
責罵看似嚴苛,倒也能看出皇帝教導汪漋為官做人的一番苦心。責令訪查“左江鎮總兵梁永禧居官如何”,是對汪漋的信任,是對臣子的天恩。汪漋對於梁永禧只有一句話評價,而且沒有實質內容,怎麼看都是不負責任的。
一省官場圈子就那麼點大,作為主官,用三個月時間去了解轄區內鎮總兵的為官聲望,決不是一件難事。按照常理,對於梁永禧的評價,好的壞的都會有,真的假的說不清,汪漋只要歸納一下,如實向皇帝報告就行了。可是,汪漋沒有這樣做。
科舉出身的汪漋,用自以為深厚的文字功底跟雍正皇帝兜起了圈子,打起了哈哈。模糊表達觀點,看似說了,其實什麼也沒說。他是在跟皇帝玩心眼,在賣弄自己的小聰明。這點小把戲,肯定難逃雍正“日月之照”了。這位皇帝,可是自詡可以看穿臣子“肝肺”的。
讓汪漋去訪查梁永禧居官如何,與其說是工作安排,倒不如說是雍正皇帝慣用的“術”。
作為官場特務文化的集大成者,雍正皇帝有多個渠道去了解一名中級官員的品德、才能、為官表現。從梁永禧後來的仕途發展情況看,他在“左江鎮總兵”任上的表現算不上“卓異”,甚至存在一定的雜音。對此,汪漋一定是可以打聽到的。是出於對滿族大臣的忌憚,還是害怕承擔失實的責任,不得而知,結果是,汪漋選擇了向皇上作了資訊過濾。
沒有透過雍正皇帝考察的汪漋,於雍正四年五月,被調往了江西。還好,仍然是巡撫。
雍正五年二月,汪漋捲入了江西鄉試考官查嗣庭、俞鴻圖收受舉人牌坊銀兩一案。九卿、詹事、科道議論,奏稱汪漋應該與副主考俞鴻圖一起按律治罪。
雍正皇帝發話,舉人交納的牌坊銀是“規銀”,非一般髒銀可比。汪漋作為封疆大吏,竟在這個當口與收受規銀的欽差主考買賣房屋,“應加處分,以儆將來”。這個人還算老成,“著降四級,以京員呼叫”。
由此可以看出,雍正還是給了汪漋改過的機會。然而,活該汪漋倒黴,就在當月,一份看起來沒有問題的奏摺,竟然惹出了大麻煩。又是咋回事呢?
雍正五年二月,正在被“立案調查”的汪漋,不知是出於討好還是表現,向雍正皇帝上了一份奏摺,請示一項工作。
江西地方舊有一項雜稅叫“落地稅”(其他省份也有),是對出售農副產品或手工業製品的小商販就地徵收的一種稅。在個體商業和手工業不發達的地方,這種稅的徵收難度很大,不容易完成上級下達的任務。
在白潢擔任巡撫時,便不再從小商小販手裡徵收這種落地稅了,改由巡撫司道每年的公捐銀兩代為繳納,然後呢,編造假名冊往戶部上報,而負責徵稅的官員仍然保留。
白潢離任之後,先後接任的兩位巡撫同樣照此辦理,逐漸就形成了一種慣例。汪漋以為此舉不符合朝廷法度,請示雍正皇帝是明令取消還是要恢復收取。
就是這麼一檔子事,又一次惹毛了雍正帝。
雍正皇帝上諭是這麼說的:
國家經制錢糧,豈臣子可以意為增減?若江西此項銳銀不應徵收,則白潢應奏請於聖祖仁皇帝施恩豁免;若系地方應徵之項,則自應令商民完納,何得將公捐銀兩代商完課,曲市私恩,以博無知小人之稱頌,並不計及將來之可永行與否?且此端一開,他省督撫何以催辦國賦?似此沽名邀譽、大奸大詐之行為,豈人臣事君之道?
作為一國之君,雍正帝義正辭嚴地講了一堆道理。
國家的錢糧稅收,怎麼可以任意增加或減少?如果江西不應該徵收落地稅,白潢應該請求康熙皇帝開恩豁免;如果是應徵之稅,就應該讓商民自行交納,怎麼可以違反國家法度去收買人心?這樣先例一開,其他省份的督撫怎麼去催辦國賦錢糧啊?像這種沽名釣譽的大奸大詐行為,哪是人臣侍奉君主的道理呢?雍正皇帝當然沒有說錯。
把前三任巡撫不符合政策的做法向雍正報告,汪漋的動機,可能有三個方面:
其一,江西政務有這麼一件事,一直以來朝廷不知道,向皇上報告以示忠誠;其二,這項工作應該如何處置,不敢自作主張,請求皇上明示;其三,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如果落地稅不能如數繳納,或者將來朝廷追究責任,主要是白潢等人之過,我既沒有欺君,任務完不成也情有可原。
官場之上,有些事情應當只說不做,有些事情應當只做不說。尺寸如何拿捏,全憑個人功夫。這點道理,以汪漋的閱歷和悟性,不可能不懂。他把這個球踢給了皇上,事實上又玩了一把小聰明。
他的小心思,被雍正皇帝看得明明白白,於是發出了靈魂三問:
汪漋身為巡撫,凡事不能據理而行,乃將白潢所行悖理之事奏聞於朕,冀朕批示。朕若批令將銳銀豁免,則是國家之經費,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所未免者,而朕安能任意輕免之耶?若朕批令仍向商民徵收,則是白潢已免之項,而朕復行徵收,無知愚民,豈不歸怨於朕乎?若批令照白潢之例,以公捐銀兩代商完課,則國體何在,有此治天下之道乎?
先皇帝六十多年沒有豁免的款項,我能輕易下令免除嗎?如果批示繼續徵收,那些無知百姓不是要把怨氣撒到我頭上來嗎?如果批示按照白潢的辦法實行,國家典章制度尊嚴何在,有這樣治理天下的道義嗎?
有一種人格叫做敏感型人格。這種型別的領導者,對於事物的感知格外敏銳,善於察覺情緒,過度關注細節,要求別人和自己都十分苛刻,有時候還會放大自己的負面情緒。雍正皇帝恰恰是這種人格。
汪漋的小聰明,著實刺激到了雍正帝敏感的神經。下意識地認為,汪漋在給他設圈套,給他出難題,要讓他陷於不仁、不明、不義。否則,一個簡單的工作請示,不會導致他釋出長篇上諭。
於是,汪漋就被降職調回了京城,從二品大員淪為從四品的光祿寺少卿。自此,汪漋再也沒有過擔當重任的機會。在雍正朝歷經幾番沉浮,甚至一度被革職。他的仕途高開低走,真的怨不得別人。一次彙報,一次請示,汪漋是怕承擔責任,反而招來了更大的責任,正可謂小聰明便是大糊塗也!
人在場面上混,偶爾抖抖機靈,確實是可以討得領導歡心的。小聰明有時候也能夠得逞。但是,這個事的機率很不穩定。有的領導是真糊塗,有的領導是裝糊塗,碰上個像雍正帝一樣不願裝糊塗的,那可就容易弄巧成拙了。
做官做事,還是實在點比較牢靠。
本文參考文獻:《清史列傳·汪漋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