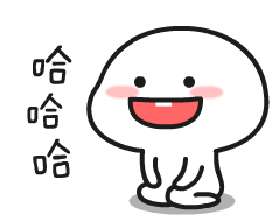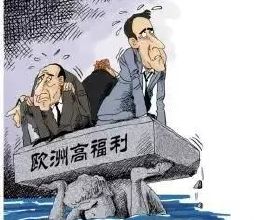拜登當局的內閣級成員、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琳達·托馬斯-格林菲爾德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說,除了經濟措施外,軍事措施也列入了美國對烏克蘭局勢升級的考慮中。
這是美國政府高階官員首次以如此明確和肯定的措辭表述其對烏克蘭局勢的軍事應對措施。總統拜登一直在此問題上閃爍其詞。
早前,當他在談及美國的反應時,強調了莫斯科將會受到的嚴厲制裁,但不包括美國出兵烏克蘭選項。
直至其入主白宮一週年,在記者會上除了重複若俄進犯烏克蘭將付出慘重代價的老調子,仍以含混的語氣就俄可能對烏進行的“小規模侵襲”表現出了綏靖主義態度,從而引發基輔當局的憂慮。
格林菲爾德的話可能是為拜登此前的“失言”聊作彌補,然而拜登當局在軍事應對方面搖擺不定和怯懦軟弱的態度,凸顯了其政府內部和美國與盟友間的深刻分歧,甚至在美方大力推動的美歐協調經濟制裁問題上,歐方內部也存在不少不同聲音。
拜登當局在軍事應對上的姿態,一方面是美國內民意及民主黨政府厭戰情緒的折射,一方面也跟華盛頓對莫斯科策略的改變緊密相關。
它在開始國政運作後不久就決定拉攏俄羅斯以集中優勢力量抗衡首要戰略對手,為此開啟了對俄外交新階段及美俄關係正常化程序,在短短一年任期裡,美俄總統級正式對話就達3次,部長級及戰略穩定對話、網路安全對話等各層級對話持續進行。
這被莫斯科視為千載難逢的機會,普京當局反客為主,擴大了胃口,提高了要價,趁機提出締結安全保障條約倡議,要求美國及北約向其提供戰略安全法律保證。
以美國對俄外交策略轉變為契機,莫斯科將其與華盛頓對話臺階大幅推高到一個新高度,並以此為新的基礎,作為開展對美、對西方外交的新基礎和新條件。
為了加強這一新立場,普京當局在俄烏邊境陳兵10萬,作出佯攻態勢,將自身進一步置於可進可退的有利地位:假如美國及西方反應軟弱,它就趁機進軍基輔,獲取更大的地緣戰略利益;假如美國及西方反應強硬,那麼至少也可以作為其加強對美、對西方外交併推動締結新安全保障條約的重要籌碼。
拜登當局當前在莫斯科那裡面臨的局面,不是如何更好地推進其戰略議程,而是被俄羅斯牽著鼻子走,考慮如何回應和滿足普京當局的“胃口”,甚至不得不降格以求莫斯科在俄烏邊境對局勢進行“外交降級”,作為進一步開展俄與美國、與北約、與歐安組織“三個平臺”談判的前提。
拜登當局一番外交操作並被莫斯科利用的戰略結果是,美國必須在接受一個在歐洲更大幅度崛起的俄羅斯以獲得其“心照不宣”地合作共同應對首要戰略對手,或者面對一個“不合作”的俄羅斯,同時在歐亞兩個方向應對首要戰略對手和次要戰略對手之間,作出選擇。
可能正因如此,布林肯最近才感慨“一旦俄羅斯人進入你的房子,有時很難讓他們離開”,拜登當局同樣嚐到了這個滋味,
華盛頓對“三個平臺”第一輪談判的三心二意引起莫斯科不滿,抱怨(美國)本應該停頓並專心就俄方提出的問題給予回覆,而白宮及其西方盟友卻發動了一波“有毒”的宣傳戰,聲稱俄羅斯是侵略者、歐洲文明的敵人、對國際穩定構成威脅。
多麼難纏的主兒!
在大國競爭背景下對莫斯科的戰略需求,特別是忌憚首要戰略對手,導致華盛頓對莫斯科態度的搖擺不定和怯懦軟弱,一方面自不必說激勵了莫斯科擴張的胃口和要價,使自身陷入了兩難境地,另一方面拜登當局在逼問之下不得不把軍事應對俄羅斯“侵犯”烏克蘭列為潛在的選項,也是對臺海局勢演變深為忌憚的結果。
基於美國的大國競爭戰略,東海最大島嶼的地緣政治、軍事和價值觀價值在美國的全球和地區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顯要,美國對烏克蘭的外部“侵犯”的反應,直接影響到該島及美國所有盟友對超級大國的戰略信心,影響到其能否像過去那樣擁有全球號召力。
為了增強該島及其廣泛的盟友的信心和信念,拜登當局就必須在烏克蘭展現“不惜一切”的姿態並在必要時採取行動。
一旦如此,美國可能會遏制住臺海的某些局勢發展,但也意味著可能要失去莫斯科的戰略合作。
要不然,就是要與普京當局達成歷史性的“大交易”,對莫斯科的戰略安全作出法律保證,而這同樣使後者達到了更大幅度崛起的目的。
普京當局實際透過一系列外交和軍事行動,包括最近展開的與戰略協作夥伴、敘利亞、伊朗、委內瑞拉的頻密外交和軍事互動以擴充自身的外交籌碼,將拜登當局逼到了一個牆角:
是選擇在法律上對俄羅斯的戰略安全作出保證,接受一個全面崛起的俄羅斯,還是面對莫斯科進攻烏克蘭及其他軍事、經濟和外交措施,特別是與其首要戰略對手“背靠背”,破壞華盛頓的戰略意圖,失去一個合作的俄羅斯。
由此可見,普京當局不遺餘力地利用其在當今大國格局中的“關鍵變數”地位,將其作為戰略籌碼,逼美國就範。反正對於莫斯科來說,這是一筆穩賺不賠的生意。
無論作出何種選擇,對美國來說都有戰略隱憂,拜登當局面臨艱難的抉擇。